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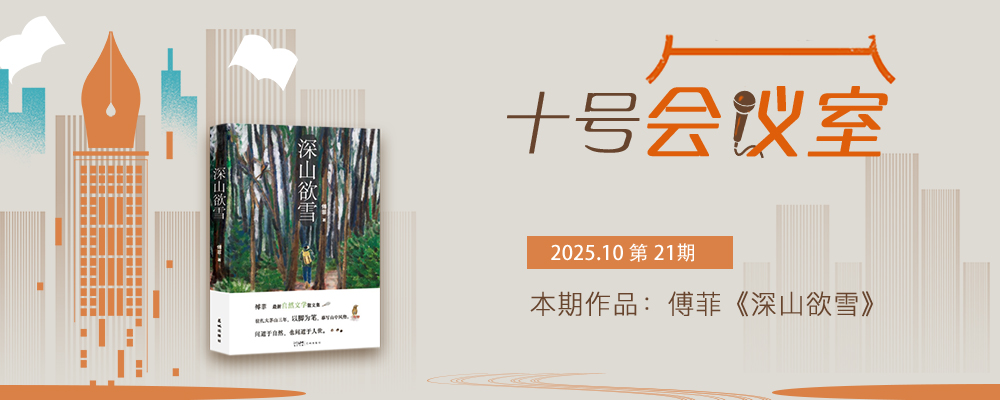
出于大力推薦優秀作品的考慮,中國作家網特開設“十號會議室”欄目,聚焦那些或受到廣泛關注的,或仍未被充分重視的文學新作,約請中青年作家、評論家參與評點,集特約評論、深度對話、創作心路等相關信息,與讀者共同展開閱讀與探討,力求以豐富的角度全面呈現作品的魅力。2025年10月總第二十一期,中國作家網“十號會議室”欄目為大家推薦傅菲的散文集《深山欲雪》。傅菲駐扎大茅山三年,實地探訪山林中的每一個角落,以腳為筆,書寫山澗、魚鳥、山民的命運。《深山欲雪》中,山澗蟲鳥蓬勃生息,山民腌菜煮茶煙火綿長。作品將山民口述史、博物學觀察與東方哲思熔鑄一體,展現散文寫作的厚重與輕盈。(本期主持人:陳澤宇)
你會有那種……除非心頭很靜時,就無法讀進去的書嗎?
傅菲的《深山欲雪》對我來說是的。那些林場、山谷、河灘間的動植物觀察,與育菇人、捕魚人、養蜂收蜂人的交談,種地、制菜、釀酒、焙茶之類的勞作過程,傅菲寫得散淡,克制,含情。
假如我不用一種與文字等速的目光屏息去讀,會錯漏大量細節,只留下模模糊糊的氣氛和印象。[詳細]
作為“深山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深山欲雪》凝結了傅菲多年的心血,由花城出版社于今年5月推出。
為了深入了解大茅山的自然生態與山民生活,傅菲耗時近三年,徒步走遍了峽谷、荒野、山脈、河流,進行了大量實地走訪。
《深山欲雪》以知行合一的田野調查、獨特的自然觀察和充滿哲思與美感的文字,為讀者呈現了深山的奧秘與自然文學的獨特力量。傅菲坦言,這是三部曲中他耗費心血最多的一本書。
[詳細]

傅菲
那時我懷有野心,以社會學的角度,解剖學的方法,批判現實主義的態度……[詳細]
自然文學最大的特質是尊重生命我一個人,深入深山,去辨識植物,去觀鳥,去傾聽蟲鳴……[詳細]
生命氣場是散文的第一要素散文無論如何變革,唯一不可變的,是散文文本里彌漫的作家生命氣場。沒有生命氣場的散文,是死散文。我把生命氣場列為散文的第一要素。 [詳細]

為山作注
在成為《深山欲雪》的責編以前,我曾編過傅菲老師發表于《花城》的《曉霞里》。其間的寧靜與詩意,曾深深滌蕩過我這位久坐辦公室的看稿人。
初讀《深山欲雪》時,這種感受更為強烈,撲面而來的山野氣息、樸素的田野底色和豐沛的詩意讓我確信:它不僅是優秀的自然文學作品,更是浮躁時代里一劑沉靜有力的心靈良方。
江西大茅山,這片雄踞贛、皖、浙三省咽喉的原始山林,在傅菲的筆下,從宏大的地理名稱聚縮成無數細微而具體的生命瞬間。
[詳細]

問道于自然
傅菲在最新散文集《深山欲雪》的跋《自然精神》中寫道:“問道于自然,也問道于人世。
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學始終更關注人的命運,更關注人的社會與歷史,當我們談問道于人世時,我們認為這樣的作家作品理所當然,實至名歸,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
但是當我們的文學關注自然,關注自然萬物的生存、習性與命運,關注人與自然的錯綜關系,問道于自然時,我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嗤之以鼻,認為這樣的作家具有隱逸趣味,玩味小道,遠離經世濟用,無補于世道人心,致遠恐泥。但是事情的真相真的如此嗎?
[詳細]

自然與人世的協奏曲
新世紀以來生態散文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韓少功筆下的山南水北,沈念筆下的大湖消息,張煒筆下萬松浦的動物,王族筆下的獸部落……許多散文家都樂于傾聽萬物的心音,宣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
以自然寫作聞名的傅菲,其散文集《深山欲雪》以獨特的視角和方式,譜寫了一首著眼自然亦不忘人世的生態協奏曲。
在觀物中感悟到人的生命應該和萬物一樣“有一種無窮無盡的生機”,應該充滿仁慈與關愛樂觀地活下去,而非深陷物質生活的泥淖,背負無盡的沉重與疲乏。
[詳細]

在自然的詩行里,我們都是蹩腳的讀者……
活在塵世間的人,或許都有一顆求取寧靜的心。當人們真正走進自然,走進寧靜,接觸草木鳥獸時,能否安然于自然之中,能否真正找到心中的桃源之地,安妥那顆心。
我想,未必。
我們可能會有一種感受,在塵世喧囂中渴望自然,在自然中又念塵世之情。一種生活總有勞累之時,徘徊成了一種生命的形態。一座圍城,進去了,再出來,出來了,還渴望進入。我們這些普通人,冬天畏懼嚴寒,渴望夏天。夏天又埋怨炎熱,迫切回到冬天。總不能安然于當下,順道于自然。
[詳細]
在《深山欲雪》中,作家多次書寫山林中的人類居所在廢棄后被荒野占據的狀況,使其成為作品難以忽略的生態隱喻:《引漿源》《楊源坑》中都記錄了峽谷的生態變遷史,森林經數十載的砍伐被消耗殆盡,又在人類撤離后的漫長光陰里漸漸恢復,木橋爛斷,屋舍倒塌,為芒草、喬木所占;《盤石山峽谷》中,雙溪水庫生活區的舊樓房廢棄坍塌后長滿荒草,成為獾、野豬、山鼠、黃鼬等野生動物的臨時避難所,昔日的菜地和樓前機耕道被樹和雜草覆蓋。曾因河水被投毒而絕跡多年的水鳥再次飛還,逐年增多,又棲息成群;《紅隼落腳之地》中,野豬占據空屋為巢,驅而復返……“人把生活之地,交還給了草、樹、鳥和野獸。”人類痕跡的消退反而使自然恢復了神性,這些荒廢的場所作為文明失落的隱喻,既是人類文明脆弱性的證明,也是自然重掌主權的刻碑。從自然狀態到人類破壞,再到人類離場后恢復至自然狀態——這一循環演變的模式,本質上是自然主體在無窮的回歸中彰顯其永恒性,而與之相對的,則是人類作為客居者的生存定位。 [詳細]
《元燈長歌》全書以傅菲的生養之地饒北河上游的鄭坊盆地為空間載體,分四輯呈現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樁樁件件。第一輯“江河合水”,主體是這土地的革命時期和繁衍其間的人,雖每篇各有側重的人物,卻都能置于時代之中,頗有群像之感。第二輯“大地芳春”,來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的鄉村當下,人在時間之河中載沉載浮,卻也展現出頑韌的生命尊嚴。第三輯“萬物生動”,主要講述人與動物的關系,在深入理解動物的同時,也深入理解了人自身。第四輯“舞詠而歸”,探看鄉村手藝人的技進乎藝,雖免不了沉重的悲歡離合,卻隱隱翻出一層扎實的豁達。一本書結束,一個村莊就成了一條綿延不絕的河流。 [詳細]
傅菲的新作《人間珍貴》是一篇題材頗為獨特的作品,這篇散文以王德華的人生經歷為主線,再現了醫院里的“擺渡者”這個隱秘群體的工作場景與生活日常。當病人在醫院去世后,“擺渡者”將逝者從病床轉運到服務車,他們是逝者最后的陪伴者和護送者。在漫長的歲月里,王德華和其他“擺渡者”懷有對生命的敬畏與尊重,堅持為那些歸去者送行,維護了逝者最后的尊嚴與體面。在現實生活中,“擺渡者”是一個個普通的勞動者,他們隱匿于醫院的角落,從不言說自己的職業,身上卻散發出溫暖的人性之光。他們是人世間的艄公,默默為眾生撐船。在傅菲的筆下,“擺渡者”所從事的逝者轉運工作,是人間最珍貴的善行,值得眾生感激與敬畏。 [詳細]
“深山”是傅菲近年文字中的一塊夢土,作者自言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境”。2020年春《深山已晚》出版,該書是他2013年夏客居閩北榮華山下一年多結集的作品。2021年夏,傅菲去往德興市大茅山北麓筆架山客居兩年多,又完成了一本有關深山的書。書中,他寫山窗明月、春酒冬菜、新麥方塘、鳥群游魚……更有一個個面目清晰、敦厚淳樸的山民。傅菲近年的創作重心從早年的鄉土書寫轉向自然書寫,對此他有頗為清楚的自覺,“我在深山之中發現萬物生命的價值,構建自己的美學。我力圖將一座普通的山寫出萬千氣象”,其間也分明辨出他個人創作一貫的對于自然鄉土的可循之跡。傅菲力圖在作品中構建一種個人的山地美學,如同懷特的塞耳彭、梭羅的康科德、約翰·巴勒斯的卡茨基爾山,他在其作品中也營筑了自己的文學夢土,早先的饒北河畔楓林村,如今的閩贛深山,因而也使得他筆下的自然萬物有強烈的地方感,那是獨屬于他的風景、他的深山。 [詳細]
張守仁先生在書的序言《自然的圣徒》中夸贊:“傅菲是個詩人。他詩意地棲居、觀察、寫作。”的確,傅菲以純美的語言為閱讀《深山已晚》的人,展開了一幅長軸山水畫卷,每一個落筆的地方都細膩婉轉,美成了空谷中回旋往復的詩。他在《鳥聲中醒來》中看到了露珠的凝結之美:“光從天上漏下來,稀稀薄薄。空氣濕潤,在欄桿在竹杈在樹丫在尼龍繩上,不斷地凝結露水。……我看見露珠,人便安靜下來,我便覺得人世間,沒什么事值得自己煩躁的,也更加尊重自己的肉身。很少人會在意一顆露珠,甚至感覺不到露珠的存在。只有露水打濕了額頭,打濕了身上的衣物,打濕了褲腳,我們才猛然發覺,露水深重濕人衣,再次歸來鬢斑白。露是即將凋謝的水之花。它的凋零似乎在說:浮塵人世,各自珍重。……每一個早晨,鳥聲清脆,光線灰白,露水凝結,這樣的境界呈現在了我面前。綴滿竹竿的露水,我是其中一滴。”[詳細]
傅菲是一位有著自覺的文體意識和創作情懷的散文家,出生于贛東北農村,對鄉村生活的體驗極其深刻,他以散文家的血氣和精神內核,構建出一個力量與美感并存的文字帝國,以悲憫之心關注草根人物的生存狀態,通過對底層、沉默的弱勢群體的關注,折射出生命的隱痛與荒涼,體現了普通人身上凸顯出的純真人性和美好品質。讀者通過他的作品,可以體會到一種由愛而生的人文關懷。此外,他的散文中還蘊含著強烈的在場感——通過生活層面、身體層面、自然層面以及靈魂層面的多層次交織與碰撞,從不同的角度感悟生活,放飛自己的內心世界。傅菲的散文是用生命去體驗的感受性文字,通過大量的靈魂與靈魂的對話、靈魂與肉體的反思,在飽嘗人間煙火中,給人一種活色生香、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在真實、接地氣的寫作中透射出其文藝風格和哲理蘊含。 [詳細]
人在繁忙奔走,萬物暗示我們不要那么匆忙,該停頓需停頓,該安歇需安歇。傅菲在山中生活之后,放下了很多東西,門前森林溪流,窗外飛鳥星空。他將自然觀察與反思一一寫入此書。自然的質地等同我們精神的質地。我們關注社會,思考個體生命,我們都在尋找自己的道,不至于活得迷茫。“夜靜了,在冰箱下、在書柜背后、在床下,蟋蟀發出了兮兮兮的鳴聲。蟋蟀的翅膀有銼狀的短刺,相互摩擦、振翅,發出一種和悅、甜美的聲音。兮兮兮,兮兮兮。我安坐下來,靜靜地聆聽。我交出耳朵,徹底安靜了下來。假如我愿意,可以一直聆聽到窗外發白。天白了,蟋蟀的鳴叫聲歇下去了,蟬吱吱吱吱,叫了起來。我是一個對聲音比較敏感的人,對溪聲、鳥聲、風聲、雨聲、蟲聲入迷。閑余之時,我去荒僻冥寂的野外,在溪流邊駐足,在林中流連。我是可以在溪邊坐一個下午的人,凝視水波。流水聲從琴弦上迸發出來似的,激越、清澈,淘洗著我的心肺。流水聲是不可模擬的,簡單往復,節奏始終也不變。入耳之后,又是千變萬化,似群馬奔騰,似崖崩石裂,似珠落玉盤,似瓦檐更漏。蟋蟀聲也是這樣的,兮兮兮,一個單音節,圓圓潤潤,一直滑下去。作為自然之聲,每一個聽力正常的人,都非常熟悉蟋蟀的鳴叫。”[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