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西岸,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

1990年代初市場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知識界掀起的一場重要思想論爭。其核心圍繞市場經濟轉型背景下,人文價值是否失落、知識分子如何自處等議題展開。通過《上海文學》《讀書》等刊物,參與者深刻反思了商業化浪潮中精神世界的危機,試圖為社會重塑價值關懷與批判精神,標志著當代知識分子對自身使命的一次集中叩問與思想自覺。這就是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從人文精神大討論到學者賀照田在2004年底提出、再到2018年開始的“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討論,構成理解橫貫三十年中國當代社會思想的重要線索。賀照田《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于2006年出版,這項研究將人文精神大討論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對象,對其構成了深刻的批判性延續與超越。
以該書出版20周年為契機,11月15-16日,“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的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西岸美術館舉行。會議雖然以賀照田著作為起點,但實則觸及了中國知識界自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以來的深層焦慮與轉型渴望。與會學者來自文學、哲學、社會學、藝術策展等多個領域,他們不僅回顧歷史,更試圖在當下的社會裂痕中尋找思想的支點。
人文精神的當代回聲與知識感覺的重構
回溯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目的是聚焦于其當代意義。如何理解那場討論的遺產在今天的延續與變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指出,賀照田的著作實際上是對這一時期的深化,其核心在于剖析知識界的“感覺結構”——那種精英與民眾、知識與現實之間的深刻割裂。金理認為,這種割裂感并非抽象理論問題,而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困境,例如青年學生在“考編”熱潮中的焦慮,或知識分子在學術體制內的無力感。
上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朱羽進一步深化了這一討論,他強調人文研究應當關注“觀念感覺”的歷史形成過程。朱羽以1980年代的潘曉討論為例,說明如何通過細讀歷史文本,揭示情感結構如何被時代塑造,而非簡單套用理論框架。“人文知識需要從經驗的具體性出發,”朱羽指出,“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實踐,而非沉迷于抽象的理論建構。”
解惑、解蔽與解郁,是中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吳寶林概括人文知識當代使命的三個關鍵詞。吳寶林認為,知識生產必須直面人的身心困境,例如青年在就業壓力下的焦慮或老年人在數字時代的疏離感。這種視角要求人文工作從批判轉向建設,與全球人文主義復興(如查爾斯·泰勒對“本真性”的探討)形成呼應。
上海西岸美術館學術總監劉瀟則從藝術機構的角度補充道,美術館可以成為思想再出發的“公共廣場”。她以館內近期舉辦的“甌江山水詩路展”為例,說明如何通過在地調研與社區參與,激活地方文化記憶,使知識從精英走向大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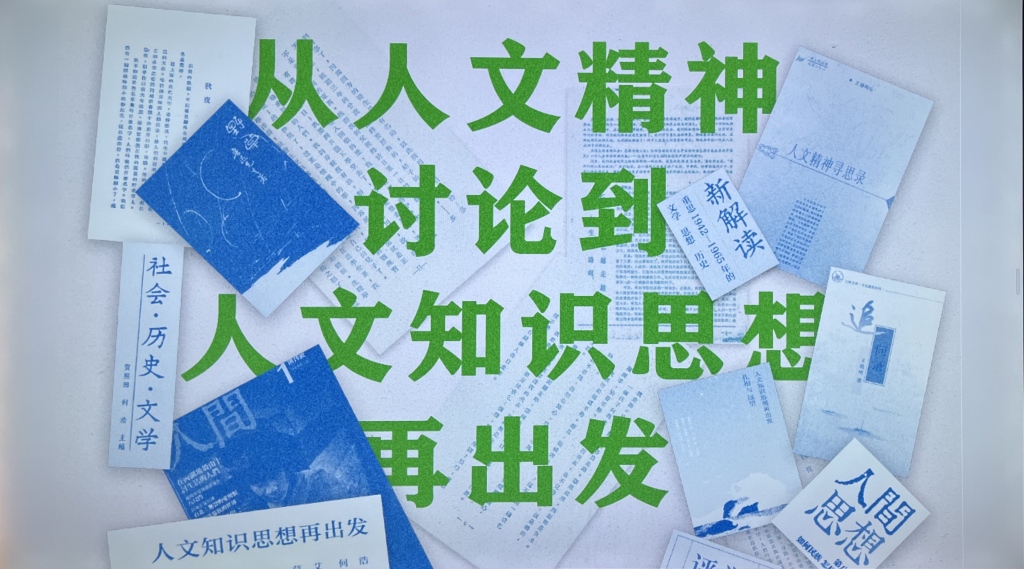
“身心”作為認知的媒介與跨界實踐
賀照田的研究從“苦惱”出發,揭示了當代中國知識感覺中“自我”與“社會主體”的深刻割裂。在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王健看來,這種割裂既源于認識結構內部的矛盾,也表現為社會主體建構對真實自我感受的排斥。其通過追溯“當代”觀念感覺的歷史形成,指出必須通過辨識“今日之我”,將那些被主流話語忽視的自我體驗納入知識建構。這種以“感覺”為方法的研究進路,旨在重建更具彈性的人文知識結構,使社會主體與自我形成共生關系,從而為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開辟新的可能。
人文知識如何實現方法論革新?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曉帆分享了教學實踐中的創新嘗試。她引導學生細讀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分析主人公孫少平在改革初期的身心掙扎,從而連接歷史與當代青年的類似困境。楊曉帆認為,這種方法打破了理論優先的慣性,讓知識從“觀照”轉向“介入”,從而讓學生能從文學中感知、理解更為廣闊的歷史與現實生活。
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夏天提供了教育現場的深度觀察。夏天發現,當代青年在虛擬世界(如二次元文化)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深刻裂痕,許多學生通過游戲或社交媒體尋求即時反饋,以緩解不確定性焦慮。在他的“中小學語文教師訪談項目”中,夏天嘗試打通高校研究與基礎教育之間的壁壘,通過深度訪談教師,探索文學教育如何回應青年的情感需求。“人文知識需要‘接地氣’的轉化,”夏天強調,“例如將經典文本與學生的日常經驗結合,從而避免知識懸浮于現實之上。”
國際視角的引入豐富了方法論討論。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鈴木將久比較了中日知識界對現代性問題的不同回應。鈴木提到,日本戰后思想家鶴見俊輔倡導的“常識的哲學”,強調知識必須貼近日常生活,這與中方學者關注的“身心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韓國圣公會大學中國學系教授李南周則分享了韓國“變革性中道”運動的經驗,強調知識需扎根本土而非移植西方范式。李南周以韓國青年運動為例,說明如何通過社區實踐化解個體化困境,為東亞對話提供參考。
青年困境、藝術介入與公共實踐
“這場討論始于對時代精神的批判,卻迅速轉向知識分子內部的自我詰問,暴露了人文學科在回應復雜現實時的準備不足與結構性乏力。”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昶以當代人文學者面臨的學術與思想困境為起點,追溯至1993-1995年的“人文精神討論” 作為關鍵參照。她指出,此后人文學術在學科化、專業化建設中,雖建立了系統知識,卻導致了思想與學術的割裂,削弱了其回應時代、安頓“人”的身心困境的能力。
由此她進一步指出了“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在當下的意義,這要求構建一種新的知識形態:既能深入文本,保持學術嚴謹;又能面向時代,涵容思想活力,讓文學研究在歷史與當下的對話中,重新承擔起其應有的人文使命。
而對于藝術如何介入人文知識的生產,南京大學莫艾教授從藝術史角度表示,當代藝術實踐為人文知識提供了新的表達形式。莫艾以一些青年藝術家的社區項目為例,說明藝術如何成為連接個體與社會的媒介。例如,某藝術家通過公共壁畫項目,讓居民參與創作,從而激活社區對話。策展人翁楨琪則分享了“莫樸藝術回顧展”的策展經驗,通過掃描手稿、重建工作場景,讓觀眾“進入”藝術家的身心軌跡,體驗創作中的掙扎與突破。“策展不僅是展示作品,更是激活歷史記憶的過程。”他說道。
劉瀟進一步闡述了美術館作為“思想廣場”的定位。她表示,美術館正在嘗試通過展覽、講座和工作坊等多種形式,構建開放的知識交流平臺。“藝術機構可以成為人文思想落地的實踐場域,”劉瀟說,“讓學術思考走出象牙塔,進入公共空間。”
人文知識的跨界對話與在地實踐
會議的尾聲,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的賀照田坦言,自己的工作是“在苦惱中承擔”,并倡導學者以“弱性格”的姿態深入現實,而非追求宏大的理論建構。
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人文知識的思想再出發,注定是一場在困境中尋找生機的漫長旅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符鵬認為,人文知識應當保持對現實問題的敏感度。他提醒,知識生產需警惕兩種風險:一是脫離現實的概念游戲,二是失去批判性的妥協。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系助理教授王東美表示,人文思想的活力不在于答案的完美,而在于問題的真誠——唯有直面時代的斷裂與個體的困惑,知識才能真正“安頓生命”。朱羽則認為,人文知識的活力來自對時代問題的敏銳把握,“當代學者需要建立更開放的知識視野,在跨學科對話中尋找新的生長點。”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姜濤的回應圍繞80后文學研究者的代際困境展開,探討了在當代學術體制與知識生產模式下青年學者面臨的普遍性挑戰。他指出,當前文學研究領域存在諸多未解難題,如歷史化與當代性、史料與批評之間的張力,這些困境背后有著結構性原因,而非僅個人能力不足。在姜濤看來,人文知識的再出發需要超越學科內部的自我循環,通過構建具有實踐性的新型知識社群,加強與社會不同群體的有效交流,并在教學與學生互動中開拓經驗,從而推動知識感覺與現實回應的根本轉化。
以人文知識再出發為探索方向,賀照田的“身心方法”提供了具體路徑,藝術、教育等領域的實踐展示了多元可能,全球視角的引入則提醒,中國的問題是人類共同困境的一部分。從批判到建設,從理論到實踐,從精英到大眾, 這場在美術館里的研討會既是對1990年代人文精神討論的延續,也是對新時代挑戰的積極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