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好的“故事核”,才能寫出生活的質感 ——訪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家許廷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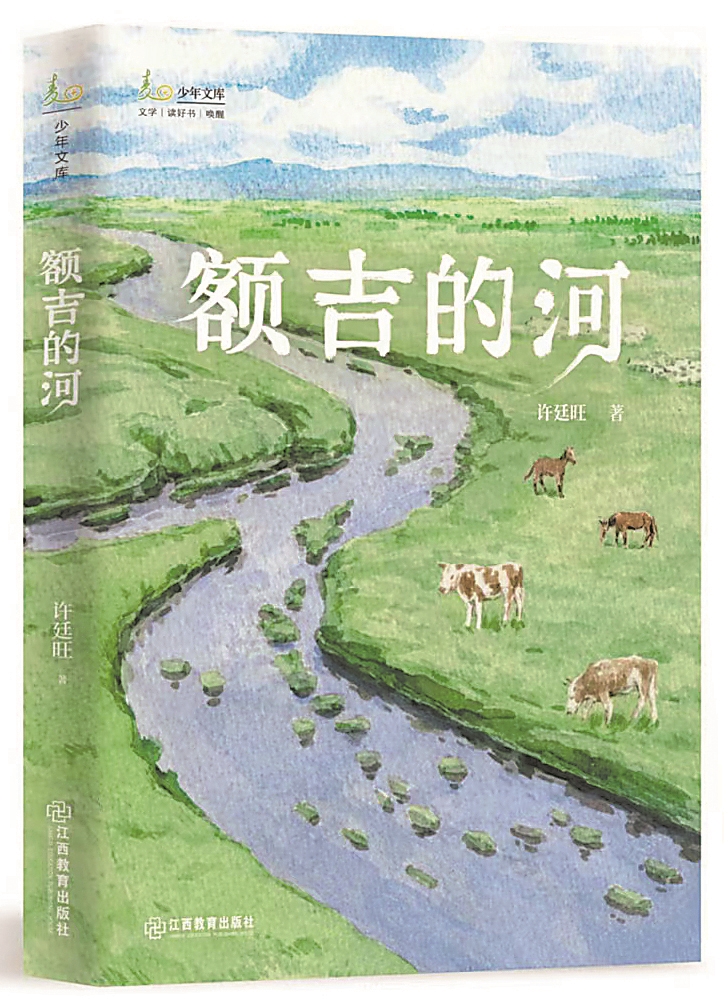
《額吉的河》,許廷旺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9月
記 者:許老師好,祝賀您的長篇小說《額吉的河》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翻開這本書,給我最直觀的印象就是目錄很特別。上中下部每一章節都用一句話作為小標題,連綴在一起,像一首詩、一篇散文,也像一段生動的故事。“額吉”與“河”這兩個關鍵詞反復出現多次,或可視為作品的“題眼”。這樣的藝術處理背后有何深意?
許廷旺:“額吉”與“河”既是作品中描述的人物形象、自然風景,更是一種意象。玉萍的媽媽顧醫生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經常帶著三個孩子去弄堂附近的小河,希望有人收養他們。她堅信小河把這個消息帶走了,堅信在陌生之地有人收養三個孩子。天下的河是相通的。玉萍做了馬背上的醫生,夜診回來,看到家附近的小河,聯想到弄堂附近的小河,這條小河從南流到北,從上海流到幾千里外的內蒙古大草原,印證了媽媽的想法:母愛如河,源遠流長。“額吉”既代表著親人對孩子的關愛,如寶力皋、銀花夫婦和另外兩對夫婦;也代表著社會層面對孩子的關愛,如蘇木達、阿力瑪老師;更代表著國家層面對孩子的關愛,如旗長。旗長這一形象只出現了兩次,卻起著“點睛”作用。關于小標題的設計,感謝你讀得很仔細,也符合了我和編輯的初衷:哪怕在小標題上也應具有文學色彩。
記 者:小說以“三千孤兒入內蒙”的真實歷史為創作題材,本身已具有一定的敘事難度。故事主人公是玉萍、玉香、玉山姐弟三人,三個主要角色的人物性格、成長經歷和人生軌跡互有交叉、互相嵌套,又為小說情節的鋪陳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增添了另一重挑戰。您是如何應對這種難度與挑戰的呢?
許廷旺:我一直認為,兒童文學應該像成人文學那樣,既要描寫出生活廣度,也要有深邃思想,更要有藝術上的追求。不能因為是兒童文學,面對讀者是未成年人,自動降低文學水準。最近幾年,我的創作一直秉承這一理念。要想達到這一效果,得更注重作品的結構,我往往會采用三條線索:主線索、副線索,在主副線索中暗藏的第三條線索。這樣人物性格、成長經歷和故事情節互有交叉,互相嵌套,作品就有種厚重感。當下,大多數兒童文學作品是線型結構、線型情節,不是說這種作品不好,但這不是我所追求的,更不是我想要的。回過頭來再說《額吉的河》的結構,它不是簡單地分成上、中、下三部分,而是每一部分開篇都有一個1500字左右的情節,這個情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把每部分的最后情節前置。初讀可能會有小小的障礙,但讀起來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想,一部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是一本百科全書。這部作品的背景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怎么寫當時的社會環境,對我來說有較大的難度。尤其是兒童文學面對的主要讀者是未成年人,如果處理不好這一背景,就會讓小讀者產生割裂感、陌生感,甚至有認知上的隔閡。所以,在創作之初,我就采取了歷史背景的“虛寫”,這種處理方式并不代表沒有歷史感,而是通過很多細節表現出來。文學作品源于現實生活的再創作,當我們讀作品的時候,有時候會產生身臨其境之感,認為作家寫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甚至忽略了它是虛構的藝術作品。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覺,原因很簡單,就是細節起著作用。細節描寫越細致、越逼真,故事情節也就越真實。就《額吉的河》來說,它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記 者:此前,我常常能在與“三千孤兒入內蒙”有關的文藝作品和新聞報道中,讀到內蒙古牧民為養育“國家的孩子”付出的辛勞與汗水,為以民族大愛回報“國”與“家”的歷史佳話而感動。但《額吉的河》讓我讀到了另一種視角,那就是這些孩子們復雜而幽微的心理活動。您為何選擇以孩子的“負面情緒”作為展開敘事的切入點?
許廷旺:無論是成人文學,還是兒童文學,最吸引讀者的首先需要有一個“好故事”。成熟的作家不僅僅要寫故事情節,還要寫到自然風光、民風民俗、文化歷史,更要寫出人物表達情感的方式等等。確切地說,一部作品要有一個好的“故事核”,這樣才能寫出生活的質感,寫出人的精神特質,也就是文學的特質。我在做閱讀推廣時,曾有小讀者提問:是否可以把人物的性格設計成活潑、可愛,以幽默、風趣的情節切入?我回答說,這是另一個故事,或是另一個類型的故事,不是我想寫的。顯然,以孩子的“負面情緒”作為敘事的切入點,基本確定了故事情節的走向,與前面我說的有個好的“故事核”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確定作品方向的一個關鍵因素。另外,以這一點切入的敘事,也更具有故事性,能讓我塑造的人物形象、性格更具有張力。
記 者:我對兒童文學作品的閱讀期待總是陽光與溫暖的,在讀到姐弟三人兩次失去父母至親的時候,覺得實在太過殘酷和沉重,由衷地希望銀花和寶力皋夫婦能夠健康長壽地陪伴他們直到長大成人。您認為,作家應該怎樣面對和處理所謂的“禁忌”書寫?
許廷旺:兒童文學發展到今天,就敘事方式來說,用“千姿百態”形容,一點兒不為過。我也曾創作過輕松、幽默的兒童文學作品,后來我的創作逐漸轉型,創作內容大多是凝重的,或者說有凝重的傾向,自然風格也就顯得凝重。曾有編輯開誠布公地給我提出這一問題:話題沉重。我不否認,或許每個作家追求不一樣,我更適合具有沉重感的創作。既然有了這種選擇,像“死亡”“疾病”這些敏感話題是無法回避的。就像成人文學有兩大永恒主題:愛情與生命,既然寫到“生命”主題,死亡、疾病就是繞不開的。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有很大區別,如何讓小讀者從心理上易于接受,往往更考驗作家的寫作水平、技巧。同時,還要考慮作品的內容,既要有利于人物形象的成長,也要考慮讀者心理承受能力。
記 者:小說的結尾,玉萍已從上海都市的孤兒成長為內蒙古草原上“馬背上的醫生”,可以說,她的成長鏈條很完整。不過,您并沒有給玉香、玉山寫一個明確的結局,“留白”給讀者帶來了想象的空間,也讓他們的成長處于“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這是為什么?
許廷旺:玉萍來到草原半年后,與妹妹、弟弟重聚于一個家庭;6年后,三個孩子成為地地道道的草原孩子;又兩年后,玉萍成長為“馬背上的醫生”,這是玉萍的閉環成長。但故事中玉香、玉山的成長是留白的,是希望給讀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間。這樣的設計意味著少年的成長永遠在路上。成長的“進行時”恰是成長小說的特點:孩子的成長處于進行時,成年人的成長也處于進行時,比如《德伯家的苔絲》《嘉莉妹妹》《簡·愛》等作品,寫的就是成年人的成長。當然,這都是成人文學作品,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內。但《額吉的河》中,孩子與成人都在故事的發展演進過程中不斷成長,這種成長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的;既是個體的,也是群體的。孩子與成人彼此攙扶,共同從“稚嫩”走向“成熟”。
記 者:草原是您特別偏愛的題材,《男孩與草原雕》《送絕影回家》《最后的木屋》《雕花的馬鞍》等作品都圍繞草原與少年的故事展開。與此前的作品相比,《額吉的河》作為兒童文學主題創作,顯得較為特殊。近年間,主題類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盛行不衰,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您認為,優秀的兒童文學主題創作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質?
許廷旺:確實,近年來主題類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很盛行。如果在創作上把握得好,堅持得好,是件好事。但如果創作直奔“主題”去,忽視了作品的“文學”性,最終創作之路會越走越窄,內容也必將越來越乏味。換句話說,主題出版考驗的是作家。作家面對主題類創作,尤其是對一個成熟作家來說,一定要堅持創作理念,堅持藝術追求——首先它是一部文學作品。同時,還要保持清醒頭腦,不能被流行裹挾,泥沙倶下,最終被湮沒。
《額吉的河》出版后,被認為是主題創作,我不反對。但在我的腦海里,壓根就沒有“主題”這一想法。我的創作規律和走向,都是沿著文學性、思想性、藝術性這一既樸實又具有高度的準則來創作的。哪怕是具有主題性的話,比如“國家的孩子”,在書稿中都沒有出現。
說到這里,我還想簡單談談主題創作背景的處理問題。有人讀《額吉的河》,就提到了作品背景的缺失。我想以海明威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為例。海明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戰爭為背景的,他做過戰地記者,如果在創作中寫戰爭,沒有誰比他寫得更詳盡。遺憾的是,他卻只字未提。當初,編輯看書稿,如果他不說明,編輯對故事發生的背景也感到一頭霧水。今天,我們讀他的作品,如果不借助資料,很難把握作品的準確歷史背景,但這并不影響讀者認為那是好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的背景是1861年俄國宣布廢除農奴制,社會發生劇烈動蕩,普通人紛紛涌進彼得堡。但陀翁卻惜墨如金,只借助了一個次要人物的一句話點明背景,而且還是譯者加了注釋,才讓讀者了解的。從這兩位作家的創作看,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可以虛化、弱化。從事主題創作的作家,要牢記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