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紙的背面:一部古代社會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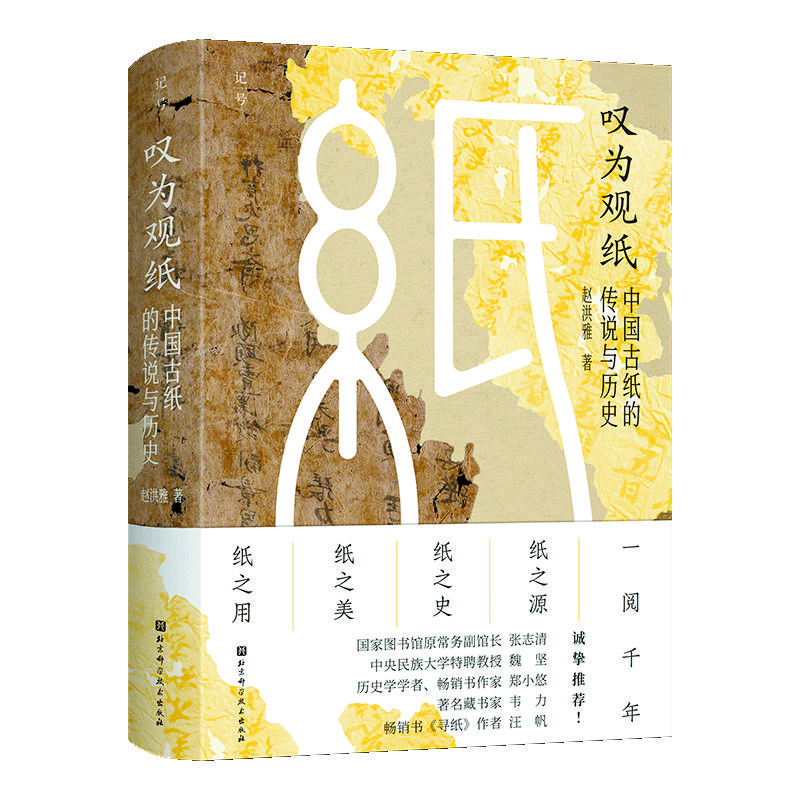
《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趙洪雅 著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出版
迄今為止,可能沒有哪一項人類的發明創造像紙一樣源遠流長,并深刻地改變和塑造了全人類的物質和精神世界。21世紀初,當人類意氣風發地站在信息技術時代的門口展望未來時,曾憧憬一個“無紙辦公室的神話”,然而,作為統治了人類千年的信息記錄載體,紙不僅沒有因為技術革新而退出現代社會,反而利用新技術改頭換面后在信息時代續寫著新的傳奇,持續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的生活。趙洪雅女史的新著《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以下簡稱《嘆為觀紙》)以淺白平易、典雅生動的文字,開啟了一段2000余年中國古紙起源、發展和普及的時光之旅,帶領讀者走進由紙構建和承載的古代社會文化生活。
紙壽千年
紙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書寫和記錄。中國5000多年的文明史,其中可考證的信史有3600多年。從繪有墨線地圖的西漢初年放馬灘紙算起,以紙作為記錄歷史信息的載體,已經有2000多年,占信史的二分之一強,并且紙作為載體記錄的歷史信息量遠大于甲骨金石竹帛等材料。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紙的發展和普及加速了中國文明的發展進程,紙這一物質載體使經驗和知識的累積與傳播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進行,并進一步促使新的經驗和知識產生,令華夏文明在古典時代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在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造紙術由于其產生時代早、對人類社會有巨大的影響力,當之無愧地坐上了古代技術發明的第一把交椅。造紙術的發源地是中國,這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事實,正如《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紙和造紙”詞條所說:“造紙術可追溯到約105年,中國的蔡倫用桑皮及漁網、破布、廢麻等韌皮纖維造成紙張。”這個詞條的描述還表明,蔡倫是造紙術的關鍵性人物——這已是世界公認的常識,但它巧妙地繞開了一個聚訟已久、筆墨官司不斷的問題,即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者還是改良者?
認為造紙術并非始于蔡倫的觀點,宋代已有人提出,隨著20世紀初考古學的新發展,西漢古紙的不斷出土,這個問題混合著國家尊嚴的維護、民族自信的重建等諸多復雜因素,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話題。不同于一般的科學技術史著重理性的評述,《嘆為觀紙》在這個問題上用了大量細膩的筆墨,詳細引述了黃文弼、李憲之、鄭天挺、徐炳昶等學者的日記和回憶錄,反映了在民族衰弱、文化淪喪之際,這些前輩學者與外國人一起科學考察時的復雜情感,讓我們對這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論爭抱有一份歷史的同情和敬意。
有關造紙術的歷史爭論隨著國家強大、民族復興而歸于平靜,國際學界早已公認造紙術和紙是中國先民智慧的結晶。如今華夏子孫繼承了這一對整個人類文明具有重要意義的寶貴財富,并正在現代社會繼續延續它的壽命,書寫下一個千年的輝煌。
“物紙”生活
《嘆為觀紙》“觀”的不僅是作為物質存在的“紙”的起源、發展和普及歷程,更是由紙反映出來的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嘆”的也不僅是紙作為一項人造物品的豐富多姿的形態,更是紙的背后所反映出的瑰麗多彩的個人精神世界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這部著作不僅像一般的科學技術史敘述了紙的制作工藝,以及紙的原料由麻到藤到樹皮再到竹的過程,更超越了一般科學技術史的敘述框架,融入物質文化研究的視角,從“物紙”進入了古代的社會文化生活研究。
法國歷史學家第二代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曾通過小麥、稻米、玉米、煙草等日常瑣碎物品來研究物質文明結構,指出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吃飯、穿衣、居住永遠不是一個毫不相關的問題。受其影響,物質文化研究試圖從“日用而不察”的物品中挖掘能揭示文化信息的蛛絲馬跡。澳大利亞物質文化研究學者伊恩·伍德沃德認為,物可以執行“社會事務”,表達出一種社會身份,具有建構社會意義的能力。紙就是一項“日用而不察”的物品,并且它貫穿不同社會階層,呈現出“具有代人行事的能力”的“物”之特點。
例如,制作名刺是紙的一種用途,交換名刺是一種社會活動。《嘆為觀紙》在敘述紙代替簡牘成為名刺主要材料時指出,交換名刺本來只是作為人際互通姓名的慣用之禮,但因與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門第觀念、科舉仕途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極為繁復的規矩。名刺的形制變化反映的是社會關系結構的變化。書中以明代經歷四朝的郎瑛《刺紙》為例,臚列刺紙從“白錄紙”“蘇箋”到“白錄羅紋箋”“大紅銷金紙”“綿紙”的演變,貶斥了“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的奢靡之風。
物質文化研究有一個觀點認為,人們需要借助物來了解自我、表現自我。《嘆為觀紙》描繪了一個繁花錦簇的紙的世界,這個紙的世界也是古人的精神生活世界。西晉傅咸《紙賦》所贊嘆的“廉方有則,體潔性貞”“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等紙的特性,其實是人通過紙的物質屬性,認識到人的方正貞潔的高尚品質和忍辱負重的人生態度。通過紙及其制品來認識古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關系,這一角度貫穿《嘆為觀紙》的始終,使這部著作不同于一般的科學技術史,更具有人文的溫情。
“紙”來“紙”往
透過一個具體的日常事物的歷史研究,去觀照人類文化交流史,《嘆為觀紙》的作者并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20世紀最后20年,季羨林完成了“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糖史》,希望通過對“糖這樣一個微末不足道的日用食品”的歷史研究,揭露出其中隱藏著的人類文化交流史,而這個歷史事實是人們通常視而不見的。《嘆為觀紙》以走向世界作結,正呼應了季羨林的《糖史》。
該書在點染造紙術西進過程中指出,在阿拉伯文學家賈希茲筆下的“隋尼婭特”很可能是指“中國女人”,她們或因戰亂被擄去,從收購破布開始,把中國造紙術帶到異國。而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婦女群體捐布造紙,被稱為“自由女神”。這兩個跨越時空的婦女形象,由“破布”連接到一起,而這些被人們視若敝履的破衣碎布,把人類文明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人類文明的進步不是某一個地區的人群獨立推進的,而是在交流、交往、交融和解決沖突中前進的,正如季羨林所希望的,從一件小事情上,“讓人們感覺到實在應該有更多的同呼吸共命運的意識,有更多的互相幫助互相依存的意識,從而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解決一些威脅著人類全體的問題”。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人類再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祈禱紙在世界上來往流動、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景象能夠再次出現。
令人感到意猶未盡的是,書中只勾勒了紙和造紙術向東、西兩個方向的傳播和發展線索,點狀式展現了“渡來人”(古倭國對中國、朝鮮等亞洲大陸移民的稱呼)、戰爭、“破布收集者”等幾個歷史片段。我們期待作者將來能不吝筆墨,繼續把紙背后的東西文化交流史鋪展開來。
“紙”向未來
回望古紙的歷史,我們看到了古人的衣食住行、行走坐臥,徜徉在文人的風雅和市民的日常中,也觀見人性的純良與貪婪。紙構建起豐盈的物質世界,也承載了精彩的精神生活。紙以其千年之壽延續了一個人短暫的生命,至今我們仍能與千年前在樓蘭邊關戍守的基層小吏張超濟共鳴,正是紙“寫情于萬里,精思于一隅”的真實反映。
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在現代信息社會,紙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信息載體。阿比蓋爾·J.塞倫和理查德·H.R.哈珀在21世紀初電腦和互聯網才開始普及時就指出,電腦和互聯網使得信息的獲取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是以數字渠道獲取的信息的最佳閱覽模式依然是紙張。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他們的觀點得到了驗證:電子設備雖然充斥了我們的生活學習,但無紙化的世界仍未到來,新技術的引入并沒有淘汰紙張,反而增加了它的使用,或者改變了它的使用方式,甚至電子設備也在想方設法實現紙質的視覺效果。此外,數字存儲設備易受溫度濕度的影響而導致數據丟失,理論上其物理壽命只有百年,且信息讀取受到設備限制,種種因素,使得紙仍是人類保存信息不可取代的載體。
紙和造紙術幾乎顛覆性地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承載方式,進而影響到人們的精神信仰、經濟制度、審美意趣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沒有過去時,只有將來時,正如《嘆為觀紙》最后一句所說:“紙張這一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也定會繼續見證人類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