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跑過去,就是新天地” ——訪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家祁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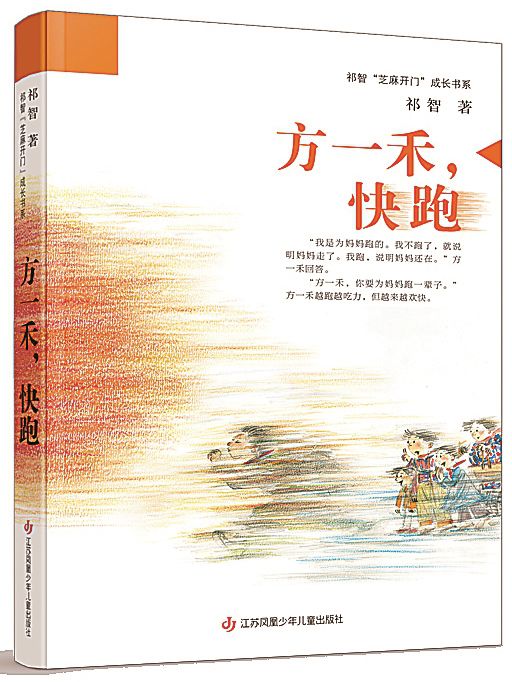
《方一禾,快跑》,祁智著,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2024年4月
記 者:祁老師好,祝賀您的作品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方一禾,快跑》面對的是兒童文學很難處理的“疾病”和“死亡”主題。您認為,兒童文學作家該如何向孩子描述這類主題?
祁 智:感謝您的祝賀。我借此機會,感謝關注《方一禾,快跑》的師友,感謝讀者朋友。
面對如同花蕾、如同朝陽的生命,兒童文學處理“疾病”和“死亡”的主題確實難度不小。但是,不涉及這一主題,兒童文學有“缺項”;這一主題涉及得不妥當,兒童文學有“缺失”。
我創作《方一禾,快跑》堅持兩點。第一點,不刻意去涉及“疾病”和“死亡”的主題,而是當成寫作的日常。《方一禾,快跑》中,爸爸在一個中午去世,雖然“突然”,但是我把這一情節處理成一天生活的一部分,而媽媽生病在床更是一家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以為,生活如此,“責任”不在我。第二點,創作之前,我用30年的時間在思考,我涉及這一主題到底想要表達什么,是對“疾病”的同情、對“死亡”的恐懼?顯然不是。在“疾病”面前,同情是淺顯的;在“死亡”面前,恐懼是簡單的。那么,是想表達方一禾的自強不息、全社會對方一禾的愛心援助?更不是——如果這樣寫,可能是通訊報道,但肯定不是小說。小說應該進入更深刻、更復雜,又更明朗、更宏大的層面。爸爸的“死”、媽媽的“病”、方一禾的“跑”、大家的“幫”,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以為,生命如此,“責任”在我。
記 者:您在后記《生命如歌》中寫道,這部作品的創作靈感來源于30年前在北方的一次采訪,“方一禾”的原型是一位父親去世、母親患病、年僅八九歲的小女孩。您為何會選擇在創作的時候,把敘事的主人公改為男孩?
祁 智:30年前的一個早春,我去青島采訪一個叫杜瑤瑤的小女孩。她的爸爸突然去世,媽媽重病臥床。她沒有時間悲傷,因為家庭需要她支撐。她每天早上狂奔去醫院拿鹽水瓶,再狂奔回家喂媽媽吃飯、給媽媽輸液,然后狂奔去學校。我問她累不累,她說:“不累。我跑,說明媽媽還在。哪天不要我跑了,說明我媽媽沒了。我要為媽媽跑一輩子!”我剎那間淚水奔涌,在蒙眬中看到了我曾經的狂奔。
小時候,我媽媽經常被救護車拉走搶救。媽媽回來的第二天,我第一節課下課,要狂奔到街上的肉案拿一對豬腰子,狂奔回家交給外婆,再狂奔回學校。我不知道什么是“速度”,只知道耳邊跑出風聲就是最快。我每天都要跑到最快。結果是我能在上課鈴響之前進校門,后果是我蹲在教室的墻邊口吐白沫。我吐的時候內心充滿了喜悅和幸福:我是為媽媽跑的。那一刻,我又非常害怕,害怕哪天不再需要我狂奔。我想:媽媽,我愿意為你跑一輩子。
小說的主人公一般都有原型。我采訪杜瑤瑤后寫了長篇報道《微笑著面對生活》。在《方一禾,快跑》中,我把“方一禾”寫成男孩子,是想盡可能把小說主人公與原型區別開來。作家優先考慮的是怎樣便于創作,我在1997年就寫過短篇小說《狂奔》,主人公“李祥”就是男孩子。何況“方一禾”也有我的影子。其實,“方一禾”有許多人的影子——我們多少人因為各種原因奔跑過,甚至還在奔跑中,耳邊呼呼生風。
記 者:《方一禾,快跑》中用宋體和楷體兩種字體對不同內容加以區分,宋體是當下正在發生的故事,楷體是在當下的敘事插入回憶、心理活動、對話或其他場景,讓人聯想起威廉·福克納等作家的作品。這種“插敘”的設計是出于什么考慮?
祁 智:我交給出版社的《方一禾,快跑》都是宋體。編輯老師經驗豐富,他們提出來,如果都是宋體,不停地出現的時空轉換,會給讀者尤其是小讀者帶來閱讀的障礙,建議把“當下”用宋體,把“過往”用楷體區別。我非常贊同并且感激這一技術處理。
福克納的小說運用了意識流手法和多角度敘事,我曾經喜歡過。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如果福克納的小說也按《方一禾,快跑》這種方法處理,可能閱讀得要順暢一些。我說,福克納不會答應,因為跳躍、混亂、糾纏、拼湊、模糊應該是他想要的。
記 者:作品的題目特別生動,充滿兒童趣味和游戲感。原本只是方一禾和同班同學追逐打鬧的時候,出自班長馬斯原之口的一句話:“方一禾,你快跑,我掩護。”但用作標題以后,又具有了新的引申含義。讓人不禁思考是誰在催促方一禾快跑,他因何而跑,又將跑向何處?能不能請您談談是如何設計作品標題的?
祁 智:我有四點考慮。第一點,“方一禾”確實在快跑。我見過杜瑤瑤有三種快跑的姿勢:早上狂奔去醫院拿鹽水瓶,雙臂前后擺動;拎鹽水瓶狂奔回家,雙臂低垂;狂奔去學校,一手劃動,一手按住背上跳躍的書包。不僅如此,我記憶里還有耳邊的風聲。讓情節有畫面感,是我小說的追求。第二點,正如您所說,“讓人不禁思考是誰在催促方一禾快跑,他因何而跑,又將跑向何處”,有懸念——我以為,兒童文學應該調動一切因素,激發起讀者的閱讀興趣,所以“懸念”也是我的追求。第三點,“方一禾,快跑”朝氣蓬勃,既有動感也有感染力,在沉重中有輕揚、在灰色中有亮光。不少讀者朋友告訴我,讀到最后,會情不自禁地喊“方一禾,快跑”,甚至不希望他停下來。第四點,我們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不測、不順是常態,唯一的辦法就是“快跑”。快跑過去,就是新天地。新的生活永遠需要我們風雨兼程。
記 者:故事里有很多讓人印象深刻的“次要角色”,有天真爛漫的小小少年羅小盼、程璐璐、謝菲、馬斯原等同齡人,還有如韓老師、岳老師、薛老師、公交司機馬叔叔、社區王阿姨等成年人。尤其讓人感動的部分是王阿姨建的微信群里的一條條信息:“方一禾起床了。方一禾點煤氣灶了。方一禾門沒關跑出去了……”方一禾不是一個人“負重前行”,有很多關心他的人,在他的背后默默無聞地付出。而且,直至故事結尾,方一禾都沒有發現這些“無名英雄”。您為何選擇把他人的付出,寫在主人公成長的背后?
祁 智:30年前,人們對“弱勢”個人或群體的關心比較簡單、直接,甚至有些“粗暴”,不怎么在乎他們的接受,考慮更多的是怎么給予。后來,人們的關心逐漸變得得體、合適,甚至不留痕跡,充分考慮到接受者的尊嚴。這是時代進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具體表現。當年的杜瑤瑤雖然想獨自擔當、不想麻煩別人,但事實是,離開了眾人的幫助,她舉步維艱。我當年每次都能在上課鈴響之前狂奔進校門,后來才知道,哪里是我準時,是校長讓門房師傅等我進了校園才敲響預備鈴。不僅如此,時代進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具體表現還在于,人們不再以為對“弱勢”個人或群體的關心是單向的給予,人們在給予中也獲得了力量、溫暖和升華。這本書的背景是社會、時代,是悲憫、博大。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這么說:我們互為主角,也互為背景。
記 者:以成年人的心態來讀這本兒童小說,會感到特別沉重,直至故事的結尾,方一禾感到“從來沒有這樣輕松過”,在酣夢中踏上了莫比烏斯帶。我聽過一種說法,如果某個人站在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帶的表面上沿著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走下去,就永遠不會停下來。這種拓撲學的概念對應的是“無窮”,可以解讀為主人公的苦難永無止境,也可以解讀為生活和希望永無止境。故事結尾的藝術處理背后有何深意?
祁 智:莫比烏斯帶是“神來之筆”。故事原本是,媽媽睡覺前在孩子手腕拴了一個鈴鐺,繩子拉在自己手上。媽媽需要孩子的幫助時就拉響鈴鐺,鈴鐺不響孩子就安心睡覺。但是我總覺得這個結尾弱了,這個結尾甚至是我一直不能動筆的原因之一。后來,我給一位數學特級教師打電話,希望聽聽數學課。老師很快安排了“學科+”的數學公開課。我聽到一位老師講“莫比烏斯帶”,立刻想到了在媽媽和孩子之間的那根繩子,想到了方一禾在夜深人靜中對爸爸的思念,熱淚盈眶。當天晚上,我寫了一章,請老師看看有沒有專業問題。老師說,雖然不知道整部小說是什么內容,但看了這一章有“說不出的難受和欣慰”。我知道“成了”。我在定稿的時候又審視了“莫比烏斯帶”的結尾,我看到了“相逢”,當然也看到了“無窮”。生活之路難免曲折坎坷,但是生命必定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記 者:您曾在中學當過多年老師,后來又在出版社從事童書出版工作。文學專業的學術訓練、語文教育的實踐經驗和童書出版的現場觀察,都為您“兒童本位”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您認為,青年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要怎樣才能貼近兒童生活?
祁 智:不要以為寫到了兒童和動物,就是兒童文學。青年兒童文學作家要發自內心地熱愛生活、敬畏文學、崇尚經典、深入孩子、永葆童心、感謝讀者,做好素材儲備、精神準備。作品永遠不注水稀釋、不胡編亂造、不嘩眾取寵、不低級趣味、不潦草急就。我們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