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讀一本書就像為自己重新書寫它
無論是對安吉拉·卡特的作品有深入了解還是僅稍有涉獵的讀者,都不難注意到她對“改寫”或“重述”的興趣,無論是以《染血之室》為代表的對經(jīng)典童話文本的改寫,非典型女性主義的文化批評專著《薩德式女人》,還是其短篇、長篇小說中豐富的互文——從《簡·愛》、波德萊爾的“黑維納斯”組詩、莎劇、圣經(jīng)典故,到民間傳說、好萊塢電影明星、歷史上的罪案……在這些充滿了改寫、重述沖動的故事中,卡特為我們生動地展示了她本人以及她的作品所依存的那個年代的時代精神、感受方式——質(zhì)疑一切,拆解一切,重新審視從每天的日常生活到長久以來的文化規(guī)范等一切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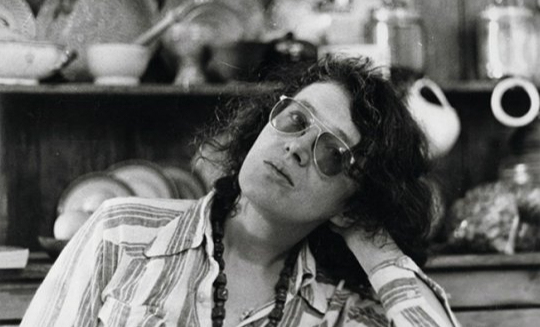
安吉拉·卡特
有時候,這會讓我們不禁好奇,這位信手拈來、旁征博引卻又充滿不敬的作家會是一位怎樣的讀者?她是怎么“閱讀”的?
好在,卡特從不吝惜與讀者分享她的真知灼見。卡特一生除了創(chuàng)作了九部長篇小說、大量短篇小說,并翻譯、整理編輯了許多童話和民間故事以外,同時曾長期撰寫社會評論、文化批評與書評。這些評論與書評在不同時期均曾集結(jié)成冊,包括《毫不神圣》(Nothing Sacred),《刪除咒罵》(Expletives Deleted)以及在卡特去世后出版的《即刻行動》(Shaking a Leg)。
在卡特看來,“讀一本書就像為自己重寫它。你在讀小說或任何可讀的東西時,你總是帶著你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經(jīng)歷去讀。你帶著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一方面,她對一些經(jīng)典文本如查爾斯·佩羅、格林兄弟編輯的童話集、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的評論幾乎與她的童話改寫作品同樣精彩。另一方面,基于某種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立場,作為讀者的卡特慣于將一切文本視作可批評的對象——“所有的書都包含敘事,連烹飪書和汽車維修手冊也一樣。敘事是用語言寫下的,卻是在時間中形成的。”對卡特來說,一切在時間中形成的敘事,都具有文化建構(gòu)的含義,因此具有“可讀性”。而由于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仍處處為父權(quán)制與資本主義所結(jié)構(gòu),這些文化建構(gòu)往往遍布裂隙、充滿可疑,因此亟待重新審視。
在南京大學出版社最新引進出版的這本《刪除咒罵》中,卡特將她在十五年間寫作的大量書評“根據(jù)不同的興趣點劃分為幾個部分”,其中包括英國、美國的當代文學,“食物和食物的符號學”,好萊塢與美國文化,等等。盡管從卡特的評論文章中,我們不難辨認出二十世紀那些人盡皆知的批評流派的術(shù)語與解讀方法,精神分析(盡管她更多時候是借用其術(shù)語來批評庸俗的精神分析解讀),結(jié)構(gòu)主義與后結(jié)構(gòu)主義對“敘事”的理解,意識形態(tài)分析,女性主義……但卡特的書評卻從不遵從特定的文學評論模式,同時也與“經(jīng)典的”“主流的”文學趣味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在書評中保持著一貫的對樂趣、令人愉悅的事物的歌頌,對差異性(無論是來自種族,性別抑或是階級)的關(guān)注,以及某種獨特的孕育自其成長環(huán)境的文化直覺——有時候,這會讓她的評論文字在語言上顯得跳躍,時而直白、迅速、一針見血,時而纏繞、迂回。
正如卡特自己所言,她是“一個先進、高度工業(yè)化、后帝國主義的衰落國家的純粹產(chǎn)物”。她的趣味、思想與她所生活的時代和社會環(huán)境的密不可分——二戰(zhàn)末期約克郡小鎮(zhèn)的生活、戰(zhàn)后福利國家及其教育福利、六七十年代的激進與反叛、隨后十年的探索和幻滅,然后是英國撒切爾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而另一方面,卡特自身的人生選擇與經(jīng)歷,也成就了她獨特的視野與風格。關(guān)于卡特的生平,其好友兼早期研究者洛娜·塞奇(Lorna Sage)有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社會流動的背景,青少年時期的厭食癥,在各種偉大傳統(tǒng)的廢墟中接受教育并自我教育,早婚和離婚,角色扮演和形象轉(zhuǎn)換,旅行,選擇一個比自己年輕得多的男人,四十歲時的生育——這是一個走鋼絲的人的故事。這一切都發(fā)生在‘邊緣,無人區(qū)’,在過去的信念留下的碎片中。到最后,她的生活或多或少像手套一樣適合她,但那是因為她將它們經(jīng)由試驗、錯位和拼貼放在一起,所有的順序都是(傳統(tǒng)上)錯誤的。她關(guān)于疏離與陌生化的才能來自于她對她的生活環(huán)境和時代跡象的極端反應。”
沒有什么是“自然的”,沒有什么是可以自外于文化建構(gòu)的。這一切似乎給予了卡特一種不依附于任何“主義”的文化直覺和批判沖動,以至于生活本身與小說創(chuàng)作、閱讀與寫作之間不再有完全確定的邊界。
在《刪除咒罵》中,對《愛爾蘭民間故事》、《阿拉伯民間故事》、《格林兄弟的德國傳說》甚至《簡·愛》的評論,反映了卡特在70年代中后期對童話與民間傳說持續(xù)的興趣。以翻譯17世紀法國佩羅童話集為開端,卡特的創(chuàng)作與童話、民間傳說從此密不可分。對卡特來說,佩羅的童話是“刻意偽裝成經(jīng)驗政治的寓言”,而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話也大多都為成年世界而設,旨在“使用童話的自由慣例來投射一個充滿恐怖和恐懼的私人世界”——這些故事從口頭流傳到進入童話故事集的那一刻,就被“體制化”了,被置入了關(guān)于階級、性別的社會規(guī)范與“教學議程”,其中一些最經(jīng)典的文本甚至成為了早期資產(chǎn)階級神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民間傳說對卡特來說則意味著一種更為野蠻生長、充滿生命力與可能性的存在。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民間傳說常常顯得怪異、矛盾、缺乏明確的意義,也沒有童話中幸福美滿的結(jié)局。但別忘了,正是這些豐富而差異化的民間傳說來源,給予了卡特改寫童話的靈感,給予了我們將經(jīng)典童話“去神話化”的資源。在這些書評中,卡特提醒我們,民間傳說都如此緊密地與自己誕生的土地聯(lián)系在一起,是不同國家、地區(qū)人民歷史中不可替代的部分,它們?nèi)绱松鷦佣敛煌讌f(xié)的部分正是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環(huán)境的時代精神的化身。當然,卡特也沒有忘記提醒我們不必對此過分理想化:“民俗學研究的興起和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之間的關(guān)系很有趣,其中有些東西撩撥著我們的思想,讓人很不自在。”
而在幾篇關(guān)于“食物與食物的符號學”的書評中,卡特的敏銳與“毒舌”再次用于拆穿中上層階級驕矜的自我粉飾。當資源短缺、只求溫飽的時代記憶逐漸淡去,在選擇多樣的時代里,食物的選擇、搭配、烹飪具有了象征性的意義。在《<時尚>中的美食》一文中,卡特寫道:“作為記錄英格蘭中產(chǎn)上層及有志攀升中產(chǎn)上層的飲食和社會習俗變遷的一部通俗歷史,《<時尚>中的美食》相當成功,如果被解讀為關(guān)于時尚生活本質(zhì)的一種‘得償所愿’幻想的具體化,那就更好了。”在精神分析中,“得償所愿”常指通過夢境、神經(jīng)癥狀象征性地實現(xiàn)欲望。同樣的,這個術(shù)語也可以直接用于概括文學與藝術(shù)的某種功能——通過虛構(gòu)、敘事象征性實現(xiàn)欲望。而在“食物與食物的符號學”中,特定類型的中產(chǎn)階級的食譜與某種關(guān)于食物的“藝術(shù)”(注意,這也是一種敘事)則象征著中上層階級那令人艷羨的生活本身——關(guān)于飲食、時尚、服飾、家居等等一切的“品味”都可以隱含著一種階級意義上的區(qū)隔。在這里,卡特憑她那出色的文化直覺和一針見血的語言概括道:“這是現(xiàn)代童話的內(nèi)容。”
卡特對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的評論更是這部書評集中最為精彩的一篇。在卡特看來,《簡·愛》具有羅曼史敘事的經(jīng)典框架,同時融合了《藍胡子》和《美女與野獸》的這兩個古老童話的元素以及哥特文學的影響,這使得這部作品擁有了一種近似于傳說的特性——正是這一特征,使得它很容易被轉(zhuǎn)譯成其他媒介,擁有強勁的跨媒介的來世生命。同時,卡特富有洞見地指出,夏洛蒂·勃朗特具有精準設置階級背景和個人歷史的能力,她的女主角絕非僅僅是羅曼史與經(jīng)典童話的女主角,而是“漂泊無依的城市知識階層的先驅(qū)”——她并非為了婚姻或魔法來到桑菲爾德莊園,而是因為自己在報紙上登了一則求職廣告。那么我們的男主角,羅徹斯特先生呢?“他是簡的欲望的客體,更是簡的欲望的客體化。”由此,“《簡·愛》是關(guān)于這個女子的欲望,關(guān)于她怎樣學會為它定名的故事。為它定名,再馴服它”。這既是一份《簡·愛》的書評,也是一份對《染血之室與其他故事》的自我陳述。
這就是安吉拉·卡特的書評,在閱讀的同時進行改寫——既是“舊瓶裝新酒”,也是某種“言語煉金術(shù)”:理解,拆解,重新建構(gòu)。
在《簡·愛》書評的最后,卡特突然收起了鋒芒,嘆息夏洛蒂·勃朗特的英年早逝。在今天,喜愛卡特及其作品的讀者也許會有同樣的感嘆,也許會更加禁不住好奇卡特如果活到了21世紀乃至今天,又會寫出怎樣充滿勇氣、洞見和不敬的文字。但只要我們?nèi)阅軓目ㄌ氐奈淖种屑橙○B(yǎng)分,并借此重新塑造我們的感知力,在自己的生活領域中一點一點地培養(yǎng)起批判的勇氣與力量,也許我們就能更加接近卡特及其作品所指引的二十世紀的珍貴遺產(chǎn):“語言是力量,是生命,是文化的工具,是統(tǒng)治和解放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