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讓眉新作《王維十五日談》出版 感受“淡人”王維 并被他療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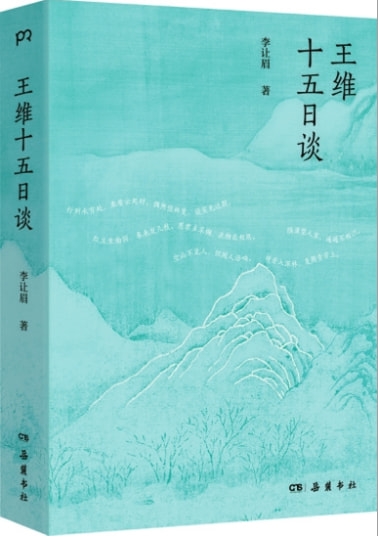

“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是李讓眉的微信簽名,她想以王維的這句詩表達自己的心境。“雖然‘我心’與‘清川’間沒有必然的關聯,但是二者的狀態又無意形成了一組平和的呼應。我覺得我們需要像王維一樣,和天地建立起這樣的關系。”
李讓眉是青年詩人、作家、詩詞研究者,著有《所思不遠:清代詩詞家生平品述》《李商隱十五日談》《香塵滅:宋詞與宋人》。據李讓眉介紹,“十五日談”系列的寫作初衷是以詩人的身份去面對另一位詩人,用平視的視角與一位投契的古人展開一場深入而有詩性的交流。近日,她的新作《王維十五日談》出版,李讓眉細述了王維的生平、時代、親交、情感、宗教、繪畫、音樂、詩藝,還原王維的人生境遇與精神世界,破除既有標簽。秋末,李讓眉在北京圖書大廈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除了沉浸在王維的詩歌世界之中,李讓眉也暢談了自己創作古詩詞的心路歷程。
自六歲嘗試寫詩 創作指引著我去賞析和研究古詩詞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同大多數孩子的開蒙方式一樣,兒時的李讓眉在母親的陪伴下背誦古詩詞,完成了對詩的第一次邂逅。
至六歲時,源于心中一次偶然的沖動,李讓眉依樣畫葫蘆地寫出了一首童謠般的七絕詩,被父母貼上了“會寫詩”的標簽。“孩子們都不缺創作沖動,他們見到很多事物時都會想去表達,并嘗試用不同的方式去講述自己,而我恰好選擇了古詩——一種和日常生活有些距離的表達方式。”李讓眉解釋道。在父母的鼓勵下,她一直用詩書寫生活。至十歲,李讓眉跟隨家人前往北京師范大學的老師家中拜訪,這位老師對她的詩進行了評點,并給她講了些詩詞的格律要求,此后,李讓眉認為自己“寫出來的東西便慢慢有些像詩了”。
不過,一直與詩打交道的李讓眉,大學卻選擇了理科,這一選擇只因與同學的一次賭氣。當時,高中要分文理班的時候,李讓眉的同學都認為她一定會選擇文科,“她文科強,如果學理科肯定不行”。李讓眉一聽便生了氣,“誰說我學不了理科”,于是報名了理科班,經過努力,也漸漸能名列前茅。到高考填報志愿時,才發覺理科生無法報考文學專業,于是她就讀了金融專業。
在大學期間,李讓眉沒有放棄過文學,在學校創立了詩社,還跨院擔任了人文學院的院刊主編。2007年,在大學接觸網絡之后,她看到有一大批網友仍在用古詩詞的形式表達內心,憶起當時網絡詩歌的創作,李讓眉稱自己趕上了當代最后一次文言詩歌的盛會。“在現當代文學史中,它通常被稱為‘網絡詩壇黃金十年’(注:2000年至2010年前后)。我開始進行一些詩學思考,比如我究竟是什么樣的詩人?我能寫出什么類型的詩?雖然當時沒有找到答案,但這是個可貴的過程。”
直至今日,李讓眉認為自己能夠堅持研究詩詞,與持續不斷的創作有著緊密關聯。“什么樣的表達是好的”“哪一次的表達與自己的感受最為匹配”“怎樣才能寫得更好”……這些問題在創作的過程中生發出來,讓李讓眉產生探索的向往。她開始從古人的詩詞中尋找答案,并嘗試進入“賞析”或“批評”的領域,站在創作者的立場去思考一首詩詞為什么好,如何“從自己的詩走向別人的詩”。
在這一過程中,李讓眉也慢慢對古代詩人祛魅,她解釋道:“帶著這樣的視角去讀詩詞,有時會覺得有些詩我也可以寫出來。詩人有自己的創作慣性,文學手感相近的詩人,會在某些瞬間感應到對方。所以有時看到一些詩人寫出的上一句,捂上后文我也大概能猜出他下一句的方向。當然,也有每次都猜不中的,比如李賀這種天才。但總而言之,創作的思維會為詩學批評與相關研究帶來新的方向,二者交疊,一步步拉著我往更深的領域探索。”
李讓眉的創作是隨時隨地的,有時看到一些生活中的畫面,想到一些字句,就會寫下來。比如她創作的《蝶戀花·通勤口占》就記錄了當代人地鐵通勤的畫面。“白月空天潛自駐,衢底終風,地鐵過無數。諸我錯肩門一阻,晨昏心氣春冬絮。漂泊浮身塵里語,幻碼方生,打閘人潮去。遮面已迷回望處,上樓去會蒼生苦。”詩人胡桑評價道:“當代打工人的通勤體驗在‘詞’這一古典體式中被裁剪、形塑、安放,同時‘詞’的形式潛能也得以激活。比如‘地鐵’‘幻碼’‘打閘’諸多語匯的嵌入,分明是在邀約當代人的生活進入古典的書寫形式。”
以詩識人 與我金融分析的工作有相似性
2017年,初為人母的李讓眉感受到時間的緊迫,常覺焦慮,“和同道交流的時間少了,很多想法來不及留下來”。
工作的忙碌與母職的辛苦,促使李讓眉嘗試將自己的思考落實在寫作中。她認為單純的無功利化寫作給自己帶來了很多新的靈感,同時,寫作本身也可以有“自我”的存在感。寫詩,李讓眉利用的是生活中的碎片時間,而研究性質的大部頭文章,李讓眉則會在黑夜里書寫,孩子們入睡后,才是獨屬于她的時間。對她而言,寫作是更恒久的快樂之源,在創作的過程中可以把一些稍縱即逝的想法落實,也會引導她更開闊、更積極地看待生活。
每研究一位詩人,李讓眉都會盡可能廣泛地讀詩人的作品,甚至是去讀全集。“當讀的詩足夠多,我們就會發現詩人在處理同類意象時,會有自己的文學慣性。但是,如果他某次創作脫離了這種慣性,或者忽然選擇用一種不常見的手法,我便會立刻察覺到其中的異常。”這一研究技法,可見于她創作的《所思不遠:清代詩詞家生平品述》《李商隱十五日談》《香塵滅:宋詞與宋人》。她從詩人的創作邏輯入手,一點點找到他們不愿說出的話,并沿著這個方向,去還原詩人的面貌和精神世界。
關于她從詩中找到研究的“線頭”,她進一步解釋道:“還有一種詩人習慣將一組同樣的意象放在一起,盡管他不一定講明這首詩在針對哪一件事,但當我們看到熟悉的一組意象團出現,這段描寫很有可能就是對同一件事的復現。因為這是記憶的邏輯,而不是單純的創作邏輯。比如李商隱的‘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是一種單純的文學構建,他第二次再去表達類似的情感,就不會把這些意象組織在同一個句子;但如果是針對記憶的創作,他則會在意象上反復地扣合。我就在李商隱的很多‘無題詩’中找到了這種回響。同時,他在不同時期的創作對某種意象團都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和表達尺度,從中又可以看到他在某件事情中的情感變化的脈絡,我們由此可以有更多的發現。”
不論是以詩識人,還是以詩證史,李讓眉認為這一研究路徑與她的日常工作有相似性。她的日常工作是金融分析,面對需要研判的公司時,也要通過大量的閱讀去熟悉對方的敘事慣性,針對獲取的數據和事實進行系統分析,后期逐步將分析過程形成結論,再落實到自己供職單位的投資偏好中。
“這一過程與我分析詩歌的過程是類似的。一方面要有前期充足的準備,另一方面要有后期嚴密的分析。同時,我要把對方自洽或不自洽的東西梳理出來。只不過,在研究詩詞時,我沒有辦法對詩人進行訪談,只能依托他作品中留下的蛛絲馬跡進行分析。”李讓眉講道。
“淡人”王維并不淡漠 他重情義也重道德
2022年,王維成為李讓眉想要書寫的詩人。她開始用閑暇時光閱讀王維全集,王維的詩讓她找到了一種安放感,甚至起到了療愈的作用。
當李讓眉更深入了解王維,去探尋他的經歷時,她發覺“王維似乎深不見底”,而他的詩具有一種“敘事者淡出”的特性。在李讓眉看來,王維本質上不是會為某個事件寫詩的人,相較于敘事和說理,他注重的是當下的感受,有些表達也就不完全遵循語言的邏輯,“生命感受對他來說是高于語言的”。因此,在寫王維時,李讓眉有著完全不同的寫作狀態。“研究王維不能用我剛剛提到的方式去做,因為他的詩不是對事件的復盤,傳導鏈是散碎的,所以無法用以詩證史的方法。他啟發我跳出詩去看詩,在這個過程中,我獲益很多。”
李讓眉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一句為例,她認為“不見人”恰如現代攝影師常用的長曝光,當曝光時間拉得足夠長,每個時點的光不斷疊加,最終會令出現過的所有人影全部虛化消失,在無限的時間面前他們都是“空”的;但同時,王維會提醒大家仍有“人語響”,他們也都真的存在過,這是一種空與有的辯證。“這種寫法的妙處并不在于詩學技巧,而來自他被佛教塑造過的世界觀。這也就讓我們這些試圖通過技術接近他的人只好望洋興嘆了。”
在《王維十五日談》中,李讓眉在“第一日”便提出了世人對王維的誤解。“讀詩時,我們要始終記得,王維是個擅長自我療愈的詩人,這意味著他本身很容易受到傷害。他的詩作,也正是在失序中追尋平衡的產物。”李讓眉講述了王維的生平,比如王維作為家中長子,年少時便要盡最大努力去謀求功名,以此撐起整個家庭,幫助弟弟們在長安立足。因此,他當時的處境不允許自己視功名如云煙,也不論自己是否愿意,王維都必須在各個方面努力學習,以便融入上流社會。在王維的詩集中,李讓眉讀到“獨在異鄉為異客”時,常感心疼,此詩下的注腳為“年十七”,而詩中的“每逢”則表明這不是王維第一次在異鄉獨自過節。李讓眉寫道:“人們常嘆服于王維在上流社交圈中展現出的交際能力,也就往往不會設想一個中級官僚家庭出身的十幾歲的孩子要經歷怎樣的努力,才能如此從容地游走周旋于長安眾多名流之中。事實上,王維后來的仕途是配不起他年少時的聲名的……”
對于大家常給王維貼上“淡人”“佛系”“情感淡漠”等標簽,或是常提到他“半官半隱”“從未給妻子寫情詩”等事,在李讓眉看來,王維并不像他的詩學人格那樣淡漠,相反他是一個重情義也重道德的人。“他深愛母親與弟弟妹妹,這都有傳世文本證明,而三十歲喪偶無嗣卻終身不再續娶,本身已是比文本更長久的表白。王維很少為痛楚哀鳴,但他一直在忠實地用詩記錄每一場失去后的自我痊愈過程。”
學習古琴和繪畫 在動態中走進王維的藝術世界
王維能讓李讓眉“跳出詩去看詩”,不僅是因為王維在心靈層面給了李讓眉諸多慰藉,而且王維用多元的藝術探索啟發著她的許多思考。因此,在書寫王維時,她也希望讀者能感受到王維的寧靜,并被他療愈。
2024年9月,在寫完“王維的藝術世界:音樂”一章之后,李讓眉開始對樂律學感興趣,尤其看到王維在中晚年時開始彈奏古琴,“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她很好奇王維后期選擇的古琴與他早年擅彈琵琶到底有何區別,于是報名學習了古琴,直至今年六月在古琴初級班畢業。
本來就會彈琵琶的李讓眉在學習古琴之后,發現了兩種樂器截然不同的風格。琵琶的旋律主要通過高頻觸弦的彈音去實現,“上一個音還未徹底消散,下一個音就立刻跟上來了”,因為指法繁復,表現力強,琵琶對余音應用不多,它不愿放棄右手,如古琴那樣有耐心地只靠左手去做線形表達。提及古琴的彈奏方法,李讓眉用雙手在桌面上演示著,她用右手彈了一個音之后便停止,左手開始在琴弦上挪移,處理著主音在消散過程中的余音,“古琴的核心美感在余音,手接觸琴弦之后,直到琴弦震動徹底消亡,古琴主要的表達都保留在這一過程中。”
在學習古琴的過程中,李讓眉不單對王維有了新感受,也對“詞”有了不同的感知。比如讀過《鳳凰臺上憶吹簫》的琴譜后,她開始明白李清照在《鳳凰臺上憶吹簫·香冷金猊》中的“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一句中的襯字的考究。“我也寫詞,但之前我會認為其中的‘念’只不過是一個領字,它可以被替換成‘憶’‘恨’‘記’等動詞,也并不影響后面‘武陵人遠,煙鎖秦樓’的句意。可是,當彈奏演唱時,我發現‘念’字與‘武陵人遠’是有音韻呼應的,如果能與‘遠’字用同一韻,演唱效果會好得多。盡管琴歌中不會對此有明確要求,詞譜也沒有強調,沒有人會意識到這里的呼應關系,但是當詞作回到音樂里,我們會發現原來李清照會把這樣的細節都照顧得如此講究。比如,我們如果把它改成‘恨’,就根本唱不順。”
《王維十五日談》的樂論部分,寫于李讓眉動念學琴前,這讓她稍顯遺憾,她坦言:“如換現在再去寫,或許會有更多的生發。不過寫作與寫作者,本就是這樣在遺憾中互相促進的。”
此外,李讓眉在去年還上了關于繪畫的網絡課程,以沒骨畫為主。“沒骨是工筆與寫意的中間態,所謂兼工帶寫,如果我們想了解文人畫,就要去了解它與書法的筆墨之間的關系——畢竟王維是后人認定的文人畫鼻祖。”在這一課程中,令李讓眉感嘆的更多是顏料的質感。她為此專門查詢了許多關于古人如何制作顏料的資料,也專門去博物館實地感受了這些顏料的質地。
對古代顏料有了實際感知后,李讓眉再去讀王維的詩,才發現他對色彩的選擇非常講究。比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中的“白”,讓李讓眉感嘆王維寫得很妙,她解釋道:“白通常用來點綴,蛤粉很昂貴,也很難調和。平涂時,要用大量的水去稀釋珍珠白。因此,王維把這種氤氳的‘白’用在了‘江湖’,而非‘山林’,雖然日落以后,所有的東西都會失去色感,但是只有‘濕潤’的事物,才配得上‘白’。試著從藝術體驗看他的詩歌,才能感覺到其中的獨特。”
“當我們真的站在詩的面前,會意識到此時的王維不是一位操控語言的詩人,只是一位虔誠的畫師。”李讓眉認為,王維許多繪景名篇的創作思維都很接近于用繪畫的視角去欣賞造物主的作品,比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她以繪畫的視角賞析說:“當王維看到大漠上這一道孤煙時,他意識到‘直’對這個畫面是多么重要——稍偏一點,美學平衡會立刻打破;此外,若畫過雪月風竹,我們也會明白用留白托出的月亮若不夠‘圓’,會對整幅畫面產生怎樣的沖擊。”
李讓眉介紹,目前針對王維的研究,限于學科的理念而就詩論詩。比如詩歸于古典文學,音樂歸于樂律學,繪畫歸于美術史……“每個領域都有高手,但大部分研究成果沒能被聚攏、回歸到一個人身上。《王維十五日談》試圖在這個方向多走一步——看看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是怎樣通過調和不同門類藝術來確認自我的。”
供圖/浦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