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作家羅日新中篇小說《巴圖姆往事》登上《人民文學》 講述商戰(zhàn)傳奇故事
原標題:羅日新《巴圖姆往事》榮登《人民文學》
2025年11月3日,最新一期《人民文學》雜志刊登黃石籍作家羅日新的中篇小說《巴圖姆往事》。這是繼2022年長篇小說《鋼的城》出版后,羅日新又一部扎根生活、書寫黃石的文學力作走向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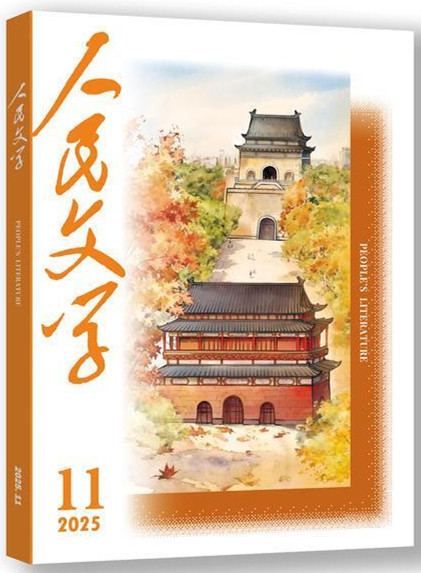
《人民文學》雜志隸屬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國第一份文學期刊,素有“文學國刊”之稱。毛澤東主席曾為《人民文學》的創(chuàng)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黃石作家羅日新
小說緣于真實事件
“我要通過他的眼睛和腳步,去踐行一個樸素的信念”
《巴圖姆往事》共3.1萬字,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講述黃石籍經(jīng)偵老羅化身推銷員,深入荒漠深處的中亞H國巴圖姆石油小鎮(zhèn),追捕詐騙犯,為家鄉(xiāng)的企業(yè)討回公道的故事。巴圖姆匯聚三教九流,環(huán)境嘈雜險惡,人情錯綜復雜,老羅與各種勢力斗智斗勇,撥筍抽繭般理清涉案人的背景關系,最終將案犯誘捕回國。小說節(jié)奏緊湊、邏輯嚴密、語言簡潔、人物形象鮮活,情節(jié)兼具懸疑小說的緊張感和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扎實性。
“在鋼材和石油行業(yè)泡了這么多年,我知道太多關于國際貿(mào)易、商戰(zhàn)騙局、人性貪婪和人間情義的故事。中國文學一直缺乏商業(yè)書寫,商場如戰(zhàn)場,這個領域是人性對決最激烈的地方。”接受黃石市融媒體中心記者采訪時,羅日新又談文學,又談經(jīng)歷。他介紹,2006年前后,國內(nèi)鋼材價格暴漲,不少企業(yè)急于在海外尋找礦山資源,這就給了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機。他一個朋友就曾遭遇過跨國詐騙,雖然最終追回部分損失,但過程艱難曲折。
“這個真實案例的尖銳深深刺痛了我。商人也是普通人,也會輕信,也會犯錯誤,當然也有道義良知。所以,當他們面對貪婪與欺騙的時候,也有一籌莫展的時刻。但在法律的幫助下,在家鄉(xiāng)人的情義加持下,更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出口。所以,商戰(zhàn)故事也是故鄉(xiāng)故事,也是情義故事。”羅日新很健談,他說這個故事如種子一般在他心里長了很多年,“我意識到,我必須寫下它。但思來想去,非虛構(gòu)不如虛構(gòu)更有寬度,更有力量,更能產(chǎn)生深刻的真實。于是,我找到了老羅這個角色,讓他作為臨江市經(jīng)偵支隊的支隊長參與其中。而且在商人羅和警察羅之間,我巧妙利用讀者容易對號入座的心理,設置了懸念,產(chǎn)生了一定的幽默效果。我其實想表達這樣一個樸素的信念:無論你是誰,無論你逃到哪里,只要你在中國的土地上欺騙了中國人,就必定有人跨越千山萬水,將你繩之以法。而生活再難,我們遇到再糟糕的事情,也不妨稍稍幽它一默。
歷時近三年藝術(shù)打磨
“寫作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自我懷疑與揚棄的過程”
“《巴圖姆往事》能夠在《人民文學》2025年第11期上和諸位名家文友的大作一起散發(fā)油墨香,我非常激動。這一刻,距離2023年元月那個寒冷的下午我寫下第一個字,已過去了兩年又十個月。”在談到小說的創(chuàng)作歷程時,羅日新說道。
他表示,從《鋼的城》的53萬字到《巴圖姆往事》的3.1萬字,看上去體量小了,但難度絲毫不減,艱苦也不會削減分毫。當然,世間所有的事都是如此,不歷苦痛難得甜蜜。而寫作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自我肯定又自我懷疑、不斷吸納又揚棄的過程。
“第一稿名字叫《中國公民》,有6萬余字,我近乎執(zhí)拗地完整復現(xiàn)了馬三強的行騙鏈條。我試圖用巨細靡遺的筆觸,構(gòu)建一個因果分明的世界。寫完放了幾個月后重讀,我發(fā)現(xiàn)了問題:對中篇小說來說,某部分過于臃腫一定會沖淡故事核心的緊張感。于是,第二稿變成了4萬字,名字也改成了《叫巴圖姆鎮(zhèn)的地方》。我開始嘗試加入敘述技巧,打碎完整鏈條,讓人物對話和心理活動也變成情節(jié)推進的方式。一個帶有推理懸疑色彩的故事,讀者需要的是即將引爆炸藥的引信燃燒過程,而不是一份詳細的炸藥成分分析報告。”羅日新介紹,到第三稿時,他再次舉起刪改的利斧,再次聚焦最核心的矛盾,小說的標題也沉淀為更具故事感與回憶感的《巴圖姆往事》,當然,因為巴圖姆之于讀者的陌生感,這個標題顯得樸素卻不普通。
“每一次修改,都不只是字數(shù)增減、題目變化那么簡單,它更像是一場漫長而孤獨的淬火,一遍遍將粗礪的礦石投入生活和藝術(shù)的熔爐,錘去雜質(zhì),最后用最妥帖的語言讓故事露出自己想象極限的光澤。”羅日新說,“實在改不下去的時候,我就大聲讀,逐字逐句讀給自己聽。如今,所有那些自我壓迫的日日夜夜,都化作了‘心有余悸的驚喜’。心有余悸,是深知創(chuàng)作之路艱險,驚喜,是慶幸自己最終沒有辜負這個好故事的原石。”
工業(yè)城市的文學回響
從工業(yè)史詩到法網(wǎng)正義,不變的是對故鄉(xiāng)的深情
羅日新的文學之路頗具傳奇色彩。他青年時期曾有作家夢,卻被父親喝止。大學畢業(yè)后他成了大冶鋼廠的技術(shù)員,從值班主任做到市場調(diào)研部長、鋼管公司副總經(jīng)理。1999年,35歲的他辭職下海,投身國際貿(mào)易。45歲開始嘗試寫小說,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尤其是長篇小說《鋼的城》的出版和廣受好評,更是給了他莫大的鼓舞。
“作家夢被我爸打斷之后,我就踏踏實實在鋼廠工作,那時候最大的夢想是當廠長;下海經(jīng)商后,我天天想的是如何把生意做大,做到全世界。”羅日新笑著說,“跟當廠長和做生意相比,寫作更難,因為文無第一,所以,開始寫作之后,我的夢想就變成了寫出更好的作品,讓自己每天進步一點點,每部作品進步一點點。”
目前為止,他兩部重要的作品,背景城市都是“臨江市”,也就是家鄉(xiāng)黃石,這個他寄托了最深感情的地方。他說:“沈從文說過,一個戰(zhàn)士,要么戰(zhàn)死沙場,要么回到故鄉(xiāng)。我覺得我的商業(yè)征戰(zhàn)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所幸沒有粉身碎骨,還取得了那么一點點的成就,那么,接下來將陪伴我余生的寫作,就要回到家鄉(xiāng)、回到黃石。這里的江河湖山、工廠街道、市井人情,都是我取之不盡的創(chuàng)作源泉,也是我的藝術(shù)之根。”羅日新說。
如今,羅日新已經(jīng)成為新大眾文藝的代表,他誠摯的書寫,換來的是讀者誠摯的回應。有網(wǎng)友留言:“羅日新的作品讓黃石這座城市有了文學的表達。《鋼的城》寫的是黃石的工業(yè)歷史,《巴圖姆往事》則展現(xiàn)了黃石人的精神氣質(zhì)。這種扎根故鄉(xiāng)、面向世界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讓人贊嘆。”
的確,《巴圖姆往事》的主要情節(jié)雖然發(fā)生在中亞荒漠,但“臨江市”作為主人公“老羅”的故鄉(xiāng)和精神依托,始終貫穿全文。小說第七章“背調(diào)”中,通過工頭老貴的回憶,還有對臨江市的生動描繪:“五十年代的蘇式老房子、鋼廠工人村、街口下棋的老工人……”這些細節(jié)都是黃石工業(yè)文化的真實寫照,羅日新寫的時候顯然也用情至深。
羅日新說:“我父親就是鋼廠的老職工,我在工廠生活區(qū)長大。那些蘇式老房子、街坊鄰居圍坐聊天的場景,都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此外,小說主人公老羅的性格也是黃石性格的代表,長江碼頭文化中“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執(zhí)著、工業(yè)城市培養(yǎng)出的務實、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都在老羅身上得到體現(xiàn)。而且,他的追逃,不僅要維護法律的尊嚴,更要守護臨江風清氣正的經(jīng)營環(huán)境和“工人村”平靜和諧的生活。正是這種種精神的匯聚,支撐他在異國他鄉(xiāng)克服重重困難,最終完成使命。
“黃石基因在我的精神血脈里,長江性格會永遠在我的故事里流淌。我會一部部寫下去,寫出家鄉(xiāng)所有的可敬可愛,寫出自己所有的激情。”羅日新說。是的,火熱的時代、沸騰的生活、寬廣博大的家鄉(xiāng),永無止境的藝術(shù)探求,哪一個都在召喚寫作者,越過高原,攀上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