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謠與貯貝器》的哲學底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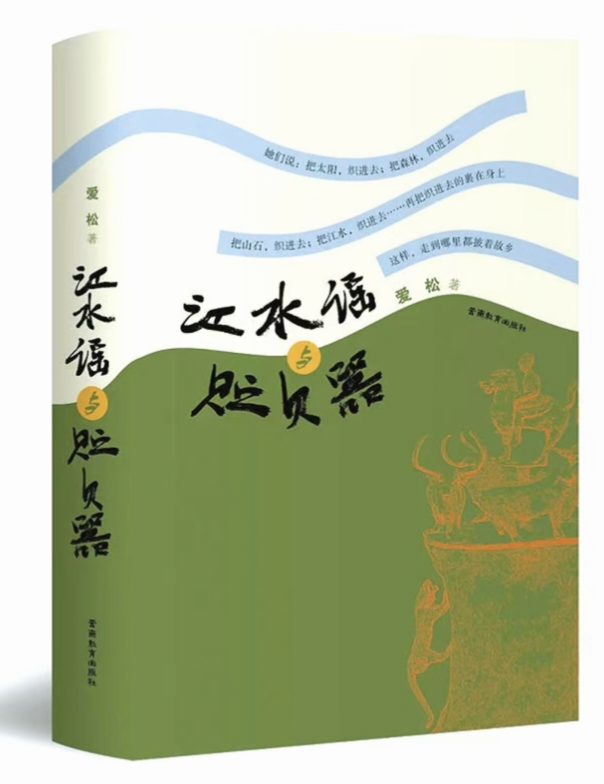
《江水謠與貯貝器》愛松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愛松的現代長詩《江水謠與貯貝器》,是由《江水謠》和《貯貝器》兩部風格迵異、厚度各不相同的長詩合在一起的。之所以放在一起,因為它們一個寫云南的一條江(獨龍江),一個寫云南出土的一件青銅器(貯貝器),二者都是頗具特色的西南風物。兩種風物對歷史造成的深刻影響,就像詩人在《江水謠》中以“風物”為題的短詩中寫的:“我不知道,山上有多少植物/如果每一種說出一句話/江水會淹到哪里?/我不知道,山上還有多少動物/如果每一種離開這里/江水會退回雪頂?/但我知道人類,從不肯善罷甘休”。這段詩,很形象地闡釋了一種動物或植物對一片土地進退的影響。有意思的是,我們抽出來的兩種風物,或者說兩個詞,一個是流動的,一個是沉潛和靜止的。一個在運動中“搬運群山”,一個在沉寂中被時間“并吞蠶食”。這一動一靜看似平常,卻道出了自然規律的不可逆轉,時移世變的勢在必然;同時講述了這片山水的博大、蒼茫、繁復、精細。江水在流逝中不斷地左右著生存其間的人類,生存在其間的人類也以他們的繁殖力和破壞力,不斷地反作用于大自然,彼此自然形成一種既創造又破壞的合力,推動著歷史發展。結果是,流淌的江水使掩埋在晉虛城南玄村地底的古滇國那段漫長的興起和消亡過程得以緩緩顯現;古滇國埋藏在地底下的那件青銅貯貝器則用靜態的方式,演繹著時間作為另一條獨龍江從古至今的緩慢移動。從遙遠的古滇國發掘的那個當時用來貯存錢幣的器物,還有它在人類百折千回的演變中貯存的生命密碼,足以讓我們推開地上地下一扇扇緊閉的大門,一窺當年的晨光夕照。
長詩對于西南風物即貯貝器的使用,和對于這片土地上的人即“我”的使用,最見詩人的煞費苦心。貯貝器是一件任時間一層層剝蝕,但清楚無誤地顯示歷史存在的標志性物證;“我”以具有血肉之軀的生命形式穿越時空,無論在青銅時代還是現當代,都無處不在,無事不曉。兩個在長詩中傾注詩人最重分量的元素,是解開一切奧秘的鑰匙。我感興趣的是,二者作為承擔詩人創新追求的哲學概念或符號,各自發揮的作用既無可替代又意味深長。
貯貝器在詩里是古滇國的圖騰,雖然古滇國真正的圖騰未必是貯貝器,但作為一件標志性青銅器,豹子、野牛、金色騎馬人——它們從時間深處帶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足以代表那個年代的圖騰,同時把西南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人與大自然的角斗、時間無可阻擋這些亙古不變的哲學命題,再清楚不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面對這件神性畢現的物體,我們會情不自禁地發出拷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詩人通過長詩告訴我們,“我”是騎在馬上的那個小金人,“我”從與豺狼虎豹等兇猛動物的搏斗中,從野牛的馴養和食物的獲取中而來,“我”騎著那匹奔跑的馬,沒有別的去處,只有向詩人稱為“時間世界”的深處走去。
這就是愛松在《江水謠》中孜孜不倦歌吟獨龍江兩岸那些動植物的原因,他從生命和事物的最細微處入手,比如鳥、夢、命、藥、桐、種子、泥巴、梯、螞蟻、生息、豹、鵑、行路、唱詞、暗語等等,但他在萬事萬物中選擇這些事物,卻是用心良苦,因為它們都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和詩歌的延展性,就像鑿壁偷光,一個細小的事物一旦被鑿空,光芒便傾瀉而來。仔細辨認這些事物,它們無不具備命運的神性和哲學的思辨性,比如《鳥》,它在天上飛,代表著先民和那片土地上至今仍感到行路難的山民對另一種生活的向往。這體現了被封閉和阻隔的一代又一代人對現代文明的傾慕和渴求;而對于正在山外泛濫和腐敗的東西,又是一種拒斥。再如《毯》,就織造而言,這是一種古老的手藝;作為能夠以任何形式出現的圖案,它又承載著美、幻象和人們對未知世界的憧憬,允許天馬行空,無邊無際。因而他們說:“把太陽,織進去/把森林,織進去/把山石,織進去/把江水,織進去……/再把織進去的裹在身上/這樣,走到哪里都披著故鄉。”如同青銅即使埋在地下也會被腐蝕,也會被無休無止地消磨和遺忘,我們司空見慣的事物也在消逝,江中的石頭就對世界說,“我原來有五個伴”,但“第一個在空中,成鷹飛走了/第二個在山林,成豹奔走了/第三個在水里,成魚游走了/第四個在地下,成泉流走了/只有第五個盤在江水中/倒曳著星空”。長詩就這樣融會貫通,消泯古今,相互印證變幻著的過去和未來、時間和空間,辯駁的力量力透紙背。
“我”在詩中的哲學意義,重點表現在人在時間河流中的生生不息。這個“我”在《貯貝器》中的不同年代、不同人群和不同身份中反復出現,有時是古滇國里的一個古人,也許是工匠、士兵、騎手、巫師,也許是名不見經傳的農婦、婢女、山林里的獵手;有時是晉虛城南玄村的一個現代人,有著隱者、菜農、屠夫、小生意人、逃亡者或罪犯等多重身份。而且這個“我”,既可以是一種文本的結構方式,比如細心的讀者很可能已經發現,長詩第一次寫到“我”和第一次寫到“父親”,都是從一個葬禮開始的,面對著讀者的,是他們的亡靈。這種結構方式就像博爾赫斯在《猜測的詩》中寫到的被加烏喬游擊隊刺殺的弗朗西斯科·拉普里達博士,他在死后以靈魂的口吻敘述其死亡過程。這個“我”,又可以是生命密碼中的“我”,漫長歷史流變中的“我”,或者人類學意義上的“我”,生命基因中的“我”。我欣賞愛松在詩中多處使用生命基因中的“我”。中國古代哲學家有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一說,這里有生與死是人生大事的意思,也有死其實是生,生其實也在死的意思。再者,人類是通過一代代繁衍而延續下來的,我們的民族那么熱心地維護姓氏的源遠流長,道理就在這里。古滇國為什么與晉虛城南玄村存在那么神秘的聯系?很可能南玄村仍然活著的人,他們的身體里仍然流著數千年之前古滇國那些人的血液。因此在詩里死人與活人懇談,實際是歷史開口說話。愛松就是這樣寫“父親”的:“我父親并沒有死去;當然/更不可能活著/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他盯著我/眼光狡黠,如同盯著別人。/從多年前,晉虛城南玄村225號/老屋送葬的熱鬧。一直到今天/我被執行死刑后,亡魂回到老屋/收拾‘腳跡’的冷凄。/我的父親,我老覺得/他就在眼睛里,等待著我”。同樣,長詩也這樣寫“母親”:“連續我的,除了迷宮內,/那根彎彎曲曲的臍帶,還有另一個/與我的心跳同步的心跳,它發出溫暖而濕潤的呼喚”。顯然,這種溫暖而濕潤的呼喚,是從埋葬著“母親”的墳墓里發出來的。后人同“我”對話,就是同歷史對話,同時間對話,也是同自己的血脈和靈魂對話。
我不隱瞞自己的閱讀感覺,當我讀到《貯貝器》的尾聲,仿佛讀到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尾聲,我感到我讀的不是云南一個叫愛松的青年寫的長詩,而是古滇國用羊皮紙傳下來的一部神秘手稿。略有不同的是,《貯貝器》最后以隱藏的“我”向世人交代:歷史的消亡雖然不可阻擋,但也不是大霧茫茫,無跡可尋。在遠處看,從遙遠的古滇國到當下的晉虛城南玄村那段漫漫長途,也不過是時間長河中的一瞬,如同河里的一滴水,山野的一塊殘破的碑。他說:“在大樂隊演奏的統一性里,/并沒有分別給予啟示。/在時間世界永恒的流動下,/一個家族的命運,和一個王國的命運,/幾乎是等同的。晉虛城,/不過只是兩者之間,/被大樂隊演奏的一塊墓碑之石。/它久遠的消亡,并未超過它/短暫的存在。”
(作者系《解放軍文藝》原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