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之名解碼《紅巖》

馬福悅,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經典再造編輯中心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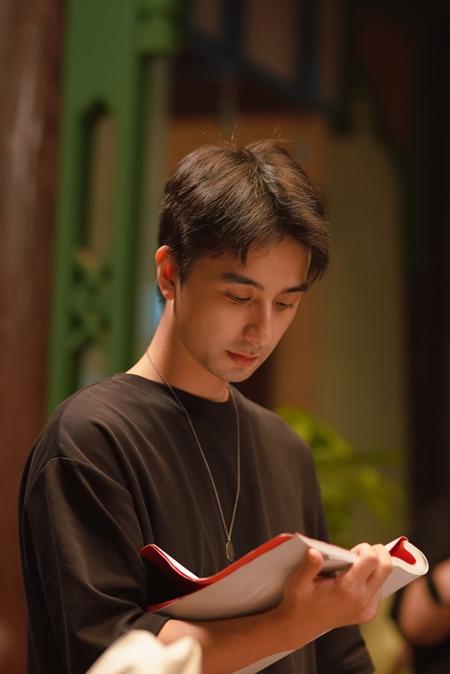
武雨澤,中國鐵路文工團藝術創作部二級導演、話劇《紅巖》導演。

王蔚,中國鐵路文工團一級演員。
由中國鐵路文工團出品的話劇《紅巖》在北京第二輪演出期間,北京二七劇場迎來了兩位特別的觀眾——當年與宋振中(小蘿卜頭原型)一起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監獄的獄友,以及宋振中的二哥。中國鐵路文工團藝術創作部二級導演、話劇《紅巖》導演武雨澤說,兩位老人看完演出后十分激動,“他們對我們說,只要這部戲一直演下去就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能夠讓大家不忘記那些革命烈士,弘揚偉大革命精神。我們也很慶幸能通過這種形式陪父輩重溫他們經歷過的歲月,從他們手中接過紅旗,堅定理想信念,傳承他們的精神”。
9月26日,第二場“新青年文學講壇”直播活動在北京前門“溫暖的BaoBao·兩岸·青年書店”舉行。武雨澤、中國鐵路文工團一級演員王蔚、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經典再造編輯中心編輯馬福悅做客書店,圍繞《紅巖》的誕生緣起與藝術改編,與線上觀眾一同探討如何在當下語境中讓紅色經典與青年產生共鳴、讓紅巖精神持續傳遞。
在更多讀者和觀眾心中種下光明的火種
1961年12月,小說《紅巖》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已陪伴中國人走過60多年的作品,為何至今仍經久不衰?
作為95后青年,馬福悅從小讀著《紅巖》長大,并在工作后參與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最新推出的第四版《紅巖》的編輯工作。在直播中,她分享了《紅巖》誕生的緣起:“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信中說道,聽了羅廣斌同志演講新中國成立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故事,深受教育,希望中青社能把這個故事以小說形式出版,讓更多人了解。”
幾經曲折與數次修改,1961年,由羅廣斌、楊益言創作的小說《紅巖》正式出版面世,如同平地起驚雷,在全國范圍引發轟動。“在回憶錄里兩位老師談到,《紅巖》真正的作者,是那些在渣滓洞、白公館里為革命獻身的先烈,這是一部由許多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譜寫成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歌’。”馬福悅說,“自從《紅巖》出現在大眾的視野里,就一直有著令人心潮澎湃的力量,其承載的紅巖精神至今仍然鮮活。從出版社的角度講,傳承和弘揚紅巖精神一直是我們的初心,也是我們共同的理想信念。”
工作時,馬福悅和同事時常會接到小讀者打來的電話,“他們經常會提出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問題,其中有些我也需要回去查資料才能回答上來。《紅巖》的故事和人物是真正走進了孩子們內心的,從多形式宣傳、版權保護等不同角度為這部旗幟性作品保駕護航,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以當代語境詮釋紅色經典
直播活動前夕,話劇《紅巖》剛剛結束在重慶的巡演,這是繼6月北京首演后,劇組首次將演出帶回紅巖精神的發源地,這也是中國鐵路文工團繼1962年、1989年、1996年后第4次排演話劇《紅巖》。
“距離上一版演出已經過去快30年了,從接到團里要把《紅巖》重新搬上舞臺的任務,我們一直想做的就是讓這部紅色經典被更多當下的觀眾所接受。”武雨澤說,“《紅巖》的故事和人物是深深刻在幾代中國人記憶當中的,如何把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講得有新意,讓觀眾坐得住、看得完,是我們必須考慮的事情。”
劇本改編方面,新版話劇《紅巖》在綜合中國鐵路文工團前三版《紅巖》精華的基礎上,加入了更多諜戰、懸疑元素,同時塑造以江姐、許云峰為首的英雄群像,挖掘每個人物身上的高光。“不管是情節、情感上,還是舞臺形式和舞美上,我們都努力做到保證每一場戲有看點、吸引人。”武雨澤說。
作為劇中江姐的飾演者,王蔚提到,對于演員來說,演繹中最大的難點是要先將大眾刻板印象中的英雄人物還原成一個“人”。“尤其是對于像江姐這樣大家耳熟能詳的英雄人物,往往已經存在先入為主的印象,很容易變成一個殼架在演員身上。但在創排的過程中,通過慢慢走進角色,挖掘江姐的內心,我更加深刻地感覺到她不僅是一位有著堅定信仰的革命者,也是一個鮮活的人。在孩子面前,她是溫柔的母親,在戰友面前,則是溫暖的大姐姐。”
從接到飾演江姐的任務,再到建組排練、站上舞臺,吶喊出那句振聾發聵的“竹簽是竹子做的,可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王蔚感覺,自己也逐漸與這位革命烈士產生了精神上的聯結。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劇中最為共情的是江姐在獄中受刑時,特務拿出她孩子的照片作威脅的一刻,“那一刻感到的不只是心痛,更是心碎,但為了黨的事業和同志們的安全,江姐挺住了酷刑,始終沒有暴露任何信息,這是革命者堅定信仰的力量”。
“這些革命戰士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會在看到孩子的照片時心疼,在得知丈夫犧牲后崩潰,但信仰的力量讓他們一次次在關鍵時刻作出了偉大的選擇。”武雨澤說。
本次新版話劇《紅巖》,武雨澤的女兒也參與到演出中,飾演小蘿卜頭一角。每場演出臨近末尾,演員們在舞臺上集體誦讀《我的“自白”書》時,她都會在側幕跟著背誦。“通過參演,她對于共產黨和共產黨人都有了一種真切的感受。”武雨澤說,“不管是我女兒還是來看演出的小朋友,我相信他們心中都潛移默化地種下了一顆光明的火種。”
馬福悅曾觀看了話劇《紅巖》北京場的演出,她還記得,演出結束散場時,有個小朋友走在她前面一路抹著眼淚。王蔚則提起,在重慶的最后一場演出結束后,有位年輕觀眾沖到舞臺邊,哭著向他們表達自己的感動。
“從創排期間劇組兩次前往重慶采風,再到這次回重慶巡演,無論淡季還是旺季,紅巖革命紀念館等紅色教育基地總能看到絡繹不絕的游客。”武雨澤回憶,而在劇場里,上至八九十歲的老人,下至被家長領著前來的小朋友,走進劇場的觀眾無不沉浸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演出中。“大眾對紅色文化一直有需求,所以我們永遠要對傳承紅色經典和紅色精神充滿信心,堅持講好觀眾愛看的紅色經典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