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鑄就“何以中國”的時空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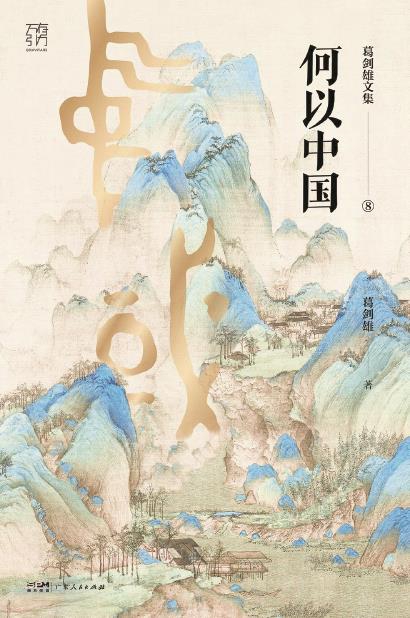
《何以中國》 葛劍雄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日,“尕日塘秦刻石”的確認可謂石破天驚。這塊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立黃河之源,補歷史之缺,也讓人重新審視秦代中國的范圍所及。
“中國”一詞,古已有之。周代初期何尊的銘文里已經有了“宅茲中國”的記載。在當時,此“中國”指的是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歷經三千年滄海桑田,“中國”一詞的內涵不斷擴展,終成今天我們腳下這片廣袤的土地。
這一變遷因何而起,又是如何發生的?葛劍雄教授在《何以中國》一書中,對此展開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討。
文明內部的雙核心
作為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教授在書中主要討論了歷史地理環境與中華文明的關系。當然,《何以中國》里也駁斥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也不能絕對說地理環境就具有決定地位。
譬如古代的徽州與山西商人很引人注目,一些觀點認為,這些地方山多地少,靠農業無法維持,繼而發展商業。但作者質疑:“中國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很少的地方很多,為什么別的地方不出徽商、不出晉商呢?”譬如明清時期的浙江紹興就是典型的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地方,但紹興人找到的出路就不是做生意,而是當師爺。可見“兩個地方,它們的地理環境差不多,但是發展出來的文化和經濟都不同”,也就是有著地理之外的原因。
不過,地理因素仍不可忽視。世界范圍內的古代文明的興起都與大江大河有關,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在世界最長的10條大河中,只有中國能完整地擁有兩條——長江和黃河”。這一點實在意義非凡:“如果只有一條河流的話,隨著氣候條件變化,這一條河流本身免不了要出現衰落,但是我們擁有黃河、長江這兩條大河”“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在不同的階段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歷史上是交相輝映的”。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5000多年前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出現的良渚文化已經跨過了“文明”的門檻,建立了早期國家。可是,“距今4300年至4100年,長江中下游的區域文明相對衰弱”,取而代之的則是中原地區的持續崛起,最終開啟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呢?《何以中國》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列舉了幾個原因。第一,氣候適宜。“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2℃左右,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充沛,是東亞大陸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這樣的描述,當然令人想起了河南的簡稱“豫”字的由來。既然大象這樣一種今天典型的南方動物能在古代的河南出現,當時中原的氣候顯然更接近亞熱帶乃至熱帶。反觀緯度靠南的長江流域,“氣候過于濕熱,降水過多”“不利于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長”。司馬遷在《史記》里寫過一句,“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就是對這一惡劣氣候的形象描述。
第二,從地理上看,黃河中下游平原面積不但遠遠超過長江中下游平原與四川盆地,甚至“比西亞、北非的肥沃新月帶的總面積還大”,堪稱“當時北半球最大的宜農地”。不僅如此,這塊黃土沖積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即使在只有石器或簡單的木制農具的情況下,上面的植被也容易清除,容易開墾成農田,并且容易耕種。而且,平原地帶“便于統治者、管理者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擴散、遷徙和重新定居”。“由于人流、物流的成本較低,強大的部落在聯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圍較大,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最終發展為酋邦或早期國家。”在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幫助下,“諸夏建成夏朝絕非偶然”。
但是,先秦以降,黃河流域卻逐漸失去了氣候、地理上的優越條件。歷史上的氣候逐漸變冷,黃河中游的降水量減少,卻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遷入造成的不合理的農業開發而加劇。在這方面,作者提到了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實例。上古時期,“江”“河”都是專名,前者指長江,后者指黃河。可是,由于大量泥沙流入河道,春秋時期,黃河已由清變濁,而被稱為“濁河”,到了西漢初期,終于有了“黃河”這樣一個形象的名字。
與此同時,長江流域卻成為氣候變化的受益者。“氣候變冷使長江流域逐漸變得溫暖濕潤,四季分明,適合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的栽種,成為宜居的樂土。”于是,當黃河流域因天災人禍陷入衰敗時,長江流域的開發及時彌補了供應不足。無論是北宋的“蘇常熟,天下足”,還是明代的“湖廣熟,天下足”,以及“蘇(州)松(江)賦稅甲天下”,都是這方面的例證。因此作者才有理由在書中斷言,“要是中國只有黃河,中華文明的衰弱不可避免。但因為有了長江,自黃河流域開始出現衰退,即由長江流域補充替代,在整體上從未有過退步”,將中華文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厘清了內部雙核心的演替之后,作者將視野進一步擴大,探討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獨特定位。無論是地中海附近的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還是古代的印度,它們距離東亞的中華文明都相當遙遠,而且隔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等地理障礙,“工業革命以前,在缺少機械動力交通工具的條件下,這些地理障礙無法克服,人流、物流的成本極其高昂,風險極大”。這就使得中華文明成為唯一傳承至今的古老文明,始終保持著獨立、延續的發展。
文明進程的加速器
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位置,或許也使得“古代中國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國’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興趣和動力”。
譬如,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古代中國人把海洋看成土地的邊緣、盡頭,到了海邊就是窮途末路”。當然,有人會問,孔子就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東亞,中國、日本、朝鮮半島是同樣的文化圈”,這基本上是中國單向輸出的結果。作者也承認“海洋對東亞起作用,主要是東海和渤海,而且影響范圍就這么大”。
至于再往外的太平洋,情況又如何呢?現代的研究已經證明,南島語系的人群上古時期就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乘坐獨木舟走向大洋,最終征服了整個太平洋,直到“長白云之鄉”(新西蘭)。但作者在書中提出問題:“既然沒有回來,跟我們飛出太陽系是一樣的,有交流嗎?”顯而易見,直到近代之前,中國與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當然也就不存在交流了。
在陸地上,“絲綢之路”當然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徑。但《何以中國》對此也提出了作者的觀點:“古代中國固然具有開辟長距離道路的能力,卻始終沒有開辟絲綢之路的需要。”反而是西亞、中亞一帶,天然資源并不豐富,能開發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才促進了商業與貿易,“以便使本地的產品得到更高的利潤,并獲取本地稀缺的物資”。在作者看來,這才是“絲綢之路”形成的真正動力。歸根結底,這其實也與古代中國的歷史地理條件有著莫大關系:畢竟古代中國人一直以為“天朝無所不有”,是天下最發達、最富裕、最文明的地方。
在作者看來,“人的開放觀念不是天然的,是周圍環境造成的”。但“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并不會因此失色。書中“中國并沒有從絲綢之路獲得經濟利益”之說似乎稍顯絕對。如果只將經濟利益限定為貴金屬等古代貨幣,情況的確如此。但“絲綢之路”開通之后,西域各地所產的瓜果、蔬菜等陸續傳入內地。《博物志》里就說,“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種,故以胡羌為名”。《本草綱目》對胡瓜(黃瓜)的記載也是,“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故名胡瓜”。這些農作物豐富了中原人民的餐桌,當然也會產生長遠的經濟利益。
書中并不諱言,早在上古時期,雖無“絲綢之路”之名,但中原與西域乃至更西方已經有了交流。“小麥在距今4000年左右傳入中國,從黃河上游傳播至黃河下游。”如今有“南稻北麥”的說法,作者在書中對小麥的意義也不吝贊美之詞:“由于小麥更適合北方平原地區的耕種環境,并且可以給人類提供較高的植物蛋白,養活更多人口,這就形成了巨大穩定的農業基礎,也使(中國)文明的發展進程得到加速。”
不過從歷史上看,這一評價或許略高。中華文明在飲食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粒食”的傳統,即將整粒谷物置于炊器中蒸煮后食用。華北本土作物粟(小米)就非常適合粒食,“膏粱(品質極好的小米)子弟”也成了富家子弟的代名詞。而小麥由于種皮堅硬不適于粒食。只是隨著石磨技術的改進和普及,面粉開始逐步進入尋常百姓的餐桌。小麥才逐漸被社會普遍認可。不過,直到唐代中葉的兩稅法里,仍舊是“粟麥并重”,可見小麥真正占據主導地位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對其早期的作用,恐怕是不能估計過高的。
可以說,葛劍雄教授的《何以中國》一書最核心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個高屋建瓴的“時空”視角,引導人們跳出傳統史學的王朝敘事,去思考山川、河流、氣候這些沉默無言的地理因素,在漫長的歲月中,如何深刻塑造了“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