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芳《小淮班》:少年成長與淮劇命運的同頻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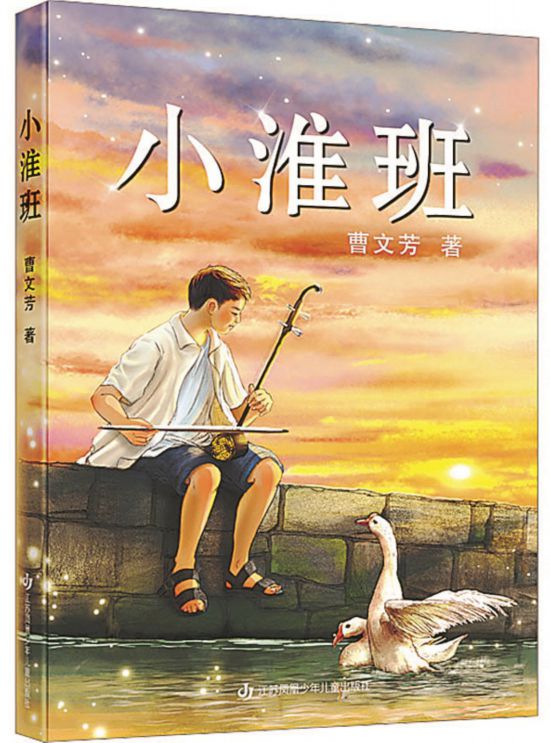
《小淮班》,曹文芳著,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2025年6月
淮劇起源于清代中葉。在戲曲的長河里,它如一葉扁舟穿行于蘇北里下河地區二百余年。曹文芳借少年之眼,凝視著這葉扁舟在時代風浪中的沉浮與新生。糖河村的虞爺爺在秦小兵幼小的心靈里播下淮劇的種子,這個舊戲班的過來人發現了秦小兵的藝術天賦。而秦小兵從虞爺爺這里,弄清了淮劇從哪里來,記住了“虞家班”的前世今生。抗戰時期,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劉少奇、陳毅組織文化人深入民間,發起新淮劇運動,創作演出一批抗日劇目,一個全新的劇種脫胎成型。新中國成立后,虞爺爺的女兒虞海翎這代演員以一出《九灣小鎮》走進北京,讓淮劇受到更多的關注。秦小兵、虎娃等少年后生走進藝校小淮班。秦小兵和他的伙伴們經歷學藝的艱苦、現實的困惑、靈魂的洗禮,最終憑借抗戰題材的現代戲《蘆葦坡》再度唱響京城。這一曲折經過正是淮劇一路走來,幾經掙扎、探索,幾起幾落的隱喻性寫照。曹文芳跟隨劇團生活采訪半年之久。作品對淮劇的細節、服飾、化妝、道具,運用精準恰當,在淮劇的歷史褶皺中挖掘了三代藝人鮮活的形象,又讓人物的呼吸與淮劇的命運起伏同頻共振。
這種苦功,首先體現在人物塑造上。秦小兵帶著西鄉湖蕩的濕潤和糖河大田的靈氣,在虞爺爺的引領下開始了他的淮劇人生。小說著力寫出秦小兵從懵懂好奇到漸漸領悟,再到精神蛻變的成長歷程。水鄉淮劇團對秦小兵的接納不僅是讓孩子開開眼界,而且寬容地接納他參加樂隊的演出伴奏。秦小兵進城拜師學藝,瓢城淮劇團的首席琴師冷峻破天荒地收他為徒,并要求劇團領導“特招”秦小兵進團。看似一路有“貴人相助”,但秦小兵也為磨煉技藝付出了艱辛與汗水。“到了冬天,寒風凜冽,手指凍僵了,拉出的音符都帶著寒氣……”日復一日的苦練讓秦小兵的手磨出了繭子,“路燈昏黃。秦小兵看著自己被路燈拉得細長的影子,不由得想:淮戲的曲調也像影子一樣,是那么的孤獨、凄涼、悠長”,折射出一個鄉村少年在淮劇的浸潤下心智成長的況味。
小說中,整理復排古裝戲《穆桂英掛帥》這一情節設計尤為出色。淮劇傳統劇目的家底,有“九蓮十三英、七十二記”的豐厚資源。曹文芳用了整整一個章節,刻意放慢敘述節奏,針腳細密地寫出了淮劇這一地方戲在“守正”的同時,須接納外來劇種優長,才能得以“創新”,“武戲文唱”,將淮劇的“唱功優勢”發揮到極致。這一章里最亮眼的一筆是秦小兵的臨危救場:打擊樂手許木突然病倒,秦小兵接過鐃順利演完全劇。在這個過程中,秦小兵感受到的不僅是經典作品的博大精深,更有對其中深沉的愛國情懷的領悟。這種精神力量引導秦小兵從單純的技藝承襲,轉變為對信念的追求、對文化責任的擔當。這個糖河村的孩子,在一切向好的時候,選擇報考瓢城魯藝學校,改行學表演。這是小說的情節“陡轉”,也為秦小兵的淮劇人生埋下懸念。
戲曲是“角兒”的藝術。“角兒”是一個劇團,乃至一個劇種的藝術標桿。梨園行有這么一句俗語:“三形、六勁、心有八、無意則十”。三形指的是扮相俊、嗓子亮、心兒靈;六勁指的是唱、念、做、打、勁頭與力度都到位;心有八指的是手眼身法步皆走心;無意則十指的是身心合一,怎么演都對。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才能稱之為“角兒”。秦小兵有形象、有嗓子、通音律、精絲弦、會鑼鼓,能吃常人難忍之苦,這在小說的前九章已鋪平墊穩。曹文芳將秦小兵當作未來淮劇界的“角兒”來塑造。她把戲劇行業的核心密碼,轉化為不露痕跡的文學形象。報考魯藝的情節與秦小兵的成長軌跡如榫卯咬合,無縫連接。秦小兵步入魯藝校園時已12歲,相對來說,學藝的年齡偏大,他將要經歷下腰、擱腿、毯子功的殘酷訓練。而瓢城淮劇團此時正逐漸步入至暗低谷:觀眾大量流失,演出幾乎停擺,員工紛紛離團,團長提前退休辭職……秦小兵能扛住難熬的練功之苦,卻對學成之后到哪兒去唱戲深感迷茫。學員考核的“淘汰風波”,讓他不得已離開校園失落回鄉,如孤舟漂浮在沒有航標的糖河之上。秦小兵與淮劇團的命運恰巧暗合。華中魯藝的歷史底蘊,在秦小兵心里點燃了信仰之火。虞海翎臨危受命接任團長;詩人編劇楊一鵬為劇團尋找生路,沒日沒夜編寫劇本;虞小妹賣掉戲船籌集資金,助力劇團渡過難關;老團長不計報酬投入新戲排練;虞爺爺叮囑海翎,“一個觀眾也是觀眾!”戲比天大的藝術倫理,深深印在秦小兵心上。老一輩藝人的形象躍然紙上,他們在困境中的堅守,顯現出淮劇藝術的靈魂與風骨,這才有了秦小兵“越是這樣,我們越要努力,把淮劇表演好”的不屈心聲。這種代際的精神延續,正是淮劇不會消逝的命脈,也讓讀者看到秦小兵終將成為“角兒”的曙光。這使小說超越了單純的成長故事,升華為地方戲曲頑強的生命力和文化自信。秦小兵和小淮班的這一代,在奔向夢想的路上扛起了傳承的責任與使命。
曹文芳愿意把美好告訴大家:秦小兵在葡萄架下練著二胡,“時常有喜鵲、畫眉、白鴿、翠鳥落在上面,發出清脆的啾鳴,像是給秦小兵的二胡伴唱”,詩意的場景將練功過程轉化為審美體驗;師傅冷峻是外冷內熱的文人琴師,得知秦小兵想報考藝校改行學表演,雖心有不舍,卻愿意為他保密,“如果沒有被錄取,也不要灰心,繼續在劇團學習二胡,以后一樣有出息。”老一輩淮劇藝術家的寬容善良,真切動人。
小說中,黑衣人在街頭拉琴賣藝的場面反復出現。這個“虞家班”的二哥,正值將要唱紅的時候卻突然風暴降臨,不讓唱戲了,所有的劇團被迫解散。他以街頭拉琴賣唱的方式,抵抗轉業去醬醋廠。隨著新時期到來,劇團復建。他自認已是“過氣藝人”,不能成為劇團的負擔,拒絕回團,成了一個在風云變幻的時代中沒有歸宿的邊緣人,折射出多少的人生無奈。水鄉淮劇團的當家花旦杏兒本可以成為瓢城淮劇團的“角兒”,但最終選擇回到水鄉淮劇團的戲船上,將舞臺中心留給了虞海翎。這樣的離別,如月光下的糖河流水微波不興。曹文芳細膩描繪了小淮班的孩子們之間沒有嫉妒攀比,相親相愛、相互扶持的感人場面。當秦小兵背起身患肌無力癥的虎娃,踏上臺階,走到燈光閃爍的舞臺中央,臺上臺下響起一片掌聲。燈光下,虎娃激動得淚流滿面。《蘆葦坡》的創排過程是瓢城淮劇團的生存突圍。解開編劇楊一鵬心結的恰是虎娃的閑聊,兩人說的是蘇鶯老師給藝校新生介紹華中魯藝那堂課,說到動情處,虎娃落淚了,楊一鵬頓覺眼前一亮,《蘆葦坡》的劇本雛形清晰起來。為了修改最后一場戲,秦小兵想起父親曾給他講述過母親臨終前的一幕,覺得應該在寂靜的氛圍中,用肅穆的方式來表達,讓作品有壯烈之美。導演聽完后驚喜不已。《蘆葦坡》于是有了新的結尾:犧牲的魯藝師生,如一組流動的雕塑站立舞臺,天幕上鮮血一樣的霧氣盈盈顫動……這是《蘆葦坡》的高潮,也是《小淮班》的高潮,是文化傳承、代際互補、藝術堅守三個維度的回響。
當戲船在水鄉的晨霧中流轉,一望無邊的大田里淮劇聲腔撫摸著青苗,葡萄架下悠悠琴聲,蕩開了西鄉蘆蕩里連綿不絕的故事;當魯藝精神在少年演繹《蘆葦坡》的汗水里閃光,淮劇藝術薪火相傳。曹文芳以詩性的筆觸,契合兒童心理的書寫,讓淮劇這一民族藝術走入萬千讀者心中。
(作者系劇作家、國家一級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