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循的歷史觀是: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為了《天著春秋》的寫作,我研讀上古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都是從“我的歷史觀”這個基點出發,尋找那個時期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這兩種狀態,是我寫作的基座。 王樹增:尋找古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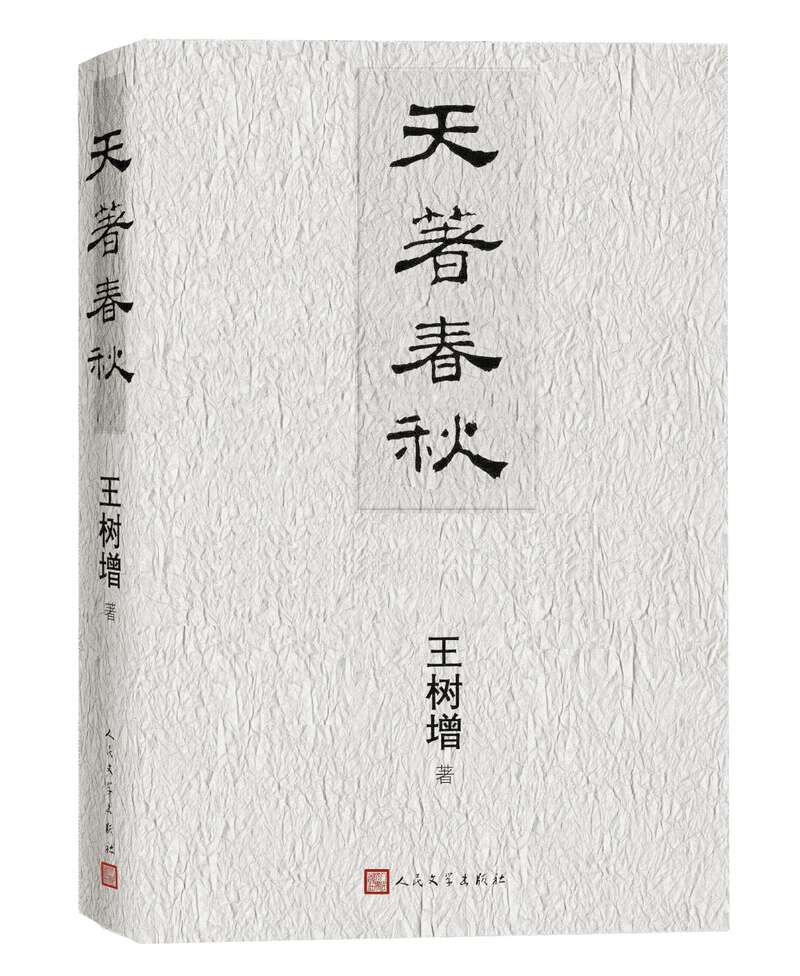
《天著春秋》,王樹增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十年前完成《抗日戰爭》后,軍旅作家王樹增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潛心搜集、整理典籍,專注于《天著春秋》的寫作。他甄別史料,也多次尋訪古戰場、古遺跡,終于以高品質的歷史書寫,完成了這部既是古代戰爭史,也凝注華夏文化、文明回望的大作。
除古代戰爭的豐富內容外,《天著春秋》將夏商周三代到春秋五霸的輝煌與挑戰,文明的興盛與延續,政治的復雜與權謀,都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既可以從中看到古代中國的治國方略、哲學理念、傳統禮俗、文化心理等,品味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智慧,又因作者從個人史觀和文化觀切入的精妙解讀,為我們理解中華傳統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據不完全記載,春秋時期的大小戰事達500多次,100多個諸侯國曾被兼并或亡國,超過50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死。戰爭在霸權更替、推動歷史發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書寫戰爭,不是為了揭秘,也不止于梳理,王樹增希望以重要戰爭為脈絡,講述一個復雜多變的時代,去發掘在極端的戰爭條件下所形成的信仰與精神力量,以及這種精神力量對于當代中國人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無論是《1901:一個封建王朝的背景》和《1911》、“現代戰爭三部曲”(《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朝鮮戰爭》,您所選擇的都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轉折點,《天著春秋》也不例外,起于夏商終于春秋戰國,中國漫長的奴隸社會走到了盡頭。您在完成《抗日戰爭》后曾透露書寫古代戰爭的設想,為何選擇從春秋時期切入?這一階段戰爭對軍事思想形成有何特殊意義?
王樹增:人類文明史,幾乎伴隨著一部戰爭史。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狩獵和農耕生產力得以迅速提高,人口繁衍加速,各部落之間的生存競爭愈演愈烈,戰爭行為便成為生存需求之一。就中國古代史而言,春秋時期是戰爭密集發生的年代,梳理發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戰爭史,春秋時期是重要的源頭。誕生于春秋時期的古中國的兵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塑造中華民族性格的重要的文化依托,是世界文明史中極為燦爛輝煌的篇章,中國的兵家文化,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完成《抗日戰爭》的寫作之后,踏著響徹這片土地上的連綿不斷的戰鼓之聲向遙遠的過去尋古溯源,是我心懷已久的寫作夙愿,因為我知道,要徹底解析人類的戰爭行為,不親耳聆聽上古戰場上的鼓樂齊鳴,幾乎無法自圓其說。
中華讀書報:為撰寫《天著春秋》,您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史料研讀與田野調查,能否分享最觸動您的發現或細節?
王樹增:我認為,中國古代典籍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史書”。無論是《史記》還是《左傳》,和《詩經》一樣,都應該歸于文學范疇。理由是:無論近現代考古學如何發展進步,人類歷史的所謂“客觀真相”,依舊是個謎團。所有的《史書》,都是編纂者站在個體立場上的“創作”。因此,對史料的研讀,最大的功課是透過狹窄的縫隙最大限度地尋找歷史真相的蛛絲馬跡——毋庸諱言,得出的結論也距離“真相”尚有相當的距離——在這個意義上講,史料的研讀是干枯艱辛的,絕少有撩撥心緒的時刻。而走訪古戰場,卻是另一番風景:大河兩岸,沃野千里,山隘險峻,溝壑幽深,大河還是那般流淌,春草還是那般婀娜,歷史上一場又一場的血流成河沒有任何留痕。于是不由得仰天詰問:那些帝王將相們呢?那些甲士兵卒們呢?人類為什么要進行戰爭? 戰爭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的影響是什么?在面對亙古山河的那一瞬,這些詰問涌上心頭,催發了我的寫作欲望。
中華讀書報:從現代戰爭史轉向古代戰爭書寫,研究方法和敘事視角有哪些突破性調整? 您認為這種跨時代解讀最大的難題是什么?
王樹增:無論是寫現代戰爭還是古代戰爭,都是對文化的解讀。所謂研究方法和敘事視角,實際上是文化解讀和視角。因此,古代戰爭的書寫,首先是對中華文化的回溯與瞻仰。但是,無論是《史記》《左傳》《詩經》《楚辭》,還是孔墨老莊,研讀都有相當的難度。這個難度,不是今人對古文字閱讀的障礙,而是要擯棄以今人的思維和視角去理解古人的思維方式,首先努力使自己成為“古人”,此乃難度之最。
中華讀書報:《天著春秋》中對“一鼓作氣”“臥薪嘗膽”“退避三舍”“秦晉之好”等典故的解析令人耳目一新,如何在保證史學嚴謹性的同時賦予文學感染力?
王樹增:如今“非虛構”類文學寫作和閱讀,似乎有熱起來的趨勢,我理解的“非虛構類”文學寫作,至少有兩個特征:一、非虛構,即嚴格遵循考證的原則,事件、情節、人物等等均不得虛構;二、是文學而不是史學,后者是以歷史事件為線索,梳理歷史的前因后果,得出歷史的規律性結論,前者是遵循“文學即人學”的原則,主旨是寫歷史中的人,梳理人的精神發展脈絡——所謂“文學感染力”,即從這里而來。因此,歷史事件僅僅是個依托,我想介紹給讀者的,是“退避三舍”“臥薪嘗膽”和“一鼓作氣”中的當事人,這些當事人的思維和行為,才是寫作和閱讀的精華。
中華讀書報:書中描寫了很多對后世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歷經千年,融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品德和智慧,同時也處處充滿哲理和辯證,比如權力和人理之辯。比如書中既呈現“血流百里”的殘酷,又描寫“君子好逑”的溫情,這種雙重性是否暗含您對戰爭與人性的思考?
王樹增:單純的、純粹的東西和事物,世間根本不存在,因此,我喜歡“雙重性”這個詞。毫無疑問,對文明的摧殘與破壞,對生命的蔑視和殺戮,莫過于戰爭。但是,人類的戰爭行為的雙重性是:戰爭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國家形態的完善和進步,推動了生產和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哲學、美學和宗教,產生了人類的英雄崇拜——可以說,沒有戰爭,人類文明的腳步便無法前行,這個結論殘酷無情,但符合人的本性和歷史發展規律。因此,“君子好逑”的同時又“血流百里”,不正是歷史的本來面目么?
中華讀書報:這種雙重甚至多重性的比照在作品中無處不在。比如表現《詩經·鄭風·東門之墠》時,您寫道:“東門外美麗的花園呀,茜草沿著山坡生長。她的家離我近在咫尺呀,人兒卻像在很遠的地方……”以現代語言傳遞出民歌風情,反映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與激烈殘酷的戰爭相互映襯,更顯出您在歷史書寫中深切的人文情懷。《天著春秋》不僅僅是戰爭史,而是以戰爭為線索的、以戰爭為脈絡的上古時期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這部書的資料多出自《左傳》《史記》等,但您的解析和判斷客觀而真實,史中見實。您在寫作中秉持怎樣的理念?
王樹增:我無法做到“客觀而真實”——《史記》是司馬遷的“真實”,《天著春秋》是我的“真實”——司馬遷秉承著怎樣的理念,不得而知,我遵循的歷史觀是: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為了《天著春秋》的寫作,我研讀上古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都是從“我的歷史觀”這個基點出發,尋找那個時期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這兩種狀態,是我寫作的基座。我寫了帝王們,但是,我力求在我的筆下,讓帝王們回歸到“人”的精神層面——只有將這種層面寫透徹,才有當代讀者的心領神會。
中華讀書報:相信有心的讀者能體會到您的良苦用心。作品以鳴條之戰、牧野之戰、長勺之戰等十場古代大戰串聯千年歷史,篩選標準是什么? 在一般讀者印象中,似乎“麻隧之戰”相對冷門?
王樹增:十場戰爭的選擇都基于一個原則:導致欲望的破滅和國運的改變。“麻隧之戰”是晉國樹立大國地位的開端,也是秦國國運處于低谷的時刻——有趣的是,不久,不可一世的晉國解體了,秦國卻成為霸主——這就是歷史。從這個角度上看,此戰不“冷門”。
中華讀書報:《天著春秋》既寫出了歷史的大脈絡,又寫出了其中的人和精神。您以戰事的視角切入,對歷史、文化進行了多維度的呈現和解析。諸多君王、重臣、將領、游俠、謀士不再只是單一的符號,更是有血有肉的個體。非虛構寫作中如何刻畫人物,您的觀點是什么?
王樹增:文學對人物的刻畫,實際上是對人物性格的塑造,這個塑造除細節之外,還是細節。我的非虛構寫作的體會是:大歷史框架和豐滿細節,兩者缺一不可,誰將兩者融合得恰到好處,誰就是大家。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李敬澤稱本書為“精神的尋根之作”,您希望讀者從中獲得哪些超越戰爭本身的理解?
王樹增:所謂“精神的尋根”,或許這是所有優秀文學作品共有的追求,只是《天著春秋》的精神溯源更為久遠。我希望讀者能夠從《天著春秋》中,不僅僅讀到了古代戰爭,更重要的是,讀到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自然的春華秋實、生命的毀滅再生和興亡的周而復始,從而使得我們看這個世界的紛繁更加理性、心胸更加開闊,使我們面對自己的人生和生命時,積極坦然,從容快樂。
中華讀書報:書中對兵器、儀式的考據極為精細,這類細節對普通讀者理解歷史有何助益?
王樹增:《天著春秋》的寫作,考據最為繁復的,是古代戰爭的樣式、陣型、兵器、戰法、部隊編制、指揮系統、后勤保障,以及戰鼓的尺寸和敲擊處不同鼓點的含義、戰旗樣式和顏色具有的不同等級和指揮權限;甚至戰場口糧的營養成分和各國軍裝樣式的設計理念等等,史料珍稀,如同瀚海拾貝。但是,這類細節的豐潤,是作品成敗的重要前提,也是讀者的期望之一。
中華讀書報:莫言評價您“主觀地解讀客觀的戰爭”,您如何理解非虛構寫作中作者主觀性與歷史客觀性的邊界?
王樹增:莫言指的是虛構類寫作和非虛構類寫作的區別。如果“客觀性”指的是歷史本身的話,作家的獨特解讀,就是所謂的“主觀性”。在優秀的非虛構類作品中,有一個必須的特質:對歷史的獨特的理性解讀。寫作的動力和靈感,正是這個“主觀性”,讀者閱讀的目標,也正是作家的這個“主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