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 | 《不舍晝夜》:通向自我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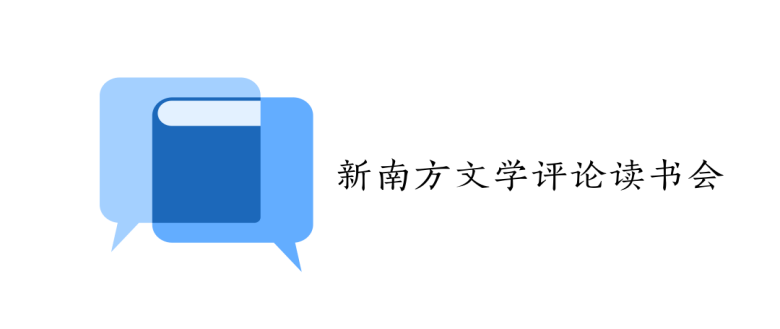
“新南方文學評論”讀書會由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申霞艷發起,成員包括愛好評論寫作的研究者及青年學子。讀書會密切關注當代文學前沿問題、關注本土文學發展,是新南方文藝評論創意寫作聯盟的首席工作坊。
申霞艷(主持人):這次讀書會共讀我們廣東作家王十月的長篇《不舍晝夜》,我想這次閱讀對我們也是通向自我之路。王十月是打工文學的代表作家。今天很多人會覺得打工這個詞不高級、不平等,試圖換成勞動者、工人文學之類,但我覺得打工是一個充滿動感、充滿能量的命名;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指認,對一代人心靈代價的指認。打工文學見證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流動與“脫嵌”,見證人往海岸、港口周邊聚集,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結構和秩序的革新。《不舍晝夜》是王十月對自己打工身份的確認,也是打工文學的升級迭代。主人公王端午通過打工體驗了多重生活,見識了一個廣闊的世界,通過閱讀改變了命運,并不斷自我反思。小說在人物、細節、城鄉空間及時代對比,主角對西方文學、哲學經典的閱讀轉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人格的多重結構與中國傳統的鬼魂敘事結合,父子代際傳承,女性成長,自我詰問與身份認同等等方面均有所思考,值得分析,下面請大家各抒己見。
劉志珍:身份的再造與自我認同危機
《不舍晝夜》中,王端午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渴望確立起“完整的自我”,卻總在現實與理想的錯位中作困獸斗。在盡顯人生的荒誕與虛妄的同時,透視出小人物絕境中掙扎的生命光亮。小說別出心裁地設置了弟弟王中秋這一“缺席的在場者”,以對中國民間鬼魂附身傳說和西方現代心理學人格理論的糅合,指涉王端午隱秘的自我認同危機。對弟弟死亡罪責的主動認領,使他產生強烈的罪感意識。弟弟由此成為他難以超克的心魔,亦是其精神自我,一個阻止他肉身下沉、墮落的自省裝置。王端午希望逃離鄉村和父親,及其象征的暴力、野蠻。但縣城并非理想的樂園,他與師兄李飛的沖突,既蘊含著城市對鄉村的傲慢與偏見,也與其孤僻、不合群的性格息息相關。弟弟則宛若其成長引路人,道出王端午受害者表象背后的自卑心理,勸說他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不愿復刻父親、師傅人生的王端午,懷揣夢想、激情和抗爭命運的執拗,踏上南下深圳打工的冒險之旅。但初到廣東的他不僅被賣豬仔,還因沒有邊防證被擋在關外,成了城市“三無人員”、盲流,于失序中迷失自我。在活著與尊嚴之間他選擇了前者,以盜用李文艷身份的方式,入職名匠廣告公司。名利雙收的他,始終面臨世俗之我和精神之我的劇烈沖突,難以掙脫良心的譴責。這在他得知真正的李文艷自殺后,體現得尤為明顯。冒名頂替被告發后,他選擇辭職去開書店,并將名字改為王端,企圖重新確證自我。但這實則是一種回避現實的消極策略。而從王端改回王端午后的流浪,則具有某種自我放逐意味,也可謂一場自我辯解的“行為藝術”。在徹底拋開世俗的考量,決定說出埋藏心底的秘密時,生命的戛然而止,預示著他終將無法實現靈魂的救贖與安妥。其身份再造凸顯出打工青年的無奈與酸楚,也以自我的不斷扭曲、變形,映射出個人與時代、社會間深刻的失調,改革開放的歷史圖景亦隨之鋪展開來。
邱雯意:“知識”的角色及其時代性
《不舍晝夜》聚焦王端午一生對人文知識的學習與輸出。改革開放初期,“卡門”式的自由和存在主義哲學為王端午帶來啟蒙,促使他走出鄉村、南下深圳,在賺錢之余尋求更廣闊的學識和有意義的生活。人物在不同時代下的知識輸出,成為歷史現場的鮮活寫照。小說中兩類不同的“讀書會”形成顯著對比。1989年的縣城文化宮讀書會是知識分子表達公共理想的場所,體現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激蕩。進入新世紀,西西弗斯書店書友會則是交流閱讀體驗的空間,同時也承辦新書發布會,其文學屬性更為突出,展現出市場經濟發展下文化空間作為精神棲息地的重要意義。另外,小說有意設置兩個頗具象征意味的“說書”場景:90年代,年輕的王端午流浪深圳,在書攤上談論第歐根尼和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其“說書”姿態閃耀著知識所賦予的尊嚴。而聽眾對“文化人”的敬仰與善待,象征著那個時代對具有稀缺性的學問的推崇。而到了互聯網時代,王端午在直播鏡頭前暢談存在主義與傳統文化,知識化身為打造網紅標簽與“割韭菜”的策略。然而,依托網紅模式傳播的知識不得不走向標簽化、娛樂化,其掀起的流量無法將大眾的注意力引向自身,只能成為互聯網上曇花一現的獵奇景觀,極易遭受網絡狂歡的反噬。小說中“流浪大師王端午”的熱度迅速衰退,知識的標簽很快被其婚姻謠言覆蓋,折射出了互聯網時代下知識的脆弱與悲劇。
張昀菡:未選擇的半個句號
縱覽《不舍晝夜》,王端午的一生總在不斷追逐,卻也不斷回顧未選擇的另一條路,這是他所有遺憾和圓滿的源頭。作者有意放大了王端午人生的所有選擇與交接點,讓他一生迷失在小徑分叉的花園中,幻想自己的另一種可能:如果參加了高考、如果入關找宋小雨、如果進了菲林畫房、如果和老曾一起投資……改革開放前后,時代的變換不可預測。因此王端午即將推石上山時總是失手滑落,在往后的人生中,錯過這些關頭的他也在接受當下的同時頻頻反顧,幻想可能畫下的另半個句號。
他靈魂的掙扎也未曾止息。從李文艷、王中秋、王端到王端午本人,主角換過數個身份,在其中糾纏、交融,最終回歸自我。故事的最后,歷經跌宕的“流浪大師”王端午終于決定鼓起勇氣直面內心,說出心底的秘密,讓喧鬧的靈魂歸于平靜,卻又在臨門一腳時被死亡阻擋,只來得及畫下半個句號。他贖罪的理想隨之消逝,再次成為即將攀上山頂前滾落的頑石,隨著生命的消逝徹底落入山崖。但西西弗斯神話之所以能流傳后世,正源于那無可回避的缺憾,與凡俗個體不舍晝夜的努力。正如王十月原本擬定的書名《凡人傳》,人之所以為人,也在于這些靈與肉的缺憾,所有未選擇的路相互交織,才能匯成一個個不完滿、卻完整復雜的“凡人”。
郭雨欣:在常與無常的張力中感受生命的荒誕
王端午中學輟學,打工是他的生存之道,他在深圳為了過關坐黑車卻遭遇搶劫,不得不流浪回家,規律的生命軌跡因而被打破,但王端午的不甘心駕馭著更大的欲望,使他成為了李文艷,原先靠體力維持生計的秩序崩解,憑知識賺得體面生活的生存方式成為新常態,可一封舉報信又改變了“李文艷”的生命軌跡……這些事例是王端午游走于常與無常之間的佐證,他在身份轉換中感受生命的荒誕與恩典,以順無常的姿態接納流動,完成了對主題的自我言說。
《不舍晝夜》無意解答人生該往何處去的重大問題,也不進行廉價的說教,而是坦然放棄對高深意義的追求,揭開生活穩定性的假面,展示個體在秩序與混亂之間的掙扎,從而完成了對生命意義的書寫:它不向人提供形而上的標準答案,而是以真實可感的生活體驗讓讀者窺見生活的荒誕,在接受無常中獲得精神上的自由。
方兆和:過一種文學人生是可能的
《不舍晝夜》表面書寫了一個普通人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實則深刻探討了文學與生命的關系。它讓我們思考,在漫長的一生中,文學到底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當下,“理想主義”似乎淪為某種嘲諷,這部小說卻以鮮活的故事證明,過一種“文學式”的人生,不僅是可能的,更是值得追求的。
在主人公王端午一生的每一次重要選擇中,文學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王端午本來只是一個出生在農村的青年,他通過四姐了解到了《卡門》,第一次領悟“自由”的涵義;《麥田守望者》堅定了他走出農村的決心;《存在與虛無》開啟了他對知識的啟蒙;《卡夫卡傳》支撐他熬過最艱難的打工歲月,并重新審視與父親的關系。在從名匠廣告公司辭職后,一直以來對文學的熱愛讓王端午選擇開書店,并采用“西西弗斯”之名。他與妻子馮素素的相知相戀,同樣根植于文學的共鳴。而王端午在重病一場后選擇放棄一切踏上流浪之路,是因為《荒原狼》的感召。甚至他最終在流浪中成為網紅“流浪大師”,其獨特魅力也源于對文學的深邃理解。
文學對我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在“文學無用論”甚囂塵上的時代,這部作品或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的角度,它告訴我們文學絕非生活的點綴或消遣,而是在無常的人生中,真正可以帶給我們對抗虛無、堅定信念的力量。王端午的一生都在追求文學,實際上他早已將自己的一生活成了文學。
伍常旭:《不舍晝夜》中的鄉土情結
《不舍晝夜》中提到了許多西方書籍,但卻始終能感受到濃烈的中國式鄉土情結。王端午的內心始終與故鄉緊密相連,即使晚年開始流浪,目的地也仍是故鄉。這片他曾經拼盡全力逃離的土地,最終卻成為他心中“精神自由”的象征。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有著“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正如路遙在《人生》中安排高加林最終回歸鄉村一樣,王端午的內心深處依然保留著對鄉土社會的眷戀與依賴。
此外,小說設置了家族中的“反叛者”形象。縱觀《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家》中的高覺新、《白鹿原》中的白靈,他們大多年輕且思想與眾不同。《不舍晝夜》中的四姐以及王端午,與父親發生沖突、并選擇離家出走等行為,契合“反叛者”形象,展現出個體與傳統之間的矛盾。
鄉土社會中人情與自然的融合碰撞,也在《不舍晝夜》的環境塑造中得以顯現。小說中改革開放前后的深圳,充滿奇幻、暴力、血腥、奮斗與遺憾。秩序僅存在于王端午打工的場所,脫離工廠后,他則開始流浪,在“無序”中尋回生命的自由。但“無序”并不意味著冷漠,當他在生病、饑餓之時,仍能得到周圍人的幫助。王端午于秩序與無序之間掙扎的過程,同樣深埋著鄉土的淳樸與野性。
馬褀宸:從“弒父”到“尋父”
王端午的一生是一場未完成的“弒父”,也是一場漫長的“尋父”之旅。他在青年時期逃離父親,卻在中年活成了父親的模樣;他的兒子也遠渡重洋,以同樣的方式逃離了他。這種父子關系的循環,既是中國文學“弒父情結”的延續,也是當代人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尋找自我的精神困境。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弒父”往往象征著對舊秩序的挑戰。但王端午的弒父是不徹底的——他逃離了父親,卻無法逃離父親的影子。當他“賦閑”在家,像父親一樣漫無目的地游蕩,甚至在江邊長椅上過夜時,驚恐地發現自己正沿著父親的軌跡行走。這種循環暗示著單純的逃離,并不能真正斬斷父權的枷鎖。
更耐人尋味的是,王端午的兒子王快樂以留學美國的方式“弒父”,完成了他當年未能徹底實現的逃離。然而,這種逃離同樣充滿矛盾——當王端午臨終時,兒子未能歸來,正如他當年未能見父親最后一面。父子之間的疏離與缺席,構成一種宿命般的輪回。王端午的出走也并未帶來真正的解脫,他的流浪更像是一場自我放逐。但或許,這種放逐本身就是一種“尋父”——不是尋找具體的父親,而是尋找自己與父輩、傳統、乃至自我和解的可能。《不舍晝夜》中的父子故事超越了簡單的反抗,揭示出父子關系中最為深層、柔軟、難以道出的復雜情感:恨與愛、逃離與回歸、斷裂與延續。王端午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成長不是徹底“弒父”,而是在循環中理解父輩,并在這種理解中找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