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2025年第9期|郭爽:留籽(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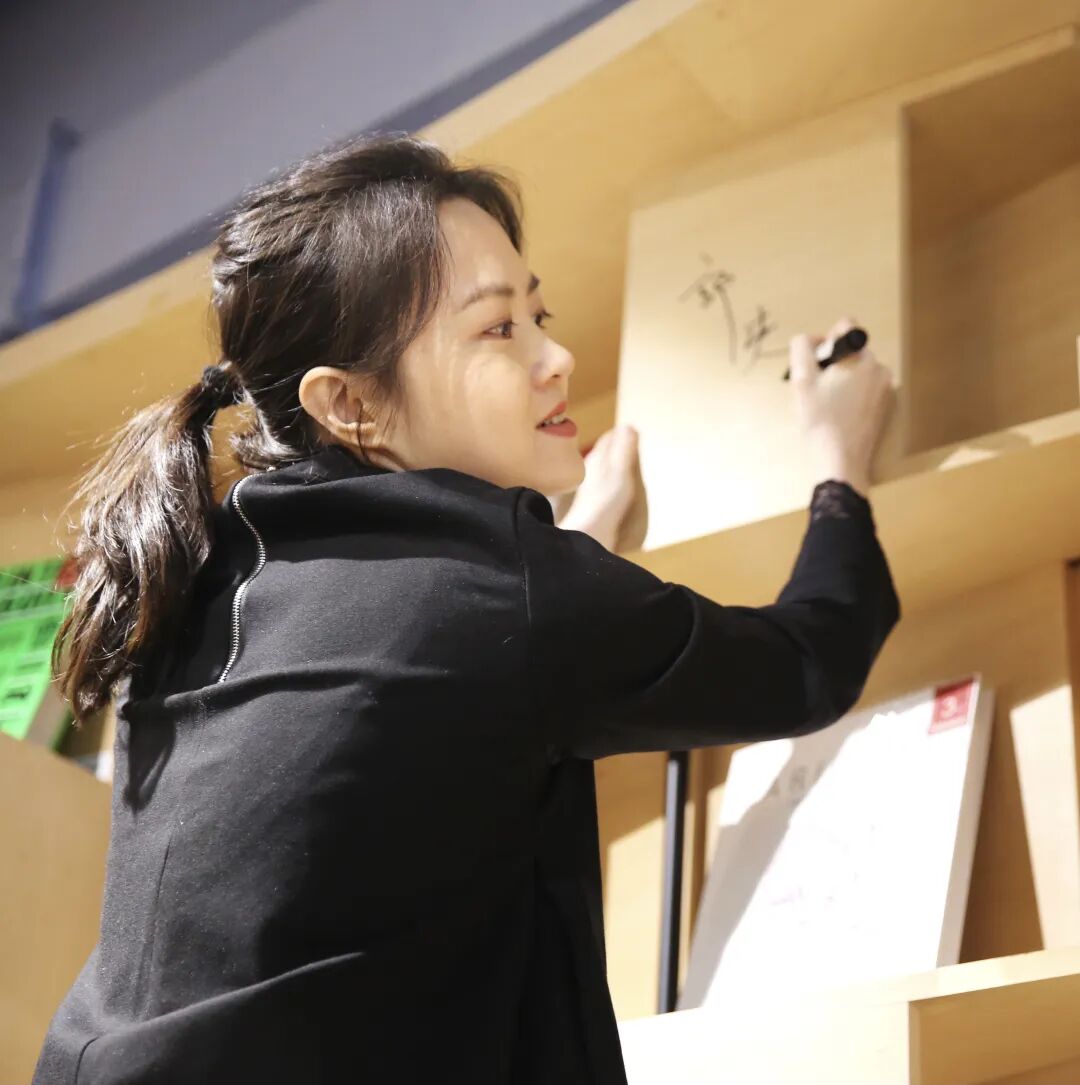
郭爽,一九八四年生于貴州。作品發表于《收獲》《作家》《山花》《鐘山》《西湖》等雜志,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思南文學選刊》等刊選載。獲《小說選刊》年度大獎·新人獎、“《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獎、“金短篇”小說獎、山花雙年獎·新人獎、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儲吉旺文學獎等。
留籽(節選)
郭 爽
窗簾還是灰藍色,天也就還未亮。這時節太陽出得早,偶爾老彭睜開眼,窗簾被天光映成淡藍色,他就知道算睡了個好覺。年歲大了,瞌睡慢慢變少,醒來時是半夜也不慌,躺著不動,多半又能盹過去了。他閉上眼,想著還早呢,再睡會兒吧,可不知怎的,就想起平平說她胃不舒服。這個月她說兩次了。老彭睜開眼,伸手摸床頭的電子鐘,液晶屏上顯示五點三十六,星期日。龍蛇馬羊猴雞狗,星期一到星期天各鄉鎮都有場可趕,但星期天在花鳥市場的場最大。他想起刺梨來。準確地說,是曬干的野生刺梨根。寄去讓平平煮水喝,喝上十天半個月,腸胃再是什么毛病也好了。他邊想邊掀開被子,身子往右側倒了一半停住了。平平的話像是在耳邊:“爸爸,聽醫生的話,曉不曉得?”于是,他忍耐著,一刻鐘,兩刻鐘……直到美麗的晨光從窗簾縫透進來,在兩扇窗簾的淡藍色中間拉出一條粉白色的光帶。老彭不知不覺微笑著。十幾年不碰刺梨了,但他覺得自己定是能認出刺梨根來,切成片、曬干了、變色了,也能認出來。他有信心。他翻身下床。
“老彭,老彭!”有人從遠處喊他。他往聲音來的方向看了又看,不知是不是眼睛又出什么毛病了。他站定,等那個聲音再喊。一把紅色大陽傘下,一個胖男子左手端碗,右手筷子懸空。他往紅傘下面走去,等走近了,胖男子說:“吃過沒有?”是老郜。
“幾點了,你吃二頓啊?”老彭看老郜碗里的牛雜粉。湯底紅、芫荽綠,油滋滋的噴香。
“老板,牛雜粉一碗,小碗。”老郜自作主張給老彭要了一碗。
“今天怕是要超標了。”老彭說。
“天天整你那個粗糧健康餐,偶爾也改善改善嘛。”老郜從老板手里接過新的一碗,遞給老彭。
兩人面對面坐在大紅陽傘下的小木桌子邊,窸窸窣窣吃起來。米粉白、滑溜,吸飽了湯汁,熱乎乎地滑進老彭嘴里,三兩口之后,他額頭、后背微微出汗了。若是從前,老彭撈完米粉,湯也要喝掉大半,今天卻不同,剩一碗湯擺在桌上。他歇口氣,看老郜繼續戰斗,直到空碗哐地落在桌面上。老郜抬頭抹把汗說,可以,這味道可以。
太陽升高了些。陽傘下,兩人的白頭、略微佝僂的背影被映得紅彤彤的。五十歲前后,兩人都戒了煙,也就沒有賴在這里消磨時間的借口。老板慢悠悠送客道,慢走啊,兩位老人家。
兩位老人家擠進趕場的人流之中,在油餅攤、炒貨攤及蔬菜瓜果、鍋碗瓢盆、豬牛羊肉檔的各種顏色氣味和吆喝聲中悠然向前。集市攤檔沿路擺出的長龍蜿蜒不見盡頭,蒼黑的山浮于人潮之上,云朵在山腰處游弋,陽光把云鍍上一層珍珠貝母的光澤。山也好,天空也好,云朵也好,既遠又近,既古老又如這嶄新一天般靜靜地庇佑著小城和它的全部居民。
“拆針沒有?”老郜問道。
“這次不用拆針。”老彭說。
“我記得你上次取出來那十幾二十顆石頭,放在一個瓶子里頭。”
“取結石,挨一刀不說,縫針、拆針……還要留院觀察。這次這個支架,小東西,放進去,指標正常就出院了。”
“科學進步快。等我再老些,裝個機械手臂,那炒起菜來才過癮喲。”
“你都裝機械手了,還操心炒菜的事!郜新民,出息啊你。”老彭一邊說笑,一邊打量草藥攤和擺賣的藥材。
“不行啊?裝了機械手就不吃飯了啊?科技再進步,人還不是要吃飯!”
不等老郜說完,老彭三步并兩步往一個攤販身前擠,指著攤販手中的麻袋問道:“是不是刺梨根?”
跟其他草藥攤少則十幾種多則幾十種藥材成堆擺放不同,這個攤販面前只三個麻袋。其中一袋粉而白的切片,是葛根。另外兩袋切片切面小、質地硬。老彭伸手分別探進兩只口袋,抓取、聞味、辨色。確實是刺梨根。老彭的舌根處隱隱涌出甘甜的津液。刺梨根的淡淡芬芳激活了他的身體記憶。刺梨根加水煮至湯底澄黃,趁熱服用,口腔、胃都會被它獨特的氣味激活繼而舒緩,余留綿長的清爽與甘香。三十多年前,不對,已經是四十年前了,下鄉落下病根后,他經常胃疼,吹了冷風就拉肚子。刺梨根的方子是陶勇媽媽給他的。陶勇媽媽說,毛,你每天熬一道,一次喝完可以,分幾次喝也可以,堅持半個月一個月。他媽媽怎么認得這些山野藥材呢?當時他沒仔細想,只按她說的照做,竟是好了,腸胃像換了一副。一眨眼,陶勇媽媽走了十幾年了,連陶勇都走了七八年了。老彭不忍再想,抓起麻袋掂了掂重量。
老郜先他一步,問道:“咋賣?”
攤販像是不知道怎么要價,嘟囔著現在不好找這野生的,原先田埂、路邊常見,如今修路硬化路面鏟掉雜草,這東西就見不著了。又說,這不是培育出來的新品種,新品種膨大,他這個不好挖,硬得很哪。
“咋賣嘛?”老彭問。
攤販下決心似的,“十塊錢一斤!”
老郜拽他袖子,“走走走!十塊錢一斤,沒聽說過。”
老彭本想討價還價一番,老郜拉得猛、力氣大,他身子偏了一下,也就跟著往前走了。
兩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從南到北走通了集市。老郜從一個挑挑子賣魚的老人手里買下一條大鰱魚,說是今晚有人預訂了一桌宴席,菜老早就點好了,主打的是他的拿手菜熗鍋魚。老顧客,老熟人,肯定要選條漂亮魚啊。這種魚跟養殖的不一樣,養殖的都是些吃飼料的笨蛋魚。這種魚是一條一條釣上來的,生命力強!
老彭看老郜小心翼翼提著魚嘴上的繩子,生怕他這條大鰱魚被人碰著了,就說:“你先回,我去把那袋刺梨根買了。這都走通了,也沒看見第二個賣的。”
老郜想了想,說:“那我先把魚提回鋪子去。你拿不拿得動?”
老彭嘴張開遲疑幾秒后咬定:“一袋就五斤,兩袋最多十斤,只是看起來多,輕得很哪。”
“買這么多啊?”
“寄給平平。”
“給平平買?那我去買。我去我去。”老郜一只手舉高了魚,生怕魚被人和人身上的背篼撞上,一只手拉扯老彭。
“哎哎,不用你去。”老彭擰住他胳膊往回扯。
“還要去寄的嘛。你那附近又沒有快遞站。”
“不用,我打電話喊快遞員上門。多幾塊錢的事。”老彭堅持道。
“那你隨時喊我,明天我都沒事。”老郜說完,轉頭都準備走了,又神神秘秘地往老彭身邊湊,“清了!我說,我債都清了!上月底最后兩千塊錢一還,哎喲,周身舒坦!”
湊這么近,老彭才看清楚老郜額頭上那條疤。十幾年前一天夜里,他們兩個吃燒烤、喝啤酒,醉了醉了,一個還堅持送另一個回家。兜來轉去,老彭準備橫穿馬路時從人行道邊緣一腳踩空,摔了下去,老郜想要拉他,卻不知怎的被他絆住,也摔了下去,正正砸在老彭背上。這一摔,老彭斷了鎖骨,老郜破了額頭,一個打三顆鋼釘,一個縫十二針。說起來是笑話了,沒想到老郜額頭上的疤還這么清晰。
“抻抻展展過幾年。”老彭說。
“啊?”老郜沒聽清。這個老家伙,耳朵越來越背了。
“我說,你快點回去把魚收拾了。”
“要得要得。我給你留得有點好茶葉……”老郜今天心情好,話也多得很。
兩人又往來幾句。老郜說,流行的口味來得快去得快,年輕人嘴饞、貪新鮮,只要新開個館子就去湊熱鬧,但吃來吃去,總歸還不是要早起一碗粉?還不是要吃回這家常菜的老味道?老郜說,積累積累,盤點盤點,他要把這老字號“打造”起來,別的不說,熗鍋魚家家會做,只有他做出了融合口味,吃過的都說好,說有特色。做餐飲,你有一兩道菜做出創意,做得不一樣,才有江湖地位。
老彭聽老郜說著、笑著,有一秒鐘,他覺得老郜走霉運的日子盡了,該是好日子來了。
最終,兩人分頭走開。兩個白頭在明晃晃的日光下,閃閃亮地走遠。
老郜咋就縮水了呢,臉小了一圈,皺巴巴地縮在被子后面。
老彭喊,老郜,老郜,起來吃牛肉了。新鮮宰殺的黃牛,清燉,安逸得很,快起來,湯要趁熱喝。
老郜的嘴在氧氣罩下緊閉,像有什么東西哽在舌根處。
老彭又喊,你給我留的茶葉呢?我還等你一起去接山泉水回來泡茶呢。
老郜雙手僵直,食肉恐龍一般蜷縮在胸前。
老郜床邊的監測儀顯示屏上,兩條綠色的波動線代表他的心臟跳動節律,紅色曲線是血壓,最下面黃色那條代表他的呼吸。老彭凝神看三色曲線和曲線旁邊的數據,又喊了幾聲,老郜仍沒有回應。他抑制住情緒,抬頭望向站在床對面的牛牛。牛牛雙眼腫著,臉頰不知怎的凹了一大塊兒,看著竟比平日更像老郜了。
該說的都跟彭伯伯說過了。
昨天晚上,老郜給那桌老顧客好好露了一手。熗鍋魚相當成功,辣子雞和干鍋牛肉也品質穩定,兩道新菜野生菌豆腐肉丸煲、傣味烤肉串拼盤也都“光盤”了。老郜在后廚忙完,還去跟老熟人們悶了兩杯。結賬時他給抹了零,堅持只收三百八十元。客人們吃得滿面紅光,站在路邊你送我我送你謙讓了一陣,才各自坐車走了。老郜靠在門口的舊竹椅上,看街對面的一排商鋪漸次關燈、拉閘,自家鋪子里兩位小工拖完地、擦完桌子、把潲水桶推到指定位置。夜靜下來了。他關燈、鎖門,哼著歌往家走。到家,妻子兒子都在,吹著電扇聽他講這晚上如何成功。老郜說得興起,又倒了一杯白酒,就著花生米在客廳里自己喝起來。牛牛明天七點要去督工,先回自己住處去了。妻子孫曉娟跟他看了一會兒電視劇,說累了,就去床上躺著玩手機。后半夜,孫曉娟起夜,發現身邊沒人,走出臥室,衛生間的燈光從玻璃門里透出來。她喊兩聲,老郜、老郜,里面沒反應。她擰開門,老郜歪倒半坐在衛生間地板上,鼻孔、耳朵流出的血順著脖子、胸口往下走。他那件滿是孔洞的白汗衫,下半截整個染紅了。
眼前,老彭見到的老郜,身上已不見血跡。不只不見血跡,老郜的頭發給剃光了,衣服全剪掉,被單下打著光胴胴。他給清理得很干凈了。
“咋剃了頭呢?”老彭轉向孫曉娟問道。
“護士說先準備好,要開顱的話,就方便些。”她邊說邊伸手摸了摸老郜光禿禿的腦袋,又順著他腦袋往下,輕輕撫摸這做了四十多年夫妻的男人的耳朵,“咋理得這么難看?他腦殼本身就小,這成個什么樣子?”孫曉娟忽地笑了,眼淚淌過皺紋叢生的眼角,大顆大顆打在老郜的被單上。她抓起老郜的手,硬是把自己的手指擠進老郜僵直、蜷縮的手里,左手輕輕撫摸老郜的胸口,湊到他耳邊說:“醒啊!醒了啊!郜新民,我是孫曉娟啊。來,你兒子在這里。你兒子牛牛啊。我們要接你回家。醒啊!醒了啊!”
醫生沒跟孫曉娟和牛牛說的話,跟老彭說了。開顱已經沒有意義。出血量太大,發現得太晚。讓他清清靜靜走吧。
老彭沒想好怎么跟孫曉娟和牛牛交代。從醫生辦公室到老郜的病房,步子再慢,三五分鐘也走到了。走到門口,他站著不動。門拉開了,孫曉娟奪門而出。兩人各退半步。孫曉娟看清是他,說:“不做手術,我們不做。我正要去找你,去跟醫生講,不做了。”
老彭怔怔道:“不做啊?”
孫曉娟聲音顫抖著說:“郜家人還不來。他們來了我也是這句話,不開顱,放棄治療。人沒給我保住,就給我好好地、完完整整地走。”
老彭聽孫曉娟又說了幾句,假裝接電話,走出病房,走進長長的走廊,不坐電梯,一口氣走下六樓,在醫院的噴水池邊繞圈圈。直到他發現六號樓邊上有條小路通向醫院后山半山腰的亭子,才順著臺階爬上去。他換步太快、太急,還沒爬到亭子,胸口那壓著的鉛塊就崩解了。他雙腿打抖,身子彎折向前,兩只手撐在大腿上,竟發不出聲音來,只有些他自己也沒聽過的、低低的哀號。
當晚八點十七分,彭宥年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他女兒平平的干爹、他的好朋友郜新民走了。享壽六十有六。
一九九三年,彭宥年三十七歲,離婚五年,帶著女兒平平過活。七月份,不知怎么搞的,才過一半,他就沒錢了。他媽陪著他爸在外地療養,他不能去煩他們。況且,如果他跟他們開了口,就應了那些老輩子的話——他一個人帶姑娘怎么行?里里外外……還是快點找個媳婦!男人可不能一個人過活!他生平第一次決定借錢。陶勇掙得多,但龔玉瑩兇得很,找他估計也是白找。郜新民呢?可能沒多少錢,但孫曉娟好說話些。他反反復復想,走到郜新民家附近又走回來。走到第二趟還是第三趟的時候,在自家樓下,他迎頭差點撞上人。一看,這風風火火的,不是郜新民是哪個?
兩個人像是心有靈犀,一前一后開始爬樓,爬上三樓,左邊戶就是彭宥年家。放暑假,平平去少年宮學美術了。郜新民往沙發上一坐,掏煙出來。彭宥年提起暖壺搖了搖,將就著半壺上午燒的開水,給兩人各泡了一杯毛峰。
“你是不是懂相面?你看看我,我是不是多子多孫的相?嘿,跟你說,我又要當爹了。”老郜喜笑顏開。
“是不是哦?”
“孫曉娟懷起了。”
“是不是哦?”
“瓜婆娘還不好意思得很,喊我不要到處亂說。”
“三個月以內是不好到處說。”
“好事不怕出門!”
“也是。”
“就是。再說,我怕哪樣?警告我處分我開除我?我幾年不領工資不端鐵飯碗……大不了罰我款。”
“你打定主意了?留這個娃娃?”
老郜沉默了一會兒,“是姑娘還好點,就怕是個兒。”
“你講反了吧?我以為你就等個兒來供起哦!”
“我是那種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兒子的超生游擊隊?”
“我看是。”
老郜笑了,“姑娘好啊。萬一是個兒,多個討債的,屋頭再多錢都擋不住被他糟蹋。”
“你咋曉得是來討債的,就不能是來報恩的啊?”
“哼,你龜兒子沒當過兒啊?裝,你裝。”
“添雙筷子的事。”
“你倒反過來勸我了。”
“都是順著你說。娃娃啊,來了就來了,來了就接住,接住就養活,養大了攆出門去……”
“要真是這樣就好咯……”
這天,兩人喝了好些散裝白酒。說到后面,老郜說,要是哪天我不在了、先走了,彭宥年,我這兩個娃娃,就只能拜托你了。孫曉娟是媽,她跑不脫。但你要管,你管,行不行?
老郜一開始耍橫、亂說話,多半就是醉了。彭宥年答應他說,你放心,郜新民,平平有的,晶晶就有。我沒錢我賣血去。
第二天一早,彭宥年在廚房給平平做早餐,聽見有人咚咚咚地敲門。孫曉娟站在門外。她遞給彭宥年一個鼓鼓囊囊的信封,說這么早銀行還沒開門,怕他著急,就把鋪子里面的錢清點了給他送來。彭宥年三只指頭撐開信封口一看,里面十元五元的紙幣疊成整齊的一沓。彭宥年要留孫曉娟吃早餐,正說著,平平走來門口。孫曉娟伸手摸摸平平的頭說,走,干媽帶你去看展銷會。那天平平回家后很興奮,她給爸爸看干媽給她買的發箍,說粉紅色的全場就這一個呢。彭宥年給平平戴上說,我姑娘就是漂亮。
一九九三年那會兒,小城沒有漢堡店,沒有健身房,電影院還在,但小家庭們熱衷于擁有自己的音響系統、卡拉OK和家庭影院。人們在樸素的慣性中感到自己對新生活的需求,但沒人輕易妄想擁有自己的手機、電腦和小汽車。當然更沒有人妄想擁有兩個以上的孩子。郜新民算相當出格。不過,在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上,出格并沒有什么用處。他的手藝是家傳的。郜家世代做餐飲,新中國成立后郜氏父子就去國營飯店和賓館掌勺。沒有私營餐館的幾十年,老郜家沒分家,一旦放開,要重新做起生意來,反而分了。同是家常菜館,分出來的三支像是彼此避忌,各占城東、城南、城北地帶,不僅互不往來,久而久之連菜式都認不出是源自同一家老號了。郜新民繼承的這一支,屬于記性好的市民口中“正宗的”“不亂來的”。郜新民前半生的三十六年里,都在他父親定下的規矩中老實過活,先在國營賓館的餐廳學廚,然后評職稱、當廚師。直到他父親百年作古,他才開始考慮是不是該按自己意思來,開館子、換新菜、走江湖。不為什么,他只是想證明,他憑本事吃飯,能養活老婆娃娃。在這個偏遠的小城,生存從來是不容易的。而人,還得活一口氣,還得活給旁人看看,就更艱辛。老郜堅持要第二個娃娃,是不是賭一口氣,沒有人知道。一旦超生,他停薪留職的那份國營賓館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出來開館子、賣牛仔褲、開酒吧、拉白酒去外省賣的人都有,但沒聽說誰就把工作打脫了的。郜新民是第一個。從此以后,這個矮小、敦實、其貌不揚的餐館老板,被人提到時就多了些說法,不再局限于老郜的手藝,而是在人人都只有一個后代的環境里,他竟然擁有一兒一女!沒有這件事,老郜原本是不會進入那些人的話題里的。這輩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兄弟姊妹一堆,他們沒有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也不承認,他們其實是盼望多子多孫的。
自己有沒有想過多子多孫這回事,彭宥年不記得了。那時候,他負責的“刺梨601”開始在全省海拔七百米到一千七百米之間的地區試驗生產。“601”是本省培育的刺梨品種,三十年前,彭宥年的老師盛懷廉跟四位同事在銅仁地區調研時,發現一株豐產、果大的野生刺梨單株,挖其根帶回農學院,經扦插繁殖后,在省內不同土質、海拔、氣候的生態區域經過長期人工馴化,成功培育出生物學及經濟性狀穩定的新品種。在正式命名為“601”前,盛老師退休,彭宥年接過盛老師衣缽,成為第三代“刺梨人”。
彭宥年侍弄刺梨,懂得了刺梨的性情。刺梨樹喜叢生,不喜強光,耐旱不耐寒。不僅果實上長滿軟刺,枝條上也遍布密密麻麻的褐色小刺,扎手,不討喜。他把刺梨的優點牢記于心:維生素C之王,維C含量是檸檬的一百倍、蘋果的五百倍。他懂得刺梨是好東西,但也知道它其貌不揚、口感不佳。人人忙著賺大錢、爭上游、跳舞唱歌,吃得油、吃得精、吃得甜,他們能不能接受刺梨?他拿不準。
出路還沒眉目,農戶那邊就先甩手不干了。農戶不愿意種這東西。村支書、村主任帶頭引種,自家土地都拿來種刺梨,也打消不了農戶的懷疑。跟同批推廣種植的花椒、薏仁、魔芋甚至藥材相比,刺梨接受度最低。將心比心,彭宥年能理解農戶的顧慮——種了賣不出去,花椒、薏仁、魔芋、藥材都能自家吃、送親朋,又丑又酸又澀的刺梨,爛在手里嗎?!家家戶戶的土地、人力都有限,蝕本就沒飯吃,沒飯吃就是等死。誰也擔不起這后果。只是,如果真走到這一步,不只是他和老師們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601”要失敗,也是“601”所意味的另一條道路被判失敗——本土作物的保育與改良、土地種植結構的優化、鄉村經濟的復合化。
彭宥年找到在深圳混出名堂的好朋友陶勇,請他幫忙聯系廣東的企業。他想登門拜訪,親自了解農產品工業化的路子。那時候的思路多半如此,要打破舊,就要走新路子,而工業化生產就是擴大規模、提升品質、促進消費的新路子。彭宥年坐火車南下廣東。車廂里,他這樣三十來歲、拎著一袋文件的人不少。他鄰座就是一位雜志社的主編,說是去廣東拉贊助,想辦法把雜志盤活,“光是印刷費、稿費,每季度硬支出就十幾萬。等財政撥款?等到什么時候?”他跟這位姓鄭的主編互留了電話號碼。雖然并不確定這樣去尋出路到底能不能有出路,但遇見同路人,總有幾分安慰。等真到了廣東,去食品企業、批發市場轉一圈下來,彭宥年在筆記本上寫下:刺梨蜜餞、刺梨可樂、刺梨軟糖、刺梨口香糖、刺梨雪糕……幾乎每一樣產品都需要一條生產線。
彭宥年常年打交道的是農作物、泥土、書本,他不懂得錢生錢的道理。調研回來的報告寫了又寫,錢卻是一直不到位。多虧遇到分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方小鳴。方小鳴從省里面下來黔南掛職,知道黔南幾片用來試種“5號”的土地,是全省為數不多符合“601”種植條件的地塊,就抓得緊。他承諾給農戶補貼到戶,還承諾收果子時從運輸公司專門調車隊,保證把果子運出去。
“601”的樹苗這才種下,都在方小鳴所管轄的農業試驗區。
樹苗種下的那個冬天,彭宥年與前妻辦完了離婚手續。他帶女兒平平一趟趟地坐長途車去黔南看那漫山遍野的“601”。每次去,“601”都躥高許多。這片水土太相宜。一年,兩年……等平平學會給自己和彭宥年收拾洗漱包、坐鄉村中巴不再嘔吐時,“601”開始掛果。
首批果子從下枝、裝袋到運送至農學院的加工廠,沒有超過兩天。以當時的路況和人力,算是快得不得了。方小鳴還在任,還在督管此事。這個言出必行的縣委副書記,多年后以正廳級待遇平安退休,時間證明了他的能力和操守。
“601”是吉祥的果子。生產試驗階段小小的波折過后,第一年就大豐收。接下來就是進加工廠、上生產線、包裝、上市。說是加工廠,其實是陶勇牽頭,彭宥年、郜新民入股的一條生產線。廠房是彭宥年跟學校借的,借的時候寫了承諾書:保證生產,完成囑托。機器是陶勇從廣東租回來的。食品安全等各種執照和證件,是郜新民跑去辦下來的。
彭宥年這輩子第一次做生意,也是唯一一次做生意,就是這回,用豐產的“601”生產刺梨可樂。說是刺梨可樂,其實是刺梨原汁打底的碳酸飲料。農學院里也有其他食品生產線,老牌子的酸奶、牛奶不說,果汁、果酒都是有的。以往彭宥年只管育種育苗的事,現在自己的“娃娃”落地要上市,也就四處請教各位老師、同事。老師們給他打氣,說不著急,小彭,你就想,等于是實驗室放大十倍,安全生產,是不是就這個道理?酸奶廠的副廠長跟他說,只要能抓住娃娃和當媽的,就穩了!學校門口、游樂場門口、公園門口的所有小攤檔,各個街道的小賣部,人家賣五角,你賣三角!外包裝顏色要鮮艷!取經取了一圈,他也就不擔心了。人人都在往熱騰騰的海里跳!
原料、生產線、校工、包裝都已到位,就差個名字。該叫個什么名字呢?郜新民說,叫“三兄弟”。陶勇說,已經有個土豆片叫“兄弟”了。那叫什么,郜新民說,三姐妹?三人笑。另外兩人罵郜新民說,咋不叫三只小豬、三套車、三國演義、三個臭皮匠呢?說說笑笑。后面,彭宥年說,就叫“三個刺梨”吧!他起調,按《兩只老虎》的旋律唱道:“三個刺梨,三個刺梨,跑得快!跑得快!”郜新民說好,舉手表決。三人舉手,全票通過。
那時候,一件商品要流行開,有兩種手段:上電視打廣告和小城居民口口相傳。郜新民請電視臺扛攝像機的王小彥拍了一條小廣告,又請電視臺的老同學、老朋友來自家館子里吃了三五頓。這條廣告以最低價貼在了本地新聞后面播放。廣告里面,三個少先隊員和一個咿呀學話的胖娃娃都在喝“三個刺梨”。三個少先隊員分別是彭宥年的女兒彭平平、郜新民的女兒郜晶晶、陶勇的兒子陶為嘉。胖娃娃也不是外人,就是郜新民的兒子郜牛牛。拍廣告那天,三個大孩子一見面就屋里屋外地跑、尖叫。牛牛還不會跑,老實待在自己爸爸身邊。老郜只用看管這么一個娃娃,心情很輕松。他聽王小彥和王小彥的同事們在商量:先拍三個娃娃喝飲料,然后拍飲料瓶,最后拍牛牛。牛牛伸出三根手指,這不就是三個刺梨?老郜頻頻點頭。
廣告確實有效果。王小彥的創意得到了市民的認可,伸出三根手指比畫出OK的手勢風行一時。“三個刺梨”銷得好,牛牛成了明星。
郜新民之前就打了包票:全城大大小小飯館、食堂,他郜新民說得上話的地方,都上架、展示、促銷。先從他自家的飯館做起,每桌免費贈送一瓶。隨著廣告效應擴散,牛牛的海報成了招牌。郜新民很滿意,跟陶勇說外省銷不動就算了,能攏住本地顧客,這生意也能做下去!陶勇說,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人的口味說變就變,還是要出去跑、想辦法。陶勇回廣東前,給三個娃娃一人一條牛仔褲,給牛牛兩袋含DHA的進口奶粉,還專門交代孫曉娟說,早晚各一杯。孫曉娟接過奶粉,看了看坐在地上玩積木的牛牛,說,跑是會跑了,就怕是個啞巴。彭宥年說,這娃娃肯定不笨,你看,從我們來到現在,他玩積木可以玩一個小時。他專注。可能是個慢性子,說話晚。
在不會說話和后面漫長的磕磕巴巴學說話的日子里,牛牛記住了眼前的世界:街道鋪的是水泥,所以是灰白色,陽光猛烈時是明晃晃的白色。街道兩旁種植的是懸鈴木,所以樹干是剝落、斑駁的灰色,樹葉夏天綠秋天黃,飄絮時是淡黃色。街道上并不擁堵的小汽車是黑色、白色和灰色,出租車是綠色。剛流行起來的鋁合金玻璃窗是茶褐色,后面又流行鈷藍色。孩子們的校服是藍白綠三色,紅領巾是紅色。大人們的襯衫是白色,的確良褲子是灰色,夢特嬌褲子是黑色和咖啡色。除了這些立體的色塊,牛牛能看見空氣里的灰塵躁動、閃亮。灰塵們頭角崢嶸、數目可數,大概因為整個世界的布景都水洗般初生、明凈。
……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5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