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雪》:以詩歌銘刻民族之殤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悼念廣場的黑色花崗巖石墻內,鑲嵌了一面名為《狂雪——為被日寇屠殺的30多萬南京軍民招魂》的銅質詩碑。每一天,都有來自各地的參觀者在此駐足、默讀。這首由詩人王久辛所寫的長詩,共23段,記述和譴責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反人類暴行。
35載光陰逝去,王久辛談起《狂雪》時依然清晰:“直接問就行,這些內容都在我腦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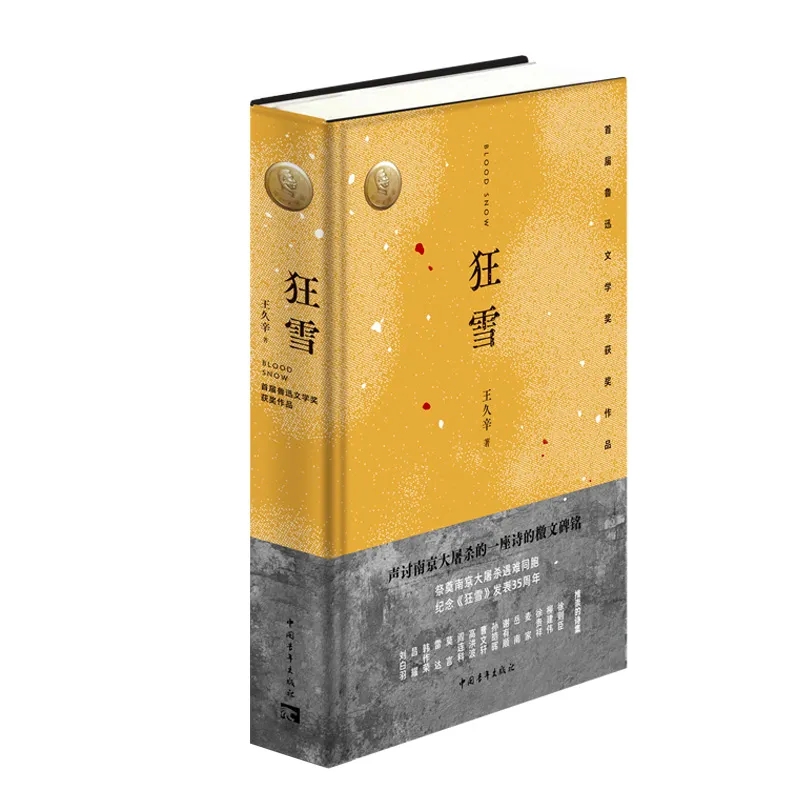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狂雪》
“我的思緒亂飛,像雪花般漫天狂舞”
1990年初春的北京,料峭寒風卷過原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課堂。
靳希光教授的聲音沉重:“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罹難,其中包含10萬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坐在第一排聽課的王久辛攥緊了筆,指節發白。那個被反復提及的慘烈畫面,隨著過去閱讀徐志耕《南京大屠殺》的文字記憶,裹挾著寒意席卷而來。
“我是個軍人啊!”多年后回憶那一刻,王久辛眼中仍有灼痛,“10萬軍人放下武器仍被屠殺,這個坎我過不去。”
當即,王久辛便決定寫一首長詩。
那天下課已是中午12點了,同學們都擁向了食堂,而王久辛則對同宿舍的同學曹慧民、趙琪、徐貴祥說:“你們去吧,給我帶兩個饅頭就行了。”
王久辛回到宿舍,坐在桌前,把紙鋪開,按下錄音機,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激昂的旋律傾瀉而出。
咖啡的霧氣在燈下升騰,血海卻在眼前翻涌,30萬人的鮮血浸透大地的想象,撕扯著神經。“必須冷到冰點以下,用不帶一丁點兒的溫度寫”,他命令自己。隨即寫下了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這樣平靜的詩句:
大霧從松軟或堅硬的泥層/慢慢升騰 大雪從無際也無表情的蒼天 緩緩飄降/那一天和那一天之前/預感便伴隨著恐懼/悄悄向南京圍來/霧一樣濕濕的氣息/雪一樣晶瑩的冰片
筆鋒流轉間,家族記憶奔涌而來,身為八路軍的父親、被活埋于抗日戰場的大舅、身為地下黨的三舅……革命血脈與課堂講述共振,淬煉出了這首一氣呵成的500余行長詩。
凌晨3點45分,長詩最后一個字落下。隨后,稿紙頂端落下兩字:狂雪。擱筆剎那,王久辛稱自己“像放下沉重的巨鼎”。
寫完后,王久辛心里久久不能平復,在天色未明的校園里,來回踱步。
4個小時后,這份手稿已出現在《人民文學》編輯韓作榮案頭。編輯讀罷拍案:“這詩我們發!”
于是,長詩《狂雪》在《人民文學》1990年7—8月合刊上刊發。作品發表后,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文壇泰斗劉白羽先生在刊物大樣上批注:“《狂雪》是可以流傳后世的。”他專門給原解放軍藝術學院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學院培養了一位優秀詩人。
1994年,長詩《狂雪》獲得《人民文學》五年一次的“優秀作品獎”;1998年,詩集《狂雪》獲首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
如今,王久辛所著詩集《狂雪》先后于2002、2005、2015、2017、2025年5次再版,并被譯為波蘭文、阿拉伯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朝鮮文等多種語言。

青年時期的王久辛
雪落無聲處
然而,長詩《狂雪》并未止步于文學。它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淵源,在發表數年后,開始了。
1995年10月,在原蘭州軍區政治部東教場家屬院一個普通的文學聚會上,24歲的范軍初次結識了王久辛。彼時王久辛家中常有文友暢談,氛圍熱烈。一次聚會中,當大家正熱烈討論《狂雪》時,王久辛在西安陸軍學院新聞班的同學劉秦川高聲提議:“別瞎扯了,我說個正事吧,你們要是真覺得《狂雪》好,就去找個企業家,把這首詩刻成碑,運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讓千千萬萬的人都能看到,才算真正干了一件正經事兒!”
這句話觸動了在場的范軍,他曾在家里仔細拜讀《狂雪》后,內心深受震撼,感覺“撕心裂肺”。他當場表態:“真的呀?我想辦法去。”當時,甘肅電視臺青年編導蒲源也同樣想促成此事,二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推進——蒲源主要負責詩碑碑形與陳列方式的設計思考,而范軍則憑借在蘭州大學廣告專業學到的知識,認真起草了一份策劃書。
在打印店打印時,店老板被策劃打動,建議加硬殼封面封底并單面打印以顯莊重。范軍聽取了他的建議,但是交錢的時候卻抓了瞎——錢不夠了!他不愿讓王久辛知曉這筆開銷,堅持自行解決。幾天后,湊足費用的他才取回這份精心準備的策劃書。
帶著滿腔熱情,范軍拿著這份策劃書先后去了好幾個大公司,推介《狂雪》立碑的構想,但全部都吃了閉門羹。
在一次人才招聘會上,范軍遇到了甘肅寶麗集團總裁胡寶衡先生。起初,胡寶衡對此并無興趣,范軍便反復請他看詩,看策劃書。這位南京出生的企業家讀過《狂雪》后,深受觸動,竟表示一定要做好這件事。最初預估的5萬元預算在實際操作中不斷升級,最終胡寶衡投入了近30萬元。
詩的碑文由青年書法家劉恩軍執筆,他選用居延海出土的漢簡體,并融入敦煌遺書的韻味。他解釋:“用草書,很多人不認識;用楷書,寫不進情緒。”在一個夜晚,他凝神聚氣,從8點開始,4000字的碑文一氣呵成。
隨后,范軍與劉恩軍找到工程復印機,按比例復印出樣稿。考慮到碑文需要前言,他們邀請蘭州《讀者》雜志總編輯胡亞權撰寫碑訓。
技術實現上,他們采用銅器蝕雕工藝,把書法作品刻入紫銅板上,鑲嵌于由胡桃木雕刻而成的碑座內,最終形成了一座長12.13米、高2米,正反兩面均刻有詩文的紫銅詩碑。胡寶衡不僅出資,更積極推動,他多次向甘肅省委宣傳部報告,并提出希望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強烈愿望。時任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石宗源同志高度重視,親赴蘭州東方紅廣場驗看了詩碑的質量,對其質量與意義給予高度肯定,隨即與江蘇省委宣傳部取得聯系,正式啟動了跨省捐贈事宜。
令人感慨的是,作為《狂雪》的作者,王久辛對詩碑從策劃、籌資、設計、書寫、制作到協調捐贈的整個過程幾乎全然不知,事后回想,此事之所以能夠得到所有人和甘肅省委、江蘇省委及蘭州市與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他猜只因兩個字:人心。
1995年12月,在詩碑啟程運往南京前夕,甘肅省委、省政府和蘭州軍區在蘭州東方紅廣場舉行了隆重的啟程儀式。現場人山人海,盛況空前。由于詩碑體量巨大,他們租用了兩輛大卡車裝載,行程2200公里,歷經三天三夜,于12月8日晚抵達南京。王久辛、劉恩軍等12人組成的創作團隊則乘坐火車臥鋪同期抵達。
12月10日凌晨2點,詩碑《狂雪》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廣場上安裝完成。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當天,紀念館莊嚴舉行了詩碑揭幕儀式。從此,《狂雪》以具象的、莊嚴的姿態,與那段民族苦難史緊密相連。
后來,隨著紀念館的擴建,詩碑從原廣場位置遷移至悼念廣場,被永久鑲嵌在一面莊嚴肅穆的黑色花崗巖石墻內。如今,它與由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腳印鑄成的銅板路相伴,無聲地向每一位駐足者訴說著歷史,也見證著后人的緬懷。

詩碑《狂雪》
沉淀
當《狂雪》亮相詩壇,并成為歷史記憶的載體時,少有人知道,這份“破土”的力量,早在西北大漠的朔風與邊塞詩的厚重中,沉淀了多年。
1978年,高中畢業并經歷了一年上山下鄉的王久辛參軍入伍,目的地是甘肅的茫茫戈壁。
這片一望無際的雄渾土地,成為他軍旅生涯和文學征程的起點。風沙漫卷的騰格里沙漠邊緣,營房的門窗常常糊不嚴實,塵土灌入;高原的饅頭容易蒸不熟,一日三餐多是鹽水煮白菜……物質條件的艱苦并未磨滅他對精神世界的渴求。
入伍時,他提著一個笨重的大旅行包,里面裝滿了書。在營區,他如饑似渴地閱讀,邊塞詩成為他最重要的精神給養。“高適、岑參的詩句,那種蒼涼、壯闊,與眼前的戈壁、心中的軍人豪情天然契合,”王久辛回憶道,“‘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讀著讀著,就覺得血液里的某種東西被點燃了。”這份對古典文學,尤其是對邊塞詩傳統的深切共鳴,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日后詩歌中宏闊的時空感和深沉的歷史意識。
在部隊,他很快因文化素養突出被選為文化教員,擁有了相對獨立的空間和更多閱讀時間。他不僅廣泛涉獵中外名著,更對詩歌藝術的形式本身產生了高度的自覺。
在他中學時代,語文老師推薦了陳望道著作的《修辭學發凡》,他竟將這本厚厚的理論著作中的72種修辭手法例句,一頁頁抄寫下來。這種“笨辦法”讓他對語言表達的精準性和藝術性的極致追求,烙印般刻入寫作基因。
“很多人誤解,以為寫重大題材就能成功,絕非如此,”王久辛強調,“它需要綜合的素養,尤其是對語言的掌控力。修辭不是花架子,是幫助你更準確、更深刻地表達內心的利器。”即便有名氣后,他仍堅持做“寫作練習”,觀察世間之美,捕捉瞬間的鼻息感觸,錘煉捕捉意象和轉換情感的能力。
源于生活、扎根傳統、精研技藝的堅持,在《狂雪》之后的歲月里,繼續催生出一系列長詩力作,并大多收錄于不同版本的《狂雪》同名詩集或后續詩集中,如《艷戕》聚焦于紅軍西路軍中被俘犧牲的8位十三四歲少女的悲壯故事,《肉搏的大雨》再現了百團大戰中驚心動魄的激烈場景,《鋼鐵門牙》隱喻軍人啃噬苦難的堅韌意志。
王久辛將長詩創作比作譜寫“交響樂”,他認為優秀的詩歌必定擁有內在的“旋律”和嚴密的結構邏輯,“優秀的詩歌一定是起承轉合,嚴絲合縫……能一口氣讀下來,就是成熟的標志”。

王久辛與《狂雪》詩碑
新雪覆舊痕
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與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協會登記在冊的在世幸存者僅剩26人。歷史的見證者正隨歲月凋零,但記憶的傳承從未止息。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中國青年出版社第五次再版詩集《狂雪》,如一場覆蓋舊痕的新雪,為新時代青年擦亮歷史的明鏡。
《狂雪》以“我”為主體的敘事扎入“血海”,撫摸著30萬亡魂,以冷冽筆觸揭露法西斯以“正義”之名僭越人性的本質,詩中“刺刀實現了真正的自由”“那皮帶上的鋼環的撞擊聲”等獰厲意向,將恥痛感深烙人心。它并非歷史事件的復述,而是以詩歌傳遞“不能忘卻”的警示。
這部作品的重量,在文學界的回響中得以印證。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感嘆“國風!感民族之傷痛者國風也——詩林之大,唯久辛矣!”莫言曾評其“系揪心之作,讀后可浮一大白!”作家閻連科更贊其“讓人燃燒、讓人沸騰、讓人在閱讀的鏗鏘中忘我和消失”。
這場落向新時代的雪,覆去創痕,更孕育新芽。當青年撫過書頁,歷史之殤與未來之望在此刻相融,雪落無聲,而回聲震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