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重溫之電視劇《闖關東》 表現民族精神是國劇的良心和擔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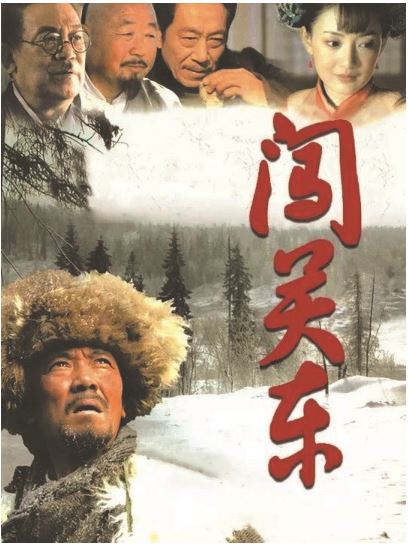
52集長篇電視連續劇《闖關東》自2008年在央視綜合頻道黃金時段作為開年大劇播出后,首輪全國平均收視率便接近11%,并創下連續四周北京地區收視冠軍的紀錄。該劇由山東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大連電視臺聯合制作,張新建任總導演,孔笙、王濱執導,高滿堂、孫建業編劇,李幼斌、薩日娜、宋佳、牛莉、馬恩然、王奎榮、高明領銜主演。該劇獲得多項國家級大獎,在中國電視劇史上無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力作。
一
17年之后的今天,《闖關東》的經典地位依舊穩固。它“大”——題材大,故事體量大;它“新”——史詩與傳奇融合為共生態敘事,釋放出強烈的民族精神題旨;它“奇”——故事大開大合,人物命運跌宕起伏,關東風情民俗獨特。這一成就的取得,有賴于主創團隊正確的價值取向和對電視劇敘事規律的深刻認知。
今天我們所謂的文藝經典,是指能廣泛地構筑于社會歷史,在較長時期傳承于社會,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影響、孵化民族精神的作品。在中國近代史上,“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華民族三次大遷徙。其中闖關東經歷時間最長,人數最多,且以山東人為最多。闖關東是一部表現中國移民的宏大奮斗史、拼搏史。幾千萬人歷盡磨難,離鄉背井,將辛勤的淚水和辛酸的故事留在了白山黑水。無疑,闖關東本身便是一座史詩級題材富礦。電視劇《闖關東》挑戰了這一題材。為達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高度統一,劇作在對歷史脈絡做出縱向呈現的同時,對故事、人物做橫向拓展,努力開掘題材中蘊含的民族精神,將劇作打造成了一座民族精神的“紀念坊”。
在以史詩劇的方式表現與解讀民族精神的主題上,《闖關東》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民族精神意味著一個民族在適應環境、改造世界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語言習俗、人文傳統,以及在長期發展歷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富有生命力的優秀思想、高尚品德和堅定志向,是為民族大部分成員所認同和接受的思想品德與道德規范。民族精神發揮著對內動員和聚集民族力量,對外展示和樹立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闖關東》主人公朱開山是生活在最底層的、最本色的山東人,是闖關東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曾是義和團的一個好漢,身上深植著民族大義。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山東連年大旱,民不聊生。朱開山帶領全家走上了茫茫闖關東之路。奔著關東“有自然之三大利:曰荒,曰礦,曰鹽”,他們來到關東種地、采礦、放排、挖參、伐木、淘金,終于找到了自己新的生存空間。朱開山身上那種吃苦耐勞、見義勇為、講信修睦、以義割恩的精神使他能夠在東北應付各種生存危機,能夠與當地的東北人共同生存。劇作展示了一個普通山東家庭在廣袤、荒涼的山水間,在悲愴、蒼涼的命運中倔強扎根、生息繁衍,最終成為一個堅韌大家族的經歷,透射出闖關東的頑強精神。甚至,朱家能夠娶到那文格格這樣的兒媳婦,都和朱家的名聲分不開。文他娘堅強、賢惠,深明大義:千里尋夫,收養日本孩子,善待鮮兒、秀兒,具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闖關東》開掘民族精神的基石。這些傳統美德超越政治、歷史的意識形態,具有不可解構、不可顛覆性。朱家特別看重“家”。傳武臨終時要求回“家”,表現出對家的眷戀;朱家曾經開除過傳文的“家”籍,傳文悔過以后請求讓他回“家”……他們如此依戀“家”,是因為朱開山、文他娘讓他們懂得了應該怎樣去做中國人。劇中的“家文化”同樣是對民族精神的詮釋。
《闖關東》在充分遵循史實與時間線的前提下,將故事的連貫性與戲劇性平衡得恰到好處,將人物命運與時代背景結合得緊致合理。朱開山這條早年反抗八國聯軍侵華的山東漢子,闖關東后運金成功,在元寶鎮站住了腳跟,此時的背景是辛亥革命成功;元寶鎮遭到散兵燒殺搶掠,朱家被迫北上齊齊哈爾,開煤礦與日本人發生利益沖突,此時背景是日本人侵占東北的野心漸顯。《闖關東》這兩個重要的情節轉折點,使其故事由家族敘事上升為家國同構敘事,人物完成了從傳統美德到民族精神的升華。《闖關東》讓觀眾耳目一新之處在于,這群中國人形象,不僅實誠而且智慧、包容,就像朱開山剛到齊齊哈爾開辦山東餐館和貨棧遇到惡性競爭所表現的那樣。表現民族精神是國劇的良心和擔當所在。歷史大戲,家族大戲,人生大戲,它們的靈魂在于能否詮釋民族精神,這也是能否創作出史詩的起碼要求。如黑格爾在論史詩時所言:“史詩就是一個民族的‘傳奇故事’,‘書’或‘圣經’。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這樣絕對原始的書,來表現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史詩這種紀念坊簡直就是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意識基礎。”
二
《闖關東》原擬創作“三部曲”,第一部時間截止到九一八事變。所以其主要篇幅并不是反映抗日斗爭。但劇作通過充分的鋪墊,在大結局中把抗日斗爭推向高潮。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朱家人不再只是關心自己的生意、煤礦,他們把維護民族尊嚴放在了首位。結局這樣一組畫面,朱傳武犧牲后,朱開山說:“把傳武拾樓上去!”面對犧牲者,不論是文他娘扶著兒子痛哭,鮮兒和他未了的夫妻情以及秀兒的夫妻情,還是朱開山獨自垂淚的鏡頭,都震撼人心、催人淚下。危局中,朱開山依然教育全家說:“我們中國人得好好活著。”一家人上陣殺了日本侵略者后,用馬車拉著全家又踏上了茫茫的遷徙之路。此時盡管文他娘已是白發老太,但他們的又一個孫子誕生了,不僅有了一個大名“國強”,還有了一個小名“亮子”,頓時就把歷史和今天觀眾對接了起來:深信民族要自立,國家亡不了,任誰也不能無視中國和中國人!
《闖關東》之后的《闖關東中篇》是又一部極具思想震撼力和史詩品格的力作,這部劇以抗戰敘事為主體,由于它和《闖關東》的主要故事已經沒有關聯,盡管編劇仍為高滿堂、孫建業,故不在本文詳述之列,但它仍無愧于《闖關東》這個品牌。
《闖關東》給當下抗戰劇的啟示在于:主創團隊首先要敬畏歷史,尊重歷史事實,正確還原歷史語境。中國抗戰題材影視作品若想成為經典,需要以嚴肅的態度、理性的創作、客觀的敘述、多元的視角、豐富的影視語匯,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美學的平衡中構建敘事。只有在歷史與美學的雙重框架下“講史”,才能真正實現“掃雷”與“去神”的效果。所有向著經典前行的劇作都應把功夫下在認真研究歷史,正確還原歷史語境上,體現對歷史的高度尊重以及勿忘國恥、緬懷英烈的敘事主旨,使劇作真正發揮歷史教科書的認知作用。正如《闖關東》所努力追求的,用客觀、理性、均衡與自省的邏輯書寫中華民族共赴國難、保家衛國的神圣戰斗詩篇。在一種整合性的書寫中,使劇作完成對中華民族共同的社會心理、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的承載。
(作者系文藝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