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醒山河 | 這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是泥土中生長的戰歌
編者按: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從1931到1945,中國作家在烽火與熱血交織的大地上,在嗚咽與戰歌共鳴的山河間,用筆寫下不屈的覺醒。抗戰文學參與了硝煙彌漫的民族記憶,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典佳作。為銘記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緬懷英勇獻身的先烈,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的“山河跡憶——手稿里的抗戰中國”特展將于2025年9月1日開幕。該展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陳列展覽推介名單。展覽開幕前夕,中國作家網特推出“筆醒山河”系列文章,分享策展人眼中的手稿、書信、日記、報刊,以及文學文物背后的抗戰往事。

泥土中的戰歌:抗戰文學代表作《差半車麥秸》
?王十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山河跡憶——手稿里的抗戰中國”特展靜謐的展廳里,一份泛黃的1947年懷正文化社版《差半車麥秸》靜靜陳列。這部由姚雪垠創作的薄薄小冊子,穿越八十載烽火歲月,成為抗戰文學的一座豐碑。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重讀這部誕生于硝煙中的杰作,我們觸摸到的不僅是一個農民的成長史詩,更是一部抗戰文學如何深扎民族土壤、喚醒民眾力量的壯闊詩篇。

《差半車麥秸》封面。姚雪垠著,懷正文化社,1947年5月版。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烽火中的文學突圍
1938年的中國文壇,正被“抗戰救亡”的急迫呼喊所席卷。報告文學、戰地通訊、宣傳劇等“小形式”作品占據主流。盡管充滿鼓動性,但隨著戰爭長期化,其“差不多”的浮面化缺陷日益顯露,“偉大時代為何無偉大作品”的質疑隨之而來。作家們雖有“忙于救亡,無暇深構”的辯解,但文學對戰爭深度表現的渴求已不可阻擋。
正是在此背景下,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如一道驚雷劈開文壇沉悶。小說摒棄了當時流行的見“事”不見“人”的速寫模式,將鏡頭對準了一個地道的河南農民——一個小名叫“王啞”的農民游擊隊員,外號“差半車麥秸”(意為“不夠數兒”,指人不夠成熟)。這個被游擊隊誤作“漢奸”抓起來的莊稼漢,以其笨拙的言行、樸素的愿望和內在的韌性,一舉顛覆了文壇對農民角色的刻板想象。
茅盾在《文藝陣地》上率先盛贊其為“目前抗戰文藝的優秀作品”,張天翼更激動地宣稱:“《差半車麥秸》寫得真好……也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最優秀的一篇文藝作品!”四年后,郭沫若回顧抗戰文藝時仍強調:“新作家姚雪垠的出現,和他的短篇《差半車麥秸》是值得我們提起的。”這部作品標志著抗戰文學焦點的重要轉向——從事件的記錄轉向人的深掘,從表面的吶喊轉向靈魂的刻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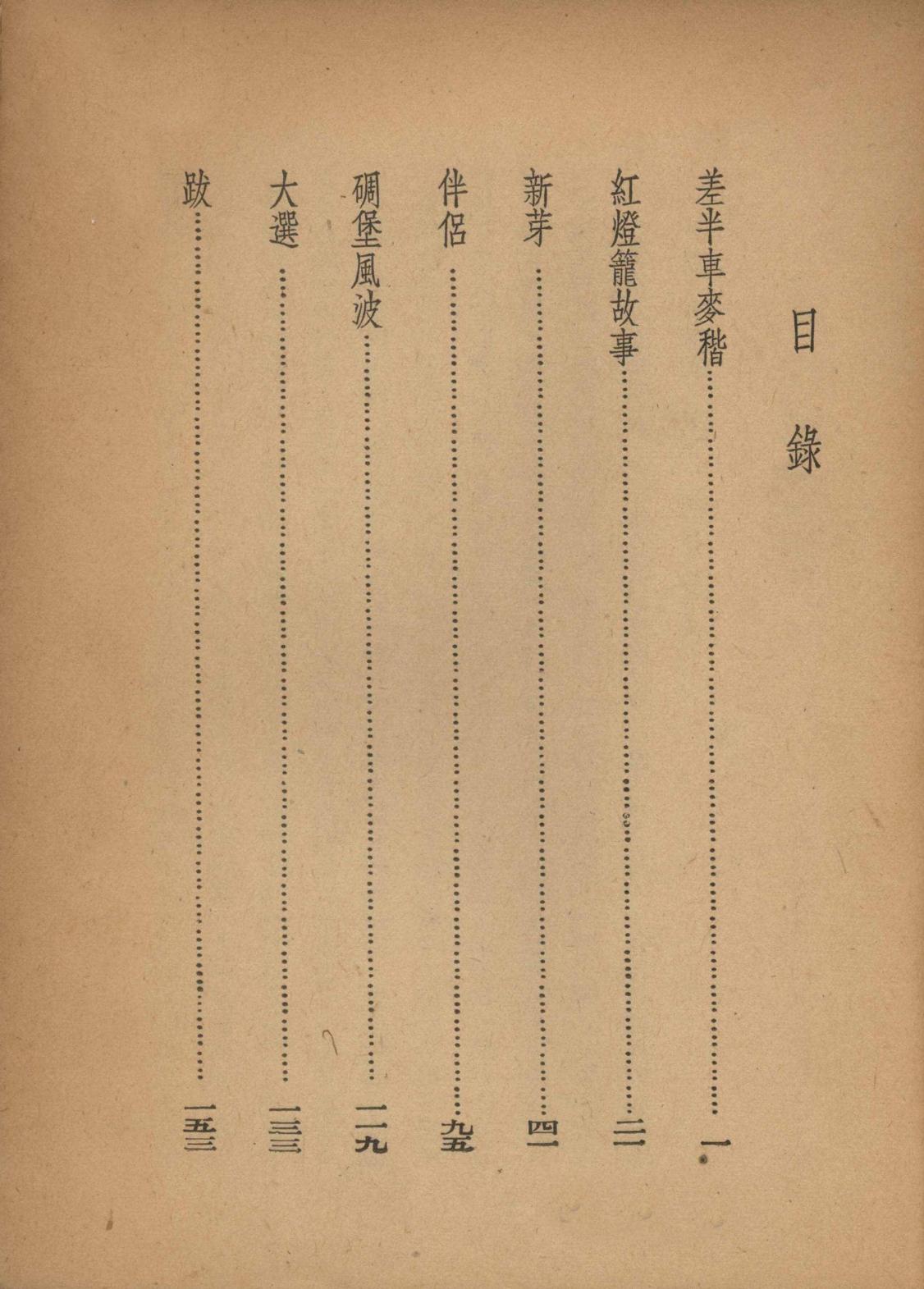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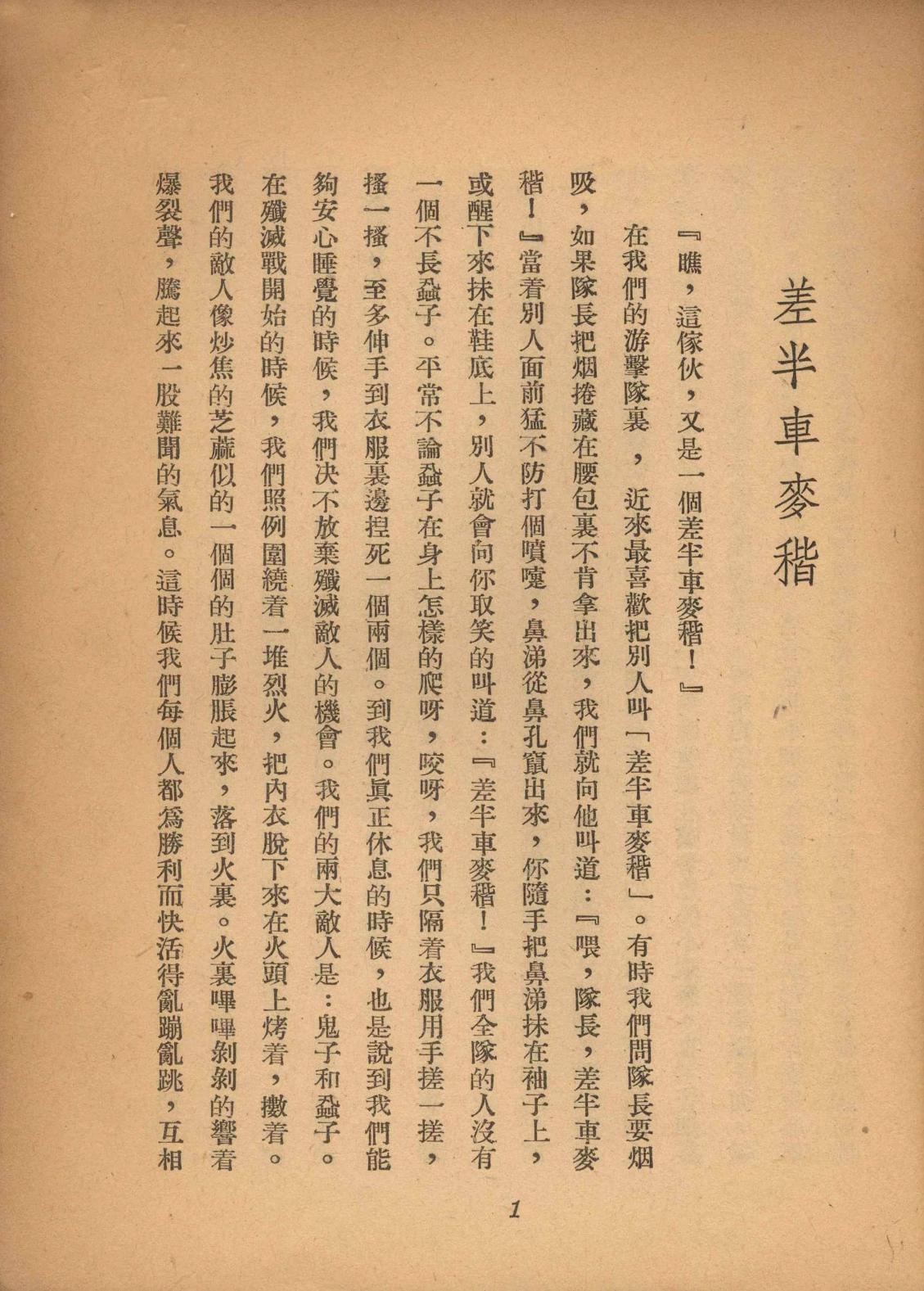
《差半車麥秸》目錄、首頁。姚雪垠著,懷正文化社,1947年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一腳踩出油”的語言革命
《差半車麥秸》最震撼文壇的,是其徹底的語言革命。面對當時創作中嚴重的歐化傾向——長句、倒裝、晦澀難懂,姚雪垠旗幟鮮明地轉向了中原大地鮮活的口語礦藏。他廣泛搜集、精心提煉河南方言,讓主人公的語言浸透泥土的芬芳與生命的質感:
被審問時,差半車麥秸看似懵懂地混淆“鬼子”與舊軍閥“北軍”,涕淚交加地賭咒:“龜孫才是漢奸啊!我要是做了漢奸,看,老爺,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托爾斯泰曾洞悉農民“笨嘴拙舌”下隱藏的智慧,“差半車麥秸”正是以此探明對方態度后才吐露真心:“俺家小狗子娘說,‘怕啥呢,我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吶,你這二百五!’……我是中國人還會當漢奸嗎?”樸素話語直指民族認同的核心。 差半車麥秸心疼荒蕪的田地:“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生生地做活,好好的地里哪能長這么深的草!”一句“這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被評論家李廣田譽為“農民的詩”:“這是多么活潑而又深刻的一句話呀!……是真正的最好的‘活的語言’”,精準傳達了農民對土地的骨血深情。差半車麥秸會習慣性地把鼻涕“一彎腰抹在鞋尖上”,鞋幫凝結著厚厚的“干的和未干的鼻涕”;加入游擊隊后半夜偷熄燈只為省油;甚至偵察敵情時還惦記著“俺家還少一根牛繩哩”,順手牽走老鄉的繩子。這些毫不避諱的細節,白描出一個在極端貧困與文化匱乏中掙扎的農民真實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烙印,其“鄉土氣味”濃郁得撲面而來。
姚雪垠坦言:“《差半車麥秸》主人公典型性格的塑造,得力于鄉土語言。”這種語言選擇,是對“五四”后部分新文學輕視民族傳統的自覺矯正,更是響應“文章下鄉,文人入伍”的時代號角。1943年《新華日報》組織了三篇文章,稱贊姚雪垠為“最肯花費匠心來使用中國大眾語文的作家”,“在文學語言創造上,有了燦爛的新成就”。繼承了《水滸》《紅樓夢》的口語傳統,為文學大眾化開辟了“平坦大道”。
沉默的大多數在覺醒
《差半車麥秸》的深層價值,在于它有力地回應了抗戰初期關于民眾角色的重大爭論。當國民黨詆毀北方農民“十人九漢奸”,當一些人哀嘆農民“隔岸觀火”時,姚雪垠以筆為矛,塑造了一個從沉默到覺醒、從懵懂到堅定的農民戰士形象,雄辯地揭示了戰爭偉力最深厚的根源——覺醒的民眾。
主人公的轉變并非一蹴而就。他加入游擊隊的最初動機極其樸素實在:“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沒有高調的口號,只有對生存根基最直接的捍衛。作者以“欲揚先抑”的筆法,精妙展現其性格的多重矛盾: 被誤會時嚇得“腿戰栗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而戰場上為救戰友,最終英勇負傷。他為省油不惜違反紀律,卻也能為集體默默承擔最艱苦的任務;他帶著濃厚的小農習氣,卻在集體熔爐中逐漸理解“中國人”的意義與抗爭的價值。茅盾精準地剖析道:“這個故事里表現的……雖然描寫缺點,但不使人悲觀,那便是農村老百姓都有先天的民族意識……敵人來了的時候,他們便要起來抵抗。”他盛贊“差半車麥秸”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形象代表了“新的典型”,是“肩負著這個時代的阿脫拉斯型人民的雄姿”——如同希臘神話中以雙肩支撐蒼穹的巨神阿特拉斯,中國億萬普通農民以他們的血肉之軀,默默扛起了民族救亡的重擔。這種覺醒,不是外部強加的“說教”或“拖拽”,而是根植于樸素民族意識、在殘酷現實激發下的必然迸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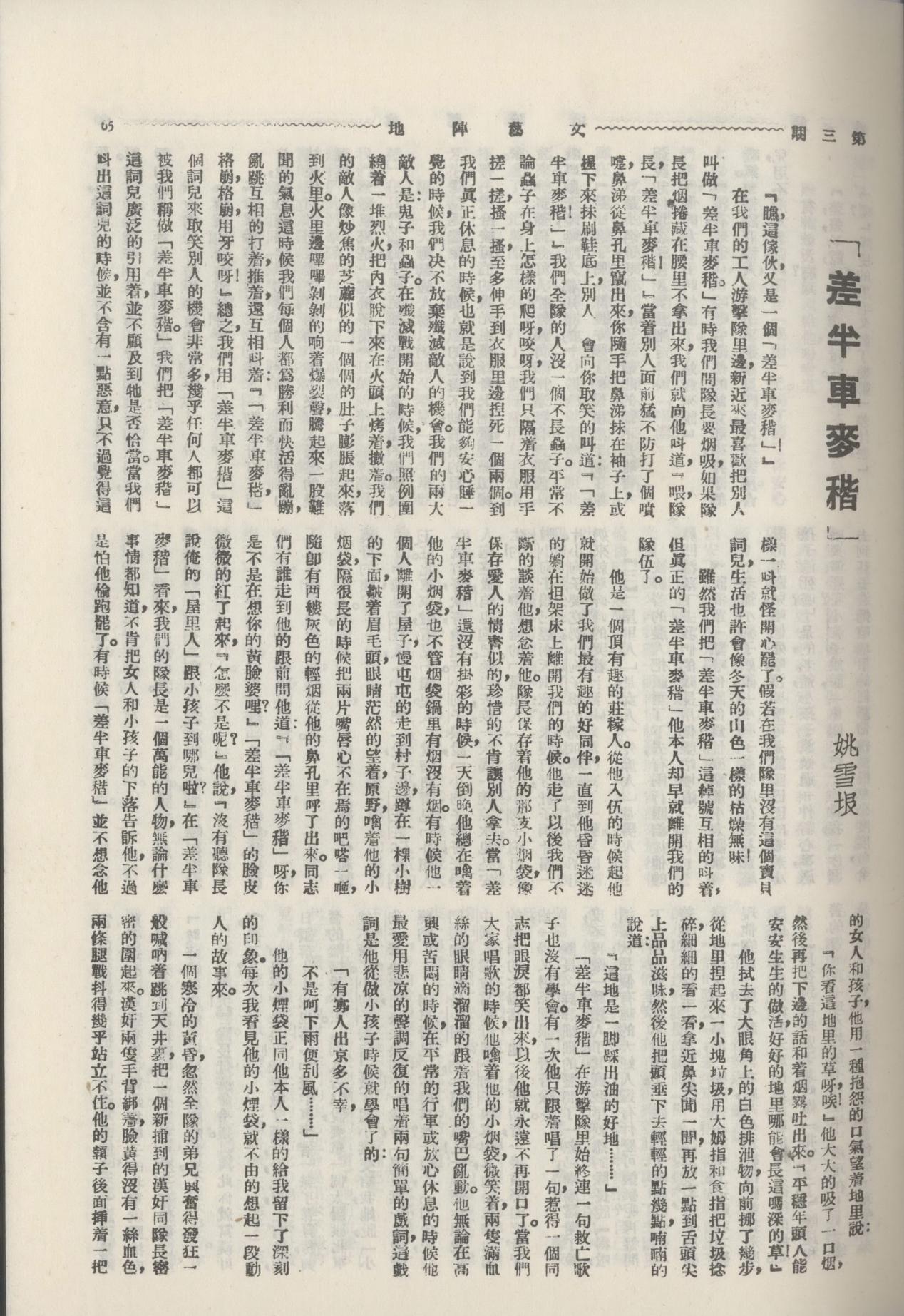
《差半車麥秸》,初刊于1938年《文藝陣地》第一卷第三期。
80年后的回響
八十余載光陰流轉,《差半車麥秸》早已超越了一部小說的范疇。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的今天,重讀這部館藏珍本,其啟示歷久彌新:它證明了真正的文學影響力源于對民族生活的深刻體察與對大眾語言的創造性運用。姚雪垠對豫西農民性格的稔熟、對鄉土語言的淬煉,使作品獲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在全球化語境下,這提醒著中國文學保持文化根性的重要。
小說以文學的方式宣告,抗戰的勝利基石是千千萬萬如“差半車麥秸”般覺醒并奮起的普通民眾。它是對“人民創造歷史”的生動文學詮釋,在宏大敘事中為沉默的大多數樹立了一座文學的豐碑。
面對復雜的歷史與人性,姚雪垠堅持不回避缺點,不簡化成長。這種扎根現實、尊重生活復雜性的“新寫實主義”精神,對克服文藝創作中的概念化、浮泛化始終具有鏡鑒意義。其白描手法、細節功力,至今仍是寫作的典范。
《差半車麥秸》是探索文學民族形式的成功典范。它沒有排斥現代意識,卻以地道的中國氣派、中國風格講述中國故事,實現了民族形式與抗戰時代精神的完美融合。這對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當代文學話語體系,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這份珍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差半車麥秸》,其紙張雖然已然泛黃,但其精神內核——那從泥土中生長出的堅韌、在民族危亡中迸發的偉力、用最鮮活語言奏響的生命戰歌——依然澎湃如昨。在紀念勝利、緬懷英烈的時刻,它不僅讓我們銘記歷史烽煙中一個農民戰士的成長足跡,更昭示著文學扎根民族、服務人民的永恒使命。
作者簡介:

王十,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主要從事展覽、檔案工作,文章見《文藝報》《縱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