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有英俊出中國(guó)”:魯迅與臺(tái)靜農(nóng)
編者按:日前,文史作家張守濤出版新作《魯迅的朋友圈:魯迅與中國(guó)現(xiàn)代英俊》(新華出版社,2005年5月)。該作是一本梳理魯迅先生人際交往,研究魯迅對(duì)當(dāng)代文壇和文化人影響的通俗著作。作者從知識(shí)分子人生和作品文本出發(fā),結(jié)合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史料,比較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書(shū)寫(xiě)了魯迅與中國(guó)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的關(guān)系,尤重魯迅對(duì)其影響。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中國(guó)作家網(wǎng)特遴選部分章節(jié),以饗讀者。本次發(fā)布的是第三章《“愿有英俊出中國(guó)”:魯迅與臺(tái)靜農(nó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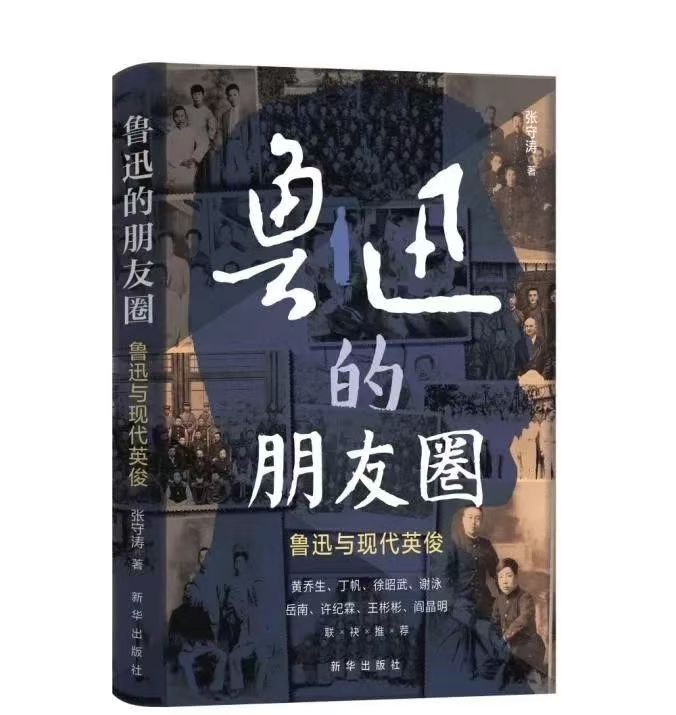
《魯迅的朋友圈:魯迅與中國(guó)現(xiàn)代英俊》,張守濤 著,新華出版社,2005年5月
“愿有英俊出中國(guó)”,魯迅甘當(dāng)“梯子”對(duì)青年寄予厚望,對(duì)眾多青年作家熱心培養(yǎng)盡力指導(dǎo)。中國(guó)眾多現(xiàn)代作家與魯迅有著密切關(guān)系,他們深受魯迅影響,臺(tái)靜農(nóng)、李霽野、曹靖華等未名社成員就是其代表。
一、“臺(tái)君為人極好”
臺(tái)靜農(nóng)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縣葉家集鎮(zhèn),他與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張目寒皆為小學(xué)同學(xué)。他雖然幼年接受傳統(tǒng)私塾教育,但后來(lái)閱讀嚴(yán)復(fù)的西方譯作而萌發(fā)先進(jìn)思想,中學(xué)時(shí)與同學(xué)合辦《新淮潮》雜志以相應(yīng)五四運(yùn)動(dòng)。1922年,臺(tái)靜農(nóng)成為北大研究所國(guó)學(xué)門(mén)旁聽(tīng)生,旁聽(tīng)了魯迅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史》等課程,對(duì)魯迅有了初步認(rèn)識(shí)。1925年4月25日夜,臺(tái)靜農(nóng)在張目寒陪同下第一次拜訪魯迅,魯迅當(dāng)天日記紀(jì)錄道: “夜目寒、靜農(nóng)來(lái),即以欽文小說(shuō)各一本贈(zèng)之。”[1]
1925年,在魯迅的提議、支持下,魯迅與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曹靖華發(fā)起成立未名社,以翻譯出版外國(guó)文學(xué)尤其是蘇俄文學(xué)為主,使得這五位文學(xué)青年正式走上文壇。其中,魯迅與臺(tái)靜農(nóng)交往非常密切。據(jù)《魯迅日記》記載,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臺(tái)靜農(nóng)致魯迅信件有74封,魯迅致臺(tái)靜農(nóng)信件有69封。魯迅甚至曾在致臺(tái)靜農(nóng)信中“吐槽”家庭負(fù)擔(dān)道:“負(fù)擔(dān)親族生活,實(shí)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頭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責(zé)任更無(wú)了期矣。”[2]在魯迅任教廈門(mén)大學(xué)的一年零四個(gè)月中,臺(tái)靜農(nóng)單獨(dú)或與友人一起拜訪魯迅多達(dá)29 次。
魯迅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極為欣賞,臺(tái)靜農(nóng)的第一篇小說(shuō)《懊悔》即由魯迅審閱后交給《語(yǔ)絲》周刊發(fā)表,他的第一部小說(shuō)集也由魯迅審定改名為《地之子》出版,魯迅稱(chēng)贊為“優(yōu)秀之作”[3]。在選編《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shuō)二集》時(shí),魯迅選了臺(tái)靜農(nóng)的《天二哥》《紅燈》《新墳》《蚯蚓們》四篇小說(shuō),與魯迅自己的入選作品數(shù)目相等同為作品最多的作者,可見(jiàn)他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的贊賞。在《<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shuō)二集序》中,魯迅更是高度贊揚(yáng)臺(tái)靜農(nóng)作品道:“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偉大的歡欣’,誠(chéng)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xiàn)了文藝;而且在爭(zhēng)寫(xiě)著戀愛(ài)的悲歡,都會(huì)的明暗的那時(shí)候,能將鄉(xiāng)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méi)有更多,更勤于這作者的了。”[4]
魯迅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的人品也極為肯定,說(shuō)“臺(tái)君為人極好”[5]。1929年5月魯迅回北京時(shí),曾多次與臺(tái)靜農(nóng)會(huì)面,其中一次到了深夜。魯迅多次贈(zèng)書(shū)及《北平箋譜》等與臺(tái)靜農(nóng),還在1932年元旦手書(shū)《二十二年元旦》贈(zèng)臺(tái)靜農(nóng):“云封高岫護(hù)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里又新春。申年元旦開(kāi)筆大吉并祝靜農(nóng)兄無(wú)咎。迅頓首。”1934年魯迅“聞天津《大公報(bào)》記我患腦炎,戲作一絕寄靜農(nóng)”[6],又贈(zèng)送臺(tái)靜農(nóng)一首《報(bào)載患腦炎戲作》:“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眾女心。詛咒而今翻異祥,無(wú)如臣腦故如冰”。臨終前,魯迅還將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寄贈(zèng)給臺(tái)靜農(nóng)。除參與集資刊印此書(shū)的人外,魯迅只給臺(tái)靜農(nóng)和許壽裳兩人贈(zèng)過(guò)此書(shū),可見(jiàn)他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的感情。
“投桃報(bào)李”,臺(tái)靜農(nóng)對(duì)魯迅也極為感恩。1926年,臺(tái)靜農(nóng)將1923至1926年四年間報(bào)刊評(píng)價(jià)魯迅的文章匯編成集,取名為《關(guān)于魯迅及其著作》出版。這是第一本有關(guān)魯迅及其著作的評(píng)論集,書(shū)前有《魯迅自敘傳略》,書(shū)后附有許廣平的《魯迅先生撰譯書(shū)錄》。應(yīng)魯迅的建議,臺(tái)靜農(nóng)將國(guó)外對(duì)魯迅及其著作的評(píng)論刪掉,而加了一篇陳源致徐志摩的信。臺(tái)靜農(nóng)選編此書(shū)目的是“只想愛(ài)讀魯迅先生作品的人籍此可以一時(shí)得到許多議論和記載,和自己的意思相參照,或許更有意味些”[7],主要原因是他愛(ài)魯迅那種被陳源罵為“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wú)完膚——還不肯罷休”的精神,認(rèn)為“這種精神是必須的,新的中國(guó)就要在這里出現(xiàn)。”[8]
1927年劉半農(nóng)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候選人,便由臺(tái)靜農(nóng)轉(zhuǎn)達(dá),魯迅也是通過(guò)回信臺(tái)靜農(nóng)拒絕。雖然魯迅拒絕了提名,但此事可見(jiàn)臺(tái)靜農(nóng)對(duì)魯迅的尊重及兩人關(guān)系的親密。1932年11月,魯迅回北平探視母親,并應(yīng)邀在北平作了五次公開(kāi)演講,時(shí)任北京輔仁大學(xué)副教授兼校長(zhǎng)秘書(shū)的臺(tái)靜農(nóng)全程陪同。臺(tái)靜農(nóng)還陪同魯迅到范文瀾家,邀請(qǐng)魯迅到自己家,以及會(huì)見(jiàn)北平左翼文化團(tuán)體代表。回到上海后,魯迅特意給臺(tái)靜農(nóng)寫(xiě)信感謝道:“廿八日破費(fèi)了你整天的時(shí)光和力氣,甚感甚歉。”[9]魯迅還給許廣平寫(xiě)信道:“我到此后……臺(tái)靜農(nóng)、霽野……皆待我甚好,這種老朋友態(tài)度,在上海勢(shì)利之都是看不到的。”[10]臺(tái)靜農(nóng)還多次為魯迅代買(mǎi)漢畫(huà)像石拓片,如《魯迅日記》中記載,1934年7月1日“得靜農(nóng)所寄漢畫(huà)像等拓片十種”[11]。“在《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到,從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臺(tái)靜農(nóng)通過(guò)友人替魯迅拓印了南陽(yáng)漢畫(huà)像共231幅。”[12]
二、“談到魯迅時(shí)特別有感情”
1936年魯迅去世后,正在山東大學(xué)任教的臺(tái)靜農(nóng)悲痛萬(wàn)分,他立即給許廣平發(fā)了唁電,還寄去100大洋作為奠儀費(fèi)用。唁電中寫(xiě)道:“周師母鑒:頃見(jiàn)報(bào)載,中央社電豫師去世,驚駭萬(wàn)分,然關(guān)于師之起居,向多謠言,頗以為疑。但記載甚詳,似果真不諱,山頹木壞,世界失此導(dǎo)師,不僅師母之慟也……生靜農(nóng)上”。1936年11月1日,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社舉行追悼魯迅大會(huì),臺(tái)靜農(nóng)在會(huì)上介紹了魯迅生平,沉痛悼念魯迅。據(jù)徐中玉回憶:“魯迅逝世那年臺(tái)靜農(nóng)老師正在山大,我們舉辦的追悼會(huì)上他帶病勉強(qiáng)參加了,傷痛之意極深。”
為紀(jì)念魯迅,臺(tái)靜農(nóng)還手抄魯迅詩(shī)作39首分送友人,如將其中一個(gè)長(zhǎng)卷送給了舒蕪。“臺(tái)靜農(nóng)‘困居危城’鈔寫(xiě)‘魯迅師遺詩(shī)’長(zhǎng)卷是尋找精神寄托;而將這長(zhǎng)卷贈(zèng)送給‘不知何年’才能相見(jiàn)的好友舒蕪,顯然是希望用這一份珍貴的禮物來(lái)維系彼此的友誼,互相勉勵(lì),永遠(yuǎn)以魯迅為楷模,永遠(yuǎn)奮進(jìn)。”[13]臺(tái)靜農(nóng)還精工裝裱了魯迅給他的書(shū)信,后經(jīng)保存收錄于《魯迅書(shū)信集》中的有43封。后來(lái),臺(tái)靜農(nóng)將保存的魯迅信件和文稿幾乎全部交給許廣平,只珍藏了魯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xué)校的演講稿即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樣》手稿,以及保存了魯迅送給臺(tái)靜農(nóng)的《二十二年元旦》《報(bào)載患腦炎戲作》等詩(shī)幅。后來(lái),臺(tái)靜農(nóng)和好友魏建功、李霽野、舒蕪等人相聚,也經(jīng)常談及魯迅,“靜農(nóng)先生談到魯迅時(shí)特別有感情”[14]。
1938年10月19日,重慶舉行魯迅逝世二周年紀(jì)念會(huì),臺(tái)靜農(nóng)在題為《魯迅先生的一生》的演講中說(shuō):“我們每一個(gè)黃帝子孫都得學(xué)習(xí)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獻(xiàn)給中華民族!’”抗戰(zhàn)時(shí)期,他還著有回憶魯迅的《魯迅先生的一生》《魯迅先生整理中國(guó)古文學(xué)之成績(jī)》等文章。在任教國(guó)立女子師范學(xué)院時(shí),臺(tái)靜農(nóng)還曾講授過(guò)魯迅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史略》。
1946年臺(tái)靜農(nóng)到臺(tái)灣大學(xué)任教,本欲“歇腳”(臺(tái)靜農(nóng)將自己臺(tái)灣居所命名為“歇腳庵”)的他陰差陽(yáng)錯(cuò)從此定居在臺(tái)北,成為臺(tái)大中文系史上任職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系主任,奠定了該系自由活潑兼容并包的學(xué)風(fēng),被臺(tái)灣學(xué)人譽(yù)為“新文學(xué)的燃燈人”。因?yàn)楫?dāng)時(shí)魯迅名字在臺(tái)灣極為敏感,魯迅至友、臺(tái)靜農(nóng)同事許壽裳便因在臺(tái)灣宣傳魯迅而不明不白地被害,臺(tái)靜農(nóng)從此不再公開(kāi)談?wù)擊斞讣o(jì)念魯迅,乃至后來(lái)被李敖批評(píng)為“愧對(duì)魯迅”。對(duì)此,他曾對(duì)林辰解釋道:“承續(xù)為豫師寫(xiě)回憶錄,雖有此意,然苦于生事,所憶復(fù)不全,故終未能動(dòng)筆也。”
但也許,臺(tái)靜農(nóng)只是將對(duì)魯迅的懷念深藏于心。據(jù)陳昌明教授的《溫州街》一文記載,1989年臺(tái)靜農(nóng)搬家時(shí),臺(tái)靜農(nóng)親自將一尊魯迅塑像抱在懷中搬到新居,“我看到臺(tái)靜農(nóng)老師緩緩起身以雙手抱著魯迅的陶瓷塑像,步履莊重而沉穩(wěn)像《儀禮》中的祀典,一步一步走向二十五號(hào)的宿舍。那是一種極慎重的態(tài)度,一種精神儀式是不能假手他人的,當(dāng)我回家后還感受到這股神圣而隆重的氣氛。”據(jù)梅家玲文章《尋找臺(tái)靜農(nóng)先生的魯迅塑像》考證,這座塑像是來(lái)自香港的大陸走私貨品,1980年由李昂買(mǎi)下送給臺(tái)靜農(nóng),臺(tái)靜農(nóng)一直將其珍藏在里屋。“這尊魯迅塑像鮮為人見(jiàn),卻儼然成為臺(tái)老師多年來(lái)始終心念魯迅,對(duì)其敬之重之的見(jiàn)證。它穿越無(wú)情的政治風(fēng)暴,為那個(gè)逝去的時(shí)代,留下有情的印記。”[15]
另?yè)?jù)施淑教授回憶,臺(tái)靜農(nóng)1990年彌留之際,他要讀魯迅作品,還特別想看《魯迅和他的同時(shí)代人》一書(shū),其中有《魯迅和臺(tái)靜農(nóng)》一章。“最是難忘少年狂”,臺(tái)靜農(nóng)晚年寫(xiě)了《酒旗風(fēng)暖少年狂》等懷舊散文,雖然沒(méi)有直接懷念魯迅,但他對(duì)青年時(shí)期與魯迅等人的交往終究難以忘懷。如施淑教授在《蹤跡》一文中所寫(xiě):“他一生懸念,至死方休的就是魯迅與北京未名社的那些往事了。”
三、“皆師法魯迅”
如上所述,魯迅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非常欣賞盡力培養(yǎng),使得臺(tái)靜農(nóng)成為了著名作家、大學(xué)教授。魯迅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的具體影響大致有三個(gè)方面。
一是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創(chuàng)作的影響。臺(tái)靜農(nóng)本不愿意寫(xiě)小說(shuō),是魯迅主編《莽原》雜志的索稿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起到了直接的催稿作用,如臺(tái)靜農(nóng)在《地之子》后記里所寫(xiě):“其實(shí)在我倒不大樂(lè)于走這一條路。人間的酸辛和凄楚,我耳邊所聽(tīng)到的,目中所看見(jiàn)的,已經(jīng)是不堪了……為了《莽原半月刊》按期的催逼,我仍舊繼續(xù)寫(xiě)下去。”“晚年,臺(tái)靜農(nóng)曾接受陳漱渝的訪問(wèn),‘他承認(rèn)他的創(chuàng)作深受魯迅影響。他原來(lái)愛(ài)寫(xiě)詩(shī),參加過(guò)‘明天社’,后來(lái)讀了周氏兄弟翻譯的《現(xiàn)代小說(shuō)譯叢》《現(xiàn)代日本短篇小說(shuō)集》,又讀了一些莫泊桑、契訶夫的作品,才把創(chuàng)作重點(diǎn)轉(zhuǎn)向小說(shuō)。’(陳漱渝《丹心白發(fā)一老翁》)”[16]魯迅曾直接和臺(tái)靜農(nóng)說(shuō)道:“直至我讀了你的小說(shuō),我才發(fā)現(xiàn)了你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才能,你應(yīng)當(dāng)多寫(xiě)小說(shuō),多寫(xiě)鄉(xiāng)土小說(shuō)。”“魯迅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驗(yàn)指導(dǎo)臺(tái)靜農(nóng)應(yīng)從自己熟悉的生活中開(kāi)掘,多讀外國(guó)小說(shuō)開(kāi)闊視野。臺(tái)靜農(nóng)便埋頭苦讀當(dāng)時(shí)能找到的外國(guó)小說(shuō)集,而使他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的還是魯迅翻譯的島武郎寫(xiě)的《與幼小者》。”[17]此外,魯迅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作品的高度贊揚(yáng),無(wú)疑也會(huì)極大地鼓勵(lì)臺(tái)靜農(nóng)的創(chuàng)作。臺(tái)靜農(nóng)的小說(shuō)主要?jiǎng)?chuàng)作于認(rèn)識(shí)魯迅之后,臺(tái)靜農(nóng)的小說(shuō)集《地之子》《建塔者》由未名社出版,臺(tái)靜農(nóng)的學(xué)術(shù)著作《中國(guó)文學(xué)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魯迅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史略》影響。
二是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作品風(fēng)格的影響。臺(tái)靜農(nóng)早期小說(shuō)內(nèi)容沉重風(fēng)格沉郁極具“魯迅風(fēng)”,被認(rèn)為“從內(nèi)容到風(fēng)格,皆師法魯迅”,尤其是《地之子》頗得魯迅鄉(xiāng)土小說(shuō)風(fēng)韻。香港文學(xué)家劉以鬯甚至認(rèn)為:“20世紀(jì)20年代,中國(guó)小說(shuō)家能夠?qū)⑴f社會(huì)的病態(tài)這樣深刻地描繪出來(lái),魯迅之外,臺(tái)靜農(nóng)是最成功的一位。”后來(lái)臺(tái)靜農(nóng)雖然不再創(chuàng)作小說(shuō),但如學(xué)者孫郁所言:“先生崇尚漢魏文風(fēng),文字與書(shū)畫(huà),流著逆俗氣息,一看便有狂放色彩。一個(gè)經(jīng)歷過(guò)‘五四’新文化的人,由創(chuàng)作走向書(shū)齋,不僅無(wú)絲毫老態(tài),且氣韻生動(dòng),于舊學(xué)之中散出宏闊的氣象,便也證明了其不失魯迅遺風(fēng)。”[18]甚至學(xué)者王德威認(rèn)為臺(tái)靜農(nóng)的歷史著作《晚明講史》是學(xué)習(xí)了魯迅的《故事新編》,“他的對(duì)話(huà)的對(duì)象不是別人,正是寫(xiě)作《故事新編》的魯迅。”[19]《晚明講史》也像《故事新編》一樣借故諷今表達(dá)作者心聲,充滿(mǎn)洞觀世情的清冷智慧和悲憫眾生的溫暖情懷,敘事方式也都比較“油滑”。
三是對(duì)臺(tái)靜農(nóng)人生的影響。在魯迅的影響下,臺(tái)靜農(nóng)早年也是“戰(zhàn)士”,他除了發(fā)表戰(zhàn)斗“檄文”外,還曾任“北平左聯(lián)”常委,曾廣泛接觸左翼人士,因此三度入獄。抗戰(zhàn)勝利后,為抗議國(guó)立女子師范學(xué)院被解散,臺(tái)靜農(nóng)還主動(dòng)辭職,并為學(xué)生題詩(shī)道:“觀人觀其敗,觀玉觀其碎。玉碎必有聲,人敗必有氣。”可“人生實(shí)難,大道多歧”,定居臺(tái)灣后,被監(jiān)視的臺(tái)靜農(nóng)從“戰(zhàn)士”轉(zhuǎn)身為“醉心”于書(shū)法與古典文學(xué)的“隱士”。這正是魯迅一直所痛惜的,這或許也是臺(tái)靜農(nóng)不愿再公開(kāi)提及魯迅的原因之一吧,他內(nèi)心或許的確感到“愧對(duì)魯迅”。但魯迅也曾勸臺(tái)靜農(nóng)潛心治學(xué),如他在1933年寫(xiě)信給臺(tái)靜農(nóng)說(shuō):“大可以趁此時(shí)候,深研一種學(xué)問(wèn),古學(xué)可,新學(xué)亦可,即足自慰,將來(lái)亦仍有用也。”[20]魯迅與臺(tái)靜農(nóng)后來(lái)的通信也大多關(guān)于學(xué)問(wèn),即臺(tái)靜農(nóng)后來(lái)的潛心治學(xué)也未嘗不是魯迅的希望。
四、魯迅與未名社
除了臺(tái)靜農(nóng),魯迅對(duì)未名社及其其他成員也都很關(guān)心。魯迅出資一大半發(fā)起成立未名社,在北大上完課后經(jīng)常來(lái)到未名社,關(guān)心編輯、校改、印刷、經(jīng)費(fèi)等事務(wù),南下后也依然非常支持未名社。李霽野在文章《魯迅先生對(duì)文藝嫩苗的愛(ài)護(hù)與培育》中回憶說(shuō):“魯迅先生對(duì)未名社成員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書(shū)面裝幀,甚至代銷(xiāo)委售方面,費(fèi)去了大量的時(shí)間與精力。先生在看了譯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總用小紙條夾記,當(dāng)面和我們商量改定。”據(jù)李霽野統(tǒng)計(jì),在《魯迅日記》中,關(guān)于未名社的記載多達(dá)七百多條;在現(xiàn)存魯迅書(shū)信中,致未名社成員的信函多達(dá)212封。到1932年未名社解體時(shí),未名社先后出版發(fā)行《莽原》周刊48期、《未名》半月刊24期,出版發(fā)行書(shū)籍33部,其中包括魯迅很多作品,對(duì)翻譯介紹外國(guó)文學(xué)尤其是蘇俄文學(xué)有重大貢獻(xiàn)。魯迅曾肯定未名社譯作道:“在那時(shí)候,也都還算是相當(dāng)可觀的作品。事實(shí)不為輕薄陰險(xiǎn)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水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里卻至今沒(méi)有枯死的。”[21]
其中,韋素園因?yàn)樯眢w不好不便外出而具體操辦未名社社務(wù),故被稱(chēng)為未名社的“守寨人”。魯迅曾推薦韋素園擔(dān)任《民報(bào)》副刊編輯,在南下后讓韋素園接手《莽原》雜志的編務(wù),與韋素園平時(shí)交往也很多,《魯迅日記》中提及他的有130多處。后來(lái)韋素園病情加重,魯迅非常關(guān)心韋素園的健康狀況,多次寫(xiě)信詢(xún)問(wèn)病情,如曾細(xì)心叮囑:“兄咳血,應(yīng)速治,除服藥打針之外,最好是吃魚(yú)肝油。”[22]1929年,魯迅回北京時(shí)三次抽空來(lái)未名社,還專(zhuān)門(mén)去醫(yī)院看望韋素園,他后來(lái)紀(jì)錄道:“素園還不準(zhǔn)起坐,因日光浴,曬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卻好,他很喜歡,談來(lái)許多閑天……接著又感到他終將于死去——這是中國(guó)的一個(gè)損失——便覺(jué)得心臟一縮,暫時(shí)說(shuō)不出話(huà),然而也只得立刻裝出歡笑,除了這幾剎那之外,我們這回的聚談是很愉快的。”[23]1932年8月1日,年僅30歲的韋素園去世,魯迅親自為韋素園書(shū)寫(xiě)了碑文:“君以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嗚呼,宏才遠(yuǎn)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934年7月16日,魯迅又寫(xiě)了文章《憶韋素園君》紀(jì)念韋素園,高度肯定了韋素園的貢獻(xiàn):“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dāng)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guó)第一要他多。”[24]
魯迅與未名社另一骨干李霽野關(guān)系也很密切。李霽野早在阜陽(yáng)第三師范學(xué)校讀書(shū)時(shí),便從《新青年》雜志上看過(guò)魯迅的文章,到北京讀書(shū)后更是仰慕魯迅的風(fēng)采,“魯迅先生的文章表現(xiàn)著鮮明的人格,讀時(shí)使人覺(jué)得親切得很,仿佛作者不僅是一個(gè)可以教導(dǎo)自己的良師,也可以成為推誠(chéng)相見(jiàn)的益友”[25]。后來(lái),李霽野在張目寒的引薦下見(jiàn)到魯迅,其翻譯受到魯迅很大鼓勵(lì),并在魯迅資助下考入燕京大學(xué)讀書(shū)。之后,他也與魯迅經(jīng)常會(huì)面談話(huà)、通信,魯迅致李霽野信有53封,“每次和先生的談話(huà),我都覺(jué)得爽快,仿佛給清晨的涼風(fēng)吹拂來(lái)一樣。”[26]魯迅去世后,李霽野陸續(xù)寫(xiě)了一些紀(jì)念魯迅的文章,并于1956年出版了《回憶魯迅先生》一書(shū),記述了魯迅對(duì)他等文學(xué)青年的培養(yǎng)情況,認(rèn)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美德——謙虛、樸素、慷慨、忠貞,和新興階級(jí)的優(yōu)良品質(zhì)——英勇、剛毅、樂(lè)觀、堅(jiān)定——融合成魯迅先生的獨(dú)特風(fēng)度。”[27]李霽野還保存了魯迅《朝花夕拾》的手稿,臺(tái)靜農(nóng)保存的《娜拉走后怎樣》手稿上最后一則題跋也出自李霽野之手,他題道:“毛錐粒粒散珠璣,奠定文壇萬(wàn)載基。墨澤猶新音容杳,愴然把卷徒唏噓。”1984年4月6日,天津市文聯(lián)和作協(xié)召開(kāi)座談會(huì)慶祝李霽野從事文學(xué)活動(dòng)六十周年,李霽野在《答謝詞》中回憶道:“在我的青年初期,我有幸親聆偉大的文學(xué)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的教誨,我的文學(xué)活動(dòng)是在先生的領(lǐng)導(dǎo)下開(kāi)始的,若是取得些微的成績(jī),那同先生的教導(dǎo)和鼓勵(lì)分不開(kāi)。”晚年,李霽野還倡導(dǎo)在天津設(shè)立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寫(xiě)了《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一書(shū),被魯迅研究專(zhuān)家陳漱渝稱(chēng)之為“霽野師的親見(jiàn)、親聞、親歷,為研究中國(guó)現(xiàn)代社團(tuán)史和文學(xué)史者所必讀。”
魯迅作品《阿Q正傳》由曹靖華介紹給俄國(guó)人王希禮翻譯到俄國(guó),這是魯迅作品傳入蘇俄的開(kāi)始。由此,魯迅和曹靖華密切交往,曹靖華成為與魯迅關(guān)系最親密的人之一。據(jù)《魯迅日記》記載,兩人書(shū)信來(lái)往多達(dá)292封,曹靖華是魯迅通信僅次于許廣平的人。在這些信中,兩人互相關(guān)心對(duì)方的家人家事、身體狀況,甚至相互代寄藥物和食品,魯迅還將自己的各種心事、難事“交代”給曹靖華,可見(jiàn)魯迅將曹靖華視為自己至交。魯迅約曹靖華翻譯蘇聯(lián)作家綏拉菲莫維奇的名著《鐵流》,親自校訂此譯作并寫(xiě)后記,又自掏一千大洋出版此書(shū)。他不斷鼓勵(lì)曹靖華積極翻譯蘇聯(lián)文學(xué),使得曹靖華后來(lái)成為我國(guó)翻譯介紹俄蘇文學(xué)的大家。魯迅還為曹靖華父親書(shū)寫(xiě)了“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這是魯迅除了給韋素園之外寫(xiě)的唯一碑文。魯迅臨終前三天寫(xiě)了《曹靖華譯<蘇聯(lián)作家七人集>序》,高度評(píng)價(jià)曹靖華的為人和譯著,說(shuō)為曹靖華寫(xiě)序“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還說(shuō)“靖華就是一聲不響,不斷地翻譯著的一個(gè),而他的譯作,也依然活在讀者們的心中。”[28]第二天,魯迅又給曹靖華寫(xiě)了一封近千字的信,這是魯迅生平的最后一封信。魯迅去世后,曹靖華收到魯迅給他的信時(shí)悲痛失聲,此后也一直悼念、感激魯迅。他在中法大學(xué)追悼會(huì)講演中哀悼“魯迅死得太早”,稱(chēng)魯迅的死“失掉了我們的燈塔”,并寫(xiě)了《我們應(yīng)該怎樣來(lái)紀(jì)念魯迅》等文章。晚年,年近九旬的曹靖華,還坐在魯迅故居的書(shū)房中拍了一張照片以示紀(jì)念。
對(duì)于韋素園的弟弟韋叢蕪,魯迅本來(lái)也很關(guān)心。在魯迅鼓勵(lì)下,韋叢蕪創(chuàng)作了愛(ài)情長(zhǎng)詩(shī)《君山》。魯迅讀后很贊賞,特請(qǐng)畫(huà)家林風(fēng)眠為此詩(shī)稿設(shè)計(jì)封面,又請(qǐng)版畫(huà)家司徒喬作插圖十幅。受此鼓舞,韋叢蕪又創(chuàng)作了小說(shuō)《校長(zhǎng)》,魯迅則將此小說(shuō)推薦發(fā)表在《小說(shuō)月報(bào)》上。但后來(lái)主持未名社社務(wù)的韋叢蕪生活腐化,和未名社其他成員產(chǎn)生矛盾,導(dǎo)致未名社解體。魯迅也因此聲明退出未名社,“韋叢蕪以后進(jìn)一步墮落,魯迅先生在書(shū)信和談話(huà)中表示很深的惋惜,并處處可以看出他對(duì)韋素園的情誼。”[29]后來(lái),韋叢蕪著有《合作同盟》,“夢(mèng)想著未來(lái)的中國(guó)是一個(gè)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并送此書(shū)請(qǐng)教魯迅。魯迅在致臺(tái)靜農(nóng)的信中對(duì)此說(shuō):“立人(韋叢蕪)先生大作,曾以一冊(cè)見(jiàn)惠,讀之既哀其夢(mèng)夢(mèng),又覺(jué)其凄凄。昔之詩(shī)人,本為夢(mèng)者,今談世事,遂如狂酲;詩(shī)人原宜熱中,然神馳宦海,則溺矣,立人已無(wú)可救;意者素園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難言也。”[30]幾十年后,韋叢蕪從《魯迅全集》中看到魯迅的這封信而感慨道:“魯迅先生寥寥數(shù)語(yǔ),說(shuō)得多么中肯,多么令人感動(dòng)!”他為此寫(xiě)有詩(shī)歌《憶魯迅先生》:“五十年來(lái)一覺(jué)醒,先生有怨我心驚!”
五、“為青年開(kāi)路”
對(duì)于和未名社合辦《莽原》的狂飆社,魯迅原本也非常關(guān)心盡力指導(dǎo)。狂飆社領(lǐng)袖高長(zhǎng)虹當(dāng)時(shí)平均每月到魯迅家六次以上,兩年時(shí)間內(nèi)兩人會(huì)面不下一百次。對(duì)于高長(zhǎng)虹個(gè)人,魯迅也特別關(guān)照,破例給予高長(zhǎng)虹編輯費(fèi)用。魯迅還選編高長(zhǎng)虹的散文和詩(shī)集為《心的探險(xiǎn)》,親自設(shè)計(jì)封面,編入《烏合叢書(shū)》,為此都累得吐了血。他還和高長(zhǎng)虹一起選編自己老鄉(xiāng)許欽文的短篇小說(shuō)集《故鄉(xiāng)》,并請(qǐng)高長(zhǎng)虹為集子寫(xiě)序。這是魯迅唯一一次請(qǐng)青年作家作序,可見(jiàn)魯迅對(duì)高長(zhǎng)虹的器重。即使后來(lái)魯迅與高長(zhǎng)虹以及狂飆社失和,魯迅依然在《<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shuō)二集序》中高度評(píng)價(jià)了高長(zhǎng)虹和狂飆社:“1925年10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現(xiàn),這其實(shí)不過(guò)是不滿(mǎn)于《京報(bào)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shè)《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bào)》發(fā)行,聊以快意的團(tuán)體。奔走最力者為高長(zhǎng)虹,中堅(jiān)的小說(shuō)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鉞、向培良三個(gè);而魯迅則是被推為編輯的。”[31]原本年輕氣盛的高長(zhǎng)虹后來(lái)在1940年8月發(fā)表的長(zhǎng)文《一點(diǎn)回憶——關(guān)于魯迅和我》中感慨說(shuō):“我和魯迅在《莽原》時(shí)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飆》周刊在上海出版后,有過(guò)一番爭(zhēng)論,不過(guò)以后我們都把它忘了。1930年以后,他的光明行動(dòng),我在國(guó)外也時(shí)常為之激賞、慶幸。”他認(rèn)為魯迅是位天才作家,承認(rèn)魯迅“為青年開(kāi)路”,贊揚(yáng)魯迅的作品鑒賞力。
魯迅對(duì)其他很多文學(xué)青年也給予了力所能及地指導(dǎo)、幫助,與眾多青年作家關(guān)系密切。如魯迅與自己學(xué)生孫伏園在《晨報(bào)副刊》上密切合作,選編老鄉(xiāng)許欽文的短篇小說(shuō)集《故鄉(xiāng)》,寫(xiě)下《悼柔石》《為了忘卻的紀(jì)念》悼念柔石、白莽等“左聯(lián)”五烈士。“魯迅先生對(duì)青年期望很殷,培養(yǎng)很勤,但是他既不虛夸,也不姑息。他對(duì)青年的要求很?chē)?yán)格,無(wú)論在言行方面,還是在工作方面。”[32]除了本文所述外,受過(guò)魯迅培養(yǎng)、直接影響的青年作家至少還有馮雪峰、丁玲、胡風(fēng)、巴金、曹白、黃源、張?zhí)煲怼⒔浴⒁恕⑹捾姟⑹捈t、黎烈文、唐弢、蕭乾等人,魯迅關(guān)心、幫助過(guò)的其他青年人就更多了。
魯迅原來(lái)相信進(jìn)化論,“總以為將來(lái)必勝于過(guò)去,青年必勝于老人”[33],而原本對(duì)青年寄予厚望。因此,他雖然認(rèn)為青年不必“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niǎo)導(dǎo)師”[34],但他自己很樂(lè)意當(dāng)青年“導(dǎo)師”,非常關(guān)心、培養(yǎng)文學(xué)青年,指導(dǎo)了狂飆社、未名社、朝花社、沉鐘社等文學(xué)社團(tuán),在北大、女師大、廈門(mén)大學(xué)、中山大學(xué)任教時(shí)與學(xué)生也密切交往。
但狂飆社領(lǐng)袖高長(zhǎng)虹對(duì)魯迅的反戈一擊,尤其是“四一二”事變帶給魯迅的沖擊,以及后來(lái)創(chuàng)作社“小將”對(duì)魯迅的攻擊,讓魯迅對(duì)青年逐漸失望。他認(rèn)為“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duì)于別個(gè)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wú)顧惜”[35],“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lái)便時(shí)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wú)條件的敬畏了。”[36]
所以,后來(lái)魯迅對(duì)一般青年不太密切交往,只對(duì)胡風(fēng)、馮雪峰、黃源、巴金、蕭軍、蕭紅等信任的文學(xué)青年交往多些。但魯迅“此后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37],也還是盡可能地幫助青年,甘做“梯子”。1930年3月27日,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曾說(shuō):“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duì)于此一節(jié),我也曾熟慮,倘使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38]
“愿有英俊出中國(guó)”,魯迅原本對(duì)文學(xué)青年充滿(mǎn)關(guān)愛(ài)竭力培養(yǎng)寄予厚望,后來(lái)雖然對(duì)青年逐漸失望,認(rèn)為僅有青年的進(jìn)化是不夠的更重要地是社會(huì)的進(jìn)化,但他依然甘做“梯子”盡力幫助文學(xué)青年。“于無(wú)聲處聽(tīng)驚雷”,正是魯迅的“潤(rùn)物無(wú)聲”,讓臺(tái)靜農(nóng)、曹靖華、胡風(fēng)、蕭軍、蕭紅、巴金等大量青年作家脫穎而出,像一聲聲驚雷一樣震驚神州大地。這正如魯迅自己的詩(shī)所言:“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fā)春華。”
注釋?zhuān)?/strong>
[1] 魯迅: 《日記·十四〔一九二五年〕四月》,《魯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62頁(yè)。
[2] 魯迅: 《書(shū)信·320605 致臺(tái)靜農(nóng)》,《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08頁(yè)。
[3] 魯迅:《二心集·我們要批評(píng)家》,《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246頁(yè)。
[4] 魯迅: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shuō)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 263 頁(yè)。
[5] 魯迅: 《書(shū)信·331219 致姚克》,《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 520頁(yè)。
[6] 魯迅:《日記·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三月》,《魯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439頁(yè)。
[7] 臺(tái)靜農(nóng):《關(guān)于魯迅及其著作》,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頁(yè)。
[8] 臺(tái)靜農(nóng):《關(guān)于魯迅及其著作》,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頁(yè)。
[9] 魯迅: 《書(shū)信·321130 致臺(tái)靜農(nóng)》,《魯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348頁(yè)。
[10] 魯迅: 《書(shū)信·321120 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 343頁(yè)。
[11] 魯迅: 《日記·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七月》,《魯迅全集》第 15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460頁(yè)。
[12] 商金林:《生而不有 為而不持———臺(tái)靜農(nóng)對(duì)魯迅的敬慕和追隨》,《魯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3] 商金林:《生而不有 為而不持———臺(tái)靜農(nóng)對(duì)魯迅的敬慕和追隨》,《魯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4] 舒蕪:《憶臺(tái)靜農(nóng)先生》,《新文學(xué)史料》,1991年第2期。
[15] 梅家玲:《尋找臺(tái)靜農(nóng)先生的魯迅塑像》,《魯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6] 汪修榮:《不盡往事盡風(fēng)流:民國(guó)先生風(fēng)華》,團(tuán)結(jié)出版社,2024年,第38頁(yè)。
[17] 陶方宣、桂嚴(yán):《魯迅的圈子》,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108頁(yè)。
[18] 孫郁:《魯迅遺風(fēng)錄》,江蘇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41頁(yè)。
[19] 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tái)靜農(nóng)的<亡明講史>》,《現(xiàn)代中文學(xué)刊》,2020年第4期。
[20] 魯迅: 《書(shū)信·331227 致臺(tái)靜農(nóng)》,《魯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 533頁(yè)。
[21] 魯迅: 《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70 頁(yè)。
[22] 魯迅: 《書(shū)信·270108 致韋素園》,《魯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8頁(yè)。
[23] 魯迅: 《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68頁(yè)。
[24] 魯迅: 《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70 頁(yè)。
[25] 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第2頁(yè)。
[26] 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第9頁(yè)。
[27] 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第55頁(yè)。
[28] 魯迅: 《且介亭雜文末編·曹靖華譯<蘇聯(lián)作家七人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68頁(yè)。
[29] 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第22頁(yè)。
[30] 魯迅: 《書(shū)信·330628 致臺(tái)靜農(nóng)》,《魯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413頁(yè)。
[31] 魯迅: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shuō)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 258頁(yè)。
[32] 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第22、23頁(yè)。
[33] 魯迅:《序言》,《三閑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頁(yè)。
[34] 魯迅:《導(dǎo)師》,《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9頁(yè)。
[35] 魯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473頁(yè)。
[36] 魯迅:《序言》,《三閑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頁(yè)。
[37] 魯迅:《序言》,《三閑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頁(yè)。
[38] 魯迅: 《書(shū)信·300327 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226頁(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