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門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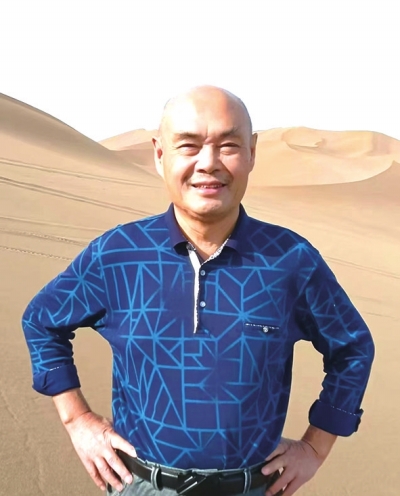
吳永煌,新疆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曾任新疆報告文學學會秘書長、理事。新疆兵團作家協會會員,新疆兵團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新疆兵團文藝審讀專家。烏魯木齊市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專委,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在《綠洲》《散文選刊》《中國農墾》《中國退役軍人》《中國環境報》《百花園》《伊犁河》《回族文學》《新疆日報》《兵團日報》《西藏日報》等報刊發表大量散文和報告文學作品,出版或合著散文集和報告文學集5部,散文和報告文學在疆內外多次獲獎。
紅其拉甫山谷,不同于其他的山谷。它地處“兩山一原”(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和帕米爾高原)結合部,海拔高,氣候寒,土地貧,進出難,屬新疆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干縣南端,素有“血谷”之稱,在波斯語中稱之為“死亡之谷”。“萬山堆積雪,積雪壓萬山”,是它的真實描寫。紅其拉甫口岸和海關邊防檢查站就在這山谷之間,海拔高度4733米。這里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口岸。今年46歲的孫超,用28年的熱血和執著,在這里創造出一個充滿生機的“生命之谷”,譜寫了一曲感人肺腑的青春之歌。——題記
“脫了軍裝也是兵”
1996年,18歲的孫超完全可以有其它選擇,而他毅然從河北保定地區應征入伍,遠赴新疆喀什當了一名武警戰士。新兵訓練結束后,他本可以有其他選擇,而他又毅然選擇了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
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地處帕米爾高原,氧氣含量不足平原一半,風力常年在七八級以上,最低氣溫達零下40多攝氏度,被當地塔吉克族稱為“血染的通道”,也被世人稱為“生命禁區”。
“4個月的新兵訓練結束后,我坐了十幾個小時的汽車,來到紅其拉甫邊防站。第一眼看到的是邊防檢查站旁邊山坡上醒目的標語:祖國在我心中,青春獻給邊防,在皚皚的白雪映襯下,顯得格外顯眼。我的心不知不覺地一下子跳動起來。”這是孫超回憶戰友們歡迎時的情形。
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被贊為“天界紅哨”,先后被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授予“艱苦奮斗模范海關”、“模范邊防檢查站”榮譽稱號等。孫超看重的就是這些榮譽,
他很快理解了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的新老“四特精神”。新世紀前的老“四特”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新世紀的新“四特”是:特別講政治,特別守紀律,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
起初,他被分配到炊事班當一名炊事員。工作之余,他先后在海關邊防檢查站所轄的水布浪溝、皮拉里、紅其拉甫這些前哨站走了一遍。體驗了高寒邊防的艱苦生活,聆聽了老戰士的動人事跡,孫超被深深地感染了。
3年的服役生活就要結束了,是回河北美麗的白洋淀湖畔老家,還是繼續留在帕米爾高原的紅其拉甫?他又一次面臨著人生的選擇。
家鄉地處華北平原,物產豐饒,湖光山色,既有著名的白洋淀景區,又有京津冀大都市環繞,交通便捷,生活富足。尤其是這里還有他的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父親和待他而嫁的女朋友。
“到時候就回來把婚結了,早點成家立業過日子。”到紅其拉甫后的第三個春節,孫超回家探望老父親時,父親急切地說。老父親能不急嗎?在老家村里,像孫超一樣歲數的小伙子都娶妻生子了。
“能不能延遲退役?”站領導找到孫超征求意見。其實,站領導看重了他的為人品格,想留他試建檢查站溫室蔬菜大棚,探索解決站上吃菜難的問題。孫超沒有馬上回答,因為這個問題也不是他一下就能回答得了的。
“誰在老家搞過溫室蔬菜大棚?”站領導在老兵即將退役的一次站務會上問。新世紀之前,生活在帕米爾高原的人還沒有聽說過溫室蔬菜大棚,見過更無從說起。
“我見過,但沒有搞過。”孫超知道,站領導這是情急之策。他心想:當過兵的人都有這樣一句話:“脫了軍裝也是兵!”何況自己還沒有正式退役。溫室蔬菜大棚應該是炊事班分內的事,沒走之前,自己還是炊事兵。他看沒人吭聲,就冒昧地說了一句。其實,他也想試試領導的態度,試試溫室蔬菜大棚。
領導高興地又一次找到孫超,說:“見過總比沒見過強。這事還是想交給你。”還用挽留的口氣懇切地說,“等把大棚搞起來了,一定熱烈歡送你退役,你看行不行?”
孫超徹底被感動了,很認真地對領導說:“領導這么信任我,那我就不走了,留下來看看咱紅其拉甫能不能闖出一條種植溫室蔬菜大棚的新路。”
孫超,這個燕趙男兒,再一次做出了人生的選擇,留在了帕米爾高原,留在了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他要用自己的青春韶華,在高寒險峻的山谷,綻放出青春無悔的光彩。
“我把青春賭在這里”
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離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簡稱“塔縣”)縣城有130公里,縣城距喀什市還有420公里。塔什庫爾干屬于高寒地區,正常條件下無法種植蔬菜。這里吃菜要靠從喀什市拉運。檢查站每個月要到喀什市采購一次生活用品。550公里,兩天一個來回。冬天,站里官兵吃的都是一路被凍傷的白菜、蘿卜、土豆這三大傳統蔬菜。夏天,吃的都是一路熱風吹蔫的蔬菜;肉蛋拉到站里,雞蛋基本壞損一半,肉也泛起刺鼻的酸味,做菜的時候只得多放把花椒壓味。如果從站里再拉往幾個都在百公里外的前哨站,情形就更加糟糕了。
在紅其拉甫種植蔬菜,成了當地塔吉克族老百姓和一批批駐守官兵的夢想。
在塔吉克族語中,塔什庫爾干就是“石頭之城”的意思。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周圍都是高聳的雪山,出站大門前,倒有一小片稍微平緩的坡地,卻遍布砂礫,終年覆蓋著難以融盡的積雪。
萬事開頭難。孫超和站里“八大員”就在靠著邊防站院墻的東南角,拉開了建設溫室蔬菜大棚的序幕。白天工作,晚上飯后睡前突擊干活,刨撿石頭,挖運沙土。
正是8月,紅其拉甫的天就開始冷了。山上融雪少了,山谷里小河的水也快枯竭了,檢查站里的小型水力發電站,只能勉強滿足白天和晚上生活用電。
“用車燈照著。”孫超提出了這樣一個建議,可以只爭朝夕地建溫室蔬菜大棚。
巍巍的昆侖,莽莽的高原,寒風陣陣,夜色茫茫。此時的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院墻東南角一片雪亮,鍬鎬聲叮當作響,在空寂的高原山谷,就像天外來聲。燈光下,塵土飛揚,人影綽綽,宛如月球幻影。
幾天下來,孫超和戰友們一樣,手掌都打起了血泡。功夫不負有心人,大家齊心協力開出了一畝荒地。
他和戰友們把檢查站皮拉里前哨站廢棄老營房的墻磚、鋼窗拉了過來,砌起了一座溫室蔬菜大棚圍墻。
1999年開春,孫超精心地在大棚里撒下了第一把種子,也看到了第一顆破土而出的幼芽。他欣喜極了,高原終于有了第一芽綠色!他天天鉆進大棚里去等啊,盼啊,而等來的看到的卻是失望。韭菜細黃細黃,趴在地上,像個黃毛丫頭;蘿卜開著艷麗的花朵,拔出來一看,根像細短鐵棒;西紅柿像一現的曇花,開出金黃的花朵就凋謝了,都是一些無果花。
第一年的溫室蔬菜大棚種植蔬菜試驗就這樣以失敗告終。
細心的孫超發現,圍墻南面的蔬菜要比東北墻角的要好些;南面離采光玻璃近的菜尖蔫了,而遠一點的要好些。蔬菜長不好還可能是高原晝夜溫差大,引來的河水太涼,中午太陽又正毒,把離采光玻璃近的菜尖灼傷了。他斷定:這是溫度的差異造成的,所以,種的蔬菜只能朝南,才能最大限度地采光。他把自己的分析匯報呈給領導。領導覺得很有道理,信任地對他說:“你準備一下,去昌吉新疆邊防總隊后勤農場學習一個月,我們在家里把大棚的朝向重新搞好,你回來就專門負責大棚種菜。”孫超的合理化建議讓單位領導看到了希望。
誰也沒有想到,2000年實驗又一次失敗了。
孫超蹲在大棚里,看著那些“殘兵敗將”似的菜苗,傷心地哭了。他覺得對不起領導的信任和培養,對不起同事們的付出和支持。
“孫超啊孫超,你什么時候能把這些問題徹底解決好?”他恨得罵自己。
經過再三分析,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溫室蔬菜大棚的土是從山上滑下來的土沙,沒有積淀,沒有肥力。必須改良土質;葉菜種得要離采光玻璃遠一點,以免灼傷;昌吉是平原地區,紅其拉甫是高寒地區,季節、氣候、光照、水溫等多種因素不同,不能照本宣科,而要因地制宜。
“站長,我把青春賭在這里,就不相信種不出來像樣的蔬菜來。”2001年開春,孫超像發了夢怔一樣,勇氣十足地給站領導立下了軍令狀,他決心要用自己的青春,在這“生命禁區”種出一片充滿生機的春綠。
他從牧民家里買來牛羊糞施進菜地里,以提高土壤肥力;他從烏魯木齊拉來了舊軍被,拼接成避光御寒的大棚棉被;他在大棚里砌起了5個土爐子,以提高和調劑大棚里面的溫度;他把床鋪也搬進了大棚,以便對大棚里溫度實時監測記錄……
功夫不負有心人。5年過去了,孫超終于在大棚里成功地種出了第一批蔬菜,而且一下就達到了13個品種。帕米爾高原真正有了第一抹最美的綠色,春天一樣的綠色。
他像第一眼見到兒子一樣,喜上眉梢。站領導和同事們也紛紛走進大棚,向他道喜,感受這來之不易的綠色。
這5年,孫超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精心呵護著溫室蔬菜大棚。一個大棚棉被就有50多公斤,需要4個人才能抬起來,拉開蓋好。掀蓋一次都得一個小時。
這5年,他做了大量溫室蔬菜大棚記錄,每3小時觀察記錄一次,為帕米爾高原發展大棚蔬菜積累了第一手資料。
這5年,他對帕米爾高原風力風向做了大量記錄。高原的風又多又大,如果一年不吹破、吹壞塑料溫室大棚和玻璃溫室蔬菜大棚四五次,那就不叫高原的風。
解決了溫室大棚蔬菜的種植問題后,新的問題又擺在了孫超的面前。時代在發展,蔬菜種植環境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從玻璃大棚到塑料大棚,再到陽光板大棚,蔬菜種植環境在逐漸改善。陽光板大棚也確實解決了原來抗風、耐寒、保溫能力差的問題,但陽光板時間長了就會老化,透光率下降,影響蔬菜的正常采光生長。沒有很好的光合作用,蔬菜就不能正常生長。多年的種植,也導致蔬菜重茬,遺傳病蟲害頻發,嚴重影響著蔬菜的品質。于是,他在擴大溫室蔬菜大棚種植面積的基礎上,又引進同類品種的不同種子,對大棚蔬菜進行倒茬種植,效果不錯。
陽光板的問題,他卻無能為力,但可以嘗試建一座地暖式溫室蔬菜大棚,既解決采光問題,又可以常年種植蔬菜,讓紅其拉甫一年四季可以看到綠色。在經過深思熟慮后,孫超大膽地向領導提出合理化建議。孫超想,如果這個地溫式溫室蔬菜大棚試種成功,那帕米爾高原就永遠有了春天一樣的綠色。
孫超未雨綢繆,他聯系到山東濟寧的一家生產恒溫機的廠家,并把帕米爾高原的相關資料提高供給他們。他請求該廠家設計適合帕米爾高原溫室大棚的恒溫機,并把地熱溫度改控在30至40攝氏度之間。如果按照原來設計的恒溫機溫度,會燙傷蔬菜的根系,導致死亡或早衰。
在鋪設管道時,孫超為保障土壤和溫室的溫度,將覆蓋管道的土層控制在60厘米厚,中間鋪上一層間隔打好孔的反光膜。這樣土壤透氣保溫,蔬菜不爛根,溫室里也有了溫度。大棚兩頭山墻用苯板加填爐渣,保證有1.2米厚,利于保溫。此外,為了管理方便,孫超自己動手研制了自動卷簾機,卷起或放下保溫棉被只需要10分鐘,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后來,他又將卷簾機改成遙控的,只要在可控范圍內,天氣一旦發生變化,隨時可以應急處置。
孫超在溫室蔬菜大棚取得巨大成功后,又提出了畜禽菜果共生,種養循環的理論,并大膽實踐,也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借鑒云南高原光足溫暖畜禽養殖大棚的經驗,并結合帕米爾高原缺照寒冷的實際,孫超在當地建起了畜禽養殖大棚,還建起一座畜禽化糞池,為蔬菜種植源源不斷地提供有機農家肥。
孫超的這一創新,獲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他在而立之年,用青春熱血種出了帕米爾高原上最鮮美的綠色,讓高原看到了生命的春天,造就了“萬仞冰峰、十畝江南”的綠色奇跡。
“我會一直堅守在帕米爾高原”
2004年,塔什庫爾干縣遭遇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災害。道路中斷半個多月,一棵白菜賣到50元。檢查站領導作出指示,只要群眾前來,哪怕站里省點,也要發放給前來買菜的群眾。孫超溫室大棚里的蔬菜,這時候就是老百姓的救命菜,“定心丸”!
菜!菜!!菜!!!
帕米爾高原必須種植蔬菜!綠滿高原,是這里所有群眾的夢想,更是孫超的夢想。
災害過后,塔縣縣委書記帶著四大班子來到孫超的溫室蔬菜大棚學習取經,要求各部門把孫超種植溫室蔬菜大棚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全縣,并大手筆地在當地建100座溫室蔬菜大棚,讓帕米爾高原上這座小城成為綠色家園,春天的世界。
他積極投身扶貧攻堅工程,先后資助10余戶特困家庭,捐款捐物30多萬元,向塔吉克族群眾傳授種養殖技術,并幫助他們辦起了牦牛、綿羊養殖合作社。塔什庫爾干縣從此也能吃上自己生產的新鮮蛋肉。不僅如此,在孫超的幫助下,塔什庫爾干縣還創造了帕米爾高原種植南瓜的歷史。種出的南瓜,可以存放一年。孫超還在大棚種植檸檬、金橘、三七等,利用這些果樹為蔬菜遮擋紫外線,在呵護蔬菜生長的同時,也打破了帕米爾高原不能種植南方果樹的神話。
帕米爾高原有了綠色蔬菜,點燃了人們生活的希望。為了充分利用好這些來之不易的食材,孫超又把富余的蔬菜切曬成干菜,腌制成咸菜,既滿足站里干警不同口味的需要,還通過銷售干菜和咸菜給當地居民,為檢查站獲得了收益。
塔吉克族是一個對鷹充滿崇敬的民族,把英雄稱為雄鷹。塔吉克族老鄉感激地把孫超稱為“高原雄鷹”,這是對他的最高稱譽。
自學成才的孫超聲名不脛而走,人們紛紛前來取經。
戰友孟宏斌拜他為師,跟著學了5年種植溫室蔬菜大棚,成為帕米爾種植溫室蔬菜大棚的第二人。轉業回到黃土高原后,結合黃土高原的特點,孟宏斌發展溫室蔬菜大棚,成為當地溫室蔬菜大棚的帶頭人。
他的跟班徒弟已經達到十幾個,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內地的,也有帕米爾高原的,他們在高原撒播出了一片片綠色,組成高原的壯闊綠錦。
同處帕米爾高原的吐爾尕特邊防檢查站也曾試驗種植溫室蔬菜大棚,但一直效果不佳,幾乎準備放棄。聽說孫超成功種植溫室蔬菜大棚的事跡后,慕名派戰士王水朋從460多公里外趕來取經。聽了王水朋種菜的情況后,孫超認為在種植方法和管理上功夫沒有做到家。他說:“種菜和軍人列隊一樣,要有精氣神,橫是橫,豎是豎。菜種不出來,地就要荒,地一荒,人就懶。”后來,王水朋也成了吐爾尕特邊防檢查站種植溫室蔬菜大棚的領軍人物。
如今的塔什庫爾干縣,居民自建的溫室蔬菜大棚星羅棋布,政府統建的50多座溫室大棚、100多座安居房庭院拱棚,像皚皚的昆侖雪山連綿起伏,蔚為壯觀,呈現出春意盎然的色彩。只要有空,孫超就會去居民的溫室蔬菜大棚義務傳經送寶。
孫超讓帕米爾高原擁有了春天的綠色,成了高原種植溫室蔬菜大棚的專家型人物。地方企業三次高薪聘請,他三次拒下高原。昌吉新疆軍區后勤基地請他去當技術指導,北京邊防局后勤基地領導打電話請他過去工作,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在參加寧波海警學院培訓學院全國轉隸高級士官學習時,他是21名學員中唯一一個搞種植的,在受訓期間,還應邀為培訓的學員授課。鑒于孫超的出色表現,學院希望他能留下管理實踐基地。特別是2018年軍改,父母和妻子都希望他回老家開辦企業,老家縣政府也根據他榮立的11次一、二、三等功,為他考慮好了工作單位,可他毅然選擇繼續堅守國門。他說:“再多的錢都有花完的時候,但離開了紅其拉甫,就永遠失去了組織。我已經把青春給了紅其拉甫,根也扎在了紅其拉甫,走了就對不起領導和戰友同事,更對不起給了我用武之地的帕米爾高原和紅其拉甫檢查站。”
不惑之年的孫超還有夢想。為了帕米爾高原的滿原春色,他從武警部隊轉隸到公安部門,申請留在紅其拉甫海關邊防檢查站。這一待,就是28年。這28年里,他只有春節回過老家,而且還是屈指可數的幾次。春夏秋三季正是蔬菜種植收獲的時節啊。
榮譽屬于英雄。2019年建軍節之際,他被評為“全國模范退役軍人”;2020年,先后被評為全國“十大國門衛士”、“最美奮斗者”;同年,孫超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授予“戍邊衛士”、“勞動模范”等榮譽稱號。
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孫超流著愧疚的眼淚,說了幾件讓人心酸的事。
他每年都要給妻子寄一條裙子,可每次他回去的時候都是冬天,看不到妻子穿。孩子要出生那年的6月20日,他回到了老家,這是他第一次夏天回老家,這也是第一次看到妻子穿裙子。
一次,一位鄰居也問他孩子:“你爸爸什么時候回來?”聰明的孩子說:“下雪了,我爸爸就回來了。”
一次,孫超讓兒子背課文《彩虹》,兒子不情愿地說:“我背了,會哭。”過一會兒,兒子又喃喃地說:“爸爸,你不用彎腰了。他在彩虹這頭,拿著虹給他的菜地澆水。”兒子知道他已經患上了腰脊勞損。
一次,老師讓每個學生寫一個小片段,他兒子就寫了一個《長大保衛祖國》的片段,實際上,也就寫了一句話:“爸爸冬天回來培養我。”
看到兒子的作文,孫超流淚了。
他說:“在帕米爾高原種出蔬菜,讓高原人民能看到吃到新鮮蔬菜,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只要黨和祖國需要,我會一直堅守在帕米爾高原,讓綠色布滿紅其拉甫山谷,讓綠色布滿帕米爾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