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人文學術的“定海神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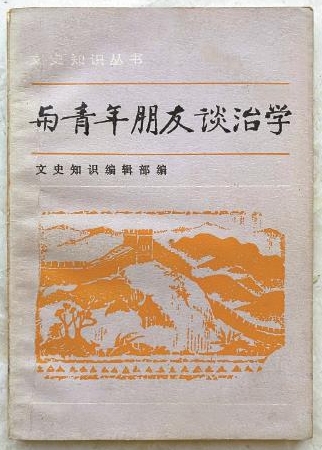
《與青年朋友談治學》文史知識編輯部 編 中華書局
與青年談治學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高中畢業之后的那個暑假,悠閑、漫長又有些無聊。記得一拿到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我就把做過的數理化習題集送去廢品站論斤賣了。回到家里,父親指著書架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以后我這里的書你可以隨便看看。
念初中時,我也算是文學愛好者,感興趣的書找來就讀,并不總盯著幾本名著。俄羅斯詩歌和中國現代左翼作家的小說,還真看了不少。整個高中幾乎沒什么自由閱讀的時間,所以“隨便看看”四個字一下子給我松了綁。我趕緊去補看了先前沒有讀過的一部分魯迅作品,再加上兩本唐詩、一本宋詞。把《史記》中感興趣的傳記都看了,又通讀了一遍《莊子》,算是自我挑戰。
進了中文系,就不再是一般的文學愛好者了,如果要走研究的路,還得做些準備。我心里這樣盤算著,就去書架里翻找,結果發現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插在最靠邊的地方,淡紫色的封面上,寫著一行字——“與青年朋友談治學”,由文史知識編輯部編撰。
現在的圖書,假如起這樣一個書名,估計青年朋友會棄若敝屣。這書“爹味”太濃!你是誰?有什么資格與青年談治學?青年憑什么要聽你談治學?再說了,你和青年做朋友,征得他們同意了嗎?
那個年代,還沒有“爹味”這個詞,我對那“味”兒也沒那么抗拒。倒想看看書里那些與青年朋友談治學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佳作背誦如流是一種基本功
翻開一看,這是20位學者談治學經驗的文章合集,依次是夏承燾、朱東潤、鄭天挺、余冠英、周祖謨、李學勤、何其芳、龐樸、蔡儀、何茲全、陸宗達、楊志玖、周一良、曹道衡、繆鉞、林庚、劉葉秋、王運熙、辛安亭、韓國磐。這些人里,我聽說過的只有夏承燾、朱東潤、何其芳和王運熙。夏先生是詞學大師,朱先生是《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教材的主編,何先生我讀過他的散文,王先生在復旦中文系任教。
我也知道,要治學首先要用功,讀書要勤奮刻苦,但究竟怎么個刻苦法,這些學者的文章還是震撼到我了。這種震撼是從書中第一篇夏承燾先生自述的一個細節開始的:“因為覺得自己‘笨’,那就必須勤奮。從十五歲到二十歲,是我讀書很努力的時期。當時,一部《十三經》,除了其中的《爾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過。記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從椅子上摔倒在地。”(《我的學詞經歷》)夏先生不是詞學大師嗎?家中的書架上擺著他的《唐宋詞人年譜》《月輪山詞論集》,他早年居然還背過《十三經》!對于《十三經》,當時的我,屬于“沒吃過豬肉,但見過豬跑”,知道這是儒家最核心的十三部經典。除了字書性質的《爾雅》,夏先生竟然都背誦過。這是什么概念呢?或許有人說,科舉時代的讀書人,不是都能背誦儒家經典嗎?但問題是,夏先生生于1900年,他是考入溫州師范學校接受新式教育的,下這么大氣力背誦《十三經》,并不是為了科舉,也沒有老師逼迫,而是為了給自己未來治學打一個堅實的底子。除此之外,他還竭盡全力,博覽群書:“我在求學階段,舉凡經、史、子、集,乃至小說、筆記,只要弄得到書,我都貪婪地看。我體會到:如果不刻苦讀書,就談不上治學,談不上什么科學研究。”(《我的學詞經歷》)我由此知道,研究詞學,只讀詞是不行的,必須經、史、子、集樣樣都看,有精力的話,基本經典最好能夠背誦。多年之后,我的博士生導師劉永翔先生建議我去讀讀夏先生的《天風閣學詞日記》,并感嘆說:“夏先生是很用功的。”導師的這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是不是只有夏承燾先生對于背誦格外重視呢?并不是。翻看后面的篇章,才知道背誦是好多學者都非常強調的。如劉葉秋先生說:“詩文佳作,背誦如流,更是一種基本功。有幾百篇詩文爛熟于胸,張口即來,才能得心應手地運用,為閱讀和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略讀與精讀》)有些學者表面上不主張背誦,其實骨子里還是看重,比如周祖謨先生說:“前人講究背文,現在我們不提倡背誦,要求熟讀,熟讀可以成誦。古代一些大文學家,對一些名著都反復念,念得非常熟。至今還有學者能背《漢書》,這很受用。”(《談治學的方法》)要熟讀成誦,能背《漢書》很受用,這才是周先生要講的重點。后來,我讀到俞平伯、葉嘉瑩等先生的回憶,都說早年背誦詩詞讓他們如何受益,我覺得都是前輩真切的體會。
背誦之外,學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談到熟讀經典的重要性。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繆鉞和陸宗達先生的自述。繆先生說:“對于史書,《資治通鑒》是我最愛讀而且熟讀的書(當我十二三歲肄業于高小時,國文教師張卓園先生經常指導我讀課外書籍,他特別指出《資治通鑒》的重要,要我讀時以硃筆斷句,并且在小本中記下疑難與心得)。”十二三歲,自己斷句讀《資治通鑒》,今天想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可是當年繆先生就是這樣讀書的。
更令人驚駭的是陸宗達先生,他講述乃師黃侃(季剛)先生親口告訴他《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的重要作用:“《說文》是一部用形音義結合的方法解釋晚周經典的專書,是研究文字訓詁學的基礎,攻‘小學’,由《說文》起步最為便捷。”(《基礎與專攻——跟從黃侃師學習〈說文解字〉的體會》)《說文》對于學習古代漢語的意義,我也有所耳聞,但讓我吃驚的是黃侃接下來的教學方法:“黃侃先生偏偏不讓我去讀那么多的書。他只是告訴我,先把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連讀三遍,基本上把《說文》的詞句點斷、讀懂,然后拋開段注,光讀《說文》白文。”段注《說文》可不是小說,其枯燥繁難人所共知,即使是小說,連讀三遍也受不了啊。更何況黃侃讓陸宗達讀的是沒有斷句的段注《說文》,讓他自己點斷文句。對于學習古代漢語來說,這就好像唐僧師徒只有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才能取得真經。陸宗達后來果然成為一代訓詁學大師。上個月,北京師范大學剛剛舉行了紀念陸先生誕辰12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高度評價他對《說文》的研究。
讀了繆、陸二位的自述,我就知道自己要去點讀古書,而不是僅僅讀現成的標點本。后來讀了博士,聽我的老師們說,當年徐震堮先生教授《漢書》課程,就是直接讓研究生們點讀《漢書》的。一部書能點下來,自然就理解了。假如讀不懂,就根本點不斷。這是讀古書的基本方法。
大學者放下架子講述治學的經驗
《與青年朋友談治學》中每個學者的治學領域和途徑有所不同,但我發現他們都反反復復講這樣幾個道理:一是要熟讀古代文史領域最基本、最核心的經典;二是要博覽群書,盡量拓寬視野,超越狹隘的單一專業;三是做學問要下苦功夫,從文獻資料出發,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四是有些特殊領域的知識,無論做哪門學問都要了解一點。比如書中龐樸先生的那篇《和初學者談“天”》,說的是文史學者必須懂得基本的古代天文和歷法知識,他舉了《詩經》里“七月流火”的例子。這里的“火”并不是太陽系的行星火星,而是心宿二的大火星,是一顆恒星。“七月流火”說的是,夏歷七月,大火星西行,表示暑往寒來,天氣開始轉涼了。后來經常看到有人誤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氣炎熱,慶幸自己較早了解了這一知識。我們在給《中國詩詞大會》命題的時候,有一道題還問“七月流火”到底是指天氣炎熱還是天氣轉涼,考問的就是古詩中的這個天文知識。
這本書還讓我有了“文史不分家”的觀念。作者們都在說,學習古代文學,要懂得典章制度,而學習古代史,也需要利用詩文的資料。現在常說人文學術要跨學科,其實中國古代學術本來就是跨學科的。書中作者們屢屢引用顧炎武的論述,后來,我參與校點整理《顧炎武全集》,分到的任務是《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地理書的校點,切實感受到顧炎武這樣的大學者跨學科的非凡成就。
《與青年朋友談治學》出版于1983年,是中華書局《文史知識叢書》之一種。所收錄的文章,都是之前曾發表在《文史知識》雜志上的。這本雜志專門請權威學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給當時社會上的文史愛好者、學習者撰寫普及文章。大學者放下架子,平易近人地講述自己的治學經驗和方法,當年對我這樣將要入門的年輕人是多么有幫助啊!今天AI時代來臨,勢不可擋。很多人說,似乎不用讀那么多書了,更不必背誦經典,寫文章也不用字斟句酌了,AI不是只需要幾秒鐘就生產出來了嗎?此時此境,重讀這本《與青年朋友談治學》,重溫這些大師的自述,我的心緒很是復雜。陷入對自己青年時代的回憶的同時,似乎又在人文學術的滔天巨浪里,找回了一根“定海神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