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宇慧:當下廚做飯不再是必選項,我們損失了什么?

陳宇慧(田螺姑娘)
陳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喜歡逛菜市場和做飯,寫了十多年菜譜。新書《誰來決定吃什么》以食物為線索,不僅書寫了她對食材的獨特認知、實用的烹飪心得,更聯想到了傾注其中的情感與勞動,由此勾連起對人與生活本身的思考。在她看來,食物從來不只是食物,而是回憶的甬道,是愛的表達與創造,是無序生活里我們的生存確定;同時,食物也意味著掌控與權力,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日常。她說,在“吃什么”以外,“誰來決定吃什么”才藏著生活最真實的答案。近日,澎湃新聞就相關美食話題專訪了陳宇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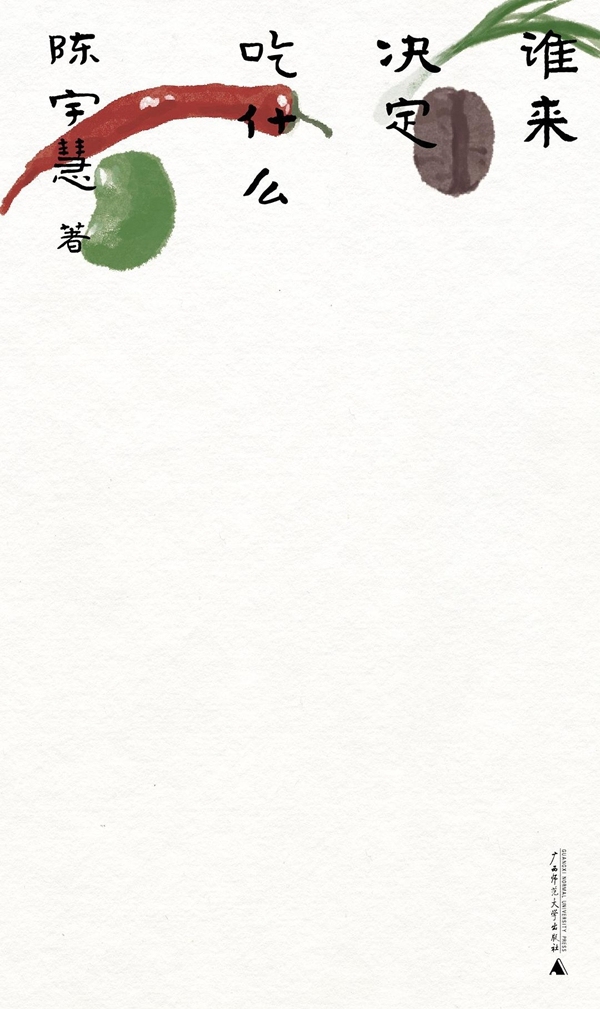
澎湃新聞:您之前出版的書都是食譜,寫作《誰來決定吃什么》這樣的美食隨筆的契機是什么?
陳宇慧:菜譜是一種工具書,在確定要下廚之前再行查詢翻看就行了,所以打開菜譜的契機是確定自己要下廚做飯。但現在因為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的變化,下廚做飯已經不是一個必備選項,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在這個變化里我們損失了什么?這是我想在《誰來決定吃什么》這本書里探討的問題。
澎湃新聞:美食主題的散文集、隨筆集以前曾經很流行,而現在是肉眼可見的衰落了,您覺得為什么現在大家不那么熱衷這類書了呢?在您的閱讀中,有沒有特別喜歡的美食散文作家或者作品?您覺得好的美食散文寫作大概是什么樣的一種寫作?
陳宇慧:在我心里,好的飲食散文是既有信息量,又能引發共鳴的作品。它既不能和讀者距離太遠,讓人覺得這是自己永遠無法企及的生活,最好也不要自說自話,讓讀文章的人體會不到和被描述的食物、被描述的這頓飯相關的氛圍、人物關系和社會背景。
早年間閱讀的陳夢因(筆名:特級校對)和殳俏都能給我這樣的感受,我從他們的文章里認識到了很多新鮮的食物,甚至知道這些食物怎么烹飪更得宜,于是我對食物越來越向往,想吃到,也想買來試著自己做做看。
但這樣的飲食散文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設定,隨著社交媒體越來越發達,和食物有關的信息逐漸被簡化成誘人的圖片和視頻,以及博主們大快朵頤的表情。品味食物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但除此之外的情緒和氛圍幾乎都被忽略了,刷到社交媒體上這樣的帖子或視頻,感受到的是一種很直觀的刺激,但很難沉浸到情緒里產生共鳴。
食物的表達被簡化了,這是我覺得飲食散文逐漸衰落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談到了如今家庭飲食習慣中的所謂“去醬油化”,包括“去肥肉化”,這個其實還可以羅列很多,都是應今天的健康標準或者說健康焦慮而產生的變化,在您看來,這些變化會使那些傳承已久的家常菜失去應有的風味而日漸同質化嗎?
陳宇慧:我家餐桌上的“去醬油化”并不是自己特意為之的,只是隨著離家時間越來越長,我接觸到了很多不同的菜系,也不那么依賴和迷戀湘菜的口味,日常烹飪里使用醬油的頻次越來越低了。而書里提到的“去肥肉化”可能和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現在的豬肉越來越瘦,二是大家越來越不敢吃肥肉。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的訴求,好像餐桌上的肥肉就慢慢變少了。
這并不是說產生這樣的變化有什么不對,家常菜本身就在不斷地流變中。一般家常菜不會特意遵循味型,也不會花費太多精力獲取一些食材和調料,家常菜就是隨意的、有什么用什么的。家常菜和餐廳菜式最大的區別就是:幾乎不會被標準化。所以家常菜也不會有同質化的風險,它甚至很難被歸類總結。
澎湃新聞:您在《標簽化的食物》一文中以您家鄉的湖南菜為例,說原本為了解膩、提香、開胃用法多樣的各色辣椒,現在都被簡化成了最好買、最穩定的小米椒,對地方菜的標簽化正在使得地方菜的豐富性不斷折損,我原本以為這種情況只是針對旅游區或者開到外地的地方館子而言,為什么在當地也會這樣呢?
陳宇慧:以我的家鄉長沙的本地湘菜變化情況為例,作為近年來炙手可熱的旅游城市,外地游客對湘菜的刻板印象和覓食需求,已經很大程度影響到了長沙本地餐廳的菜式風格。而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游客們在打卡本地餐廳之后,好評或者差評也會直接影響餐廳運營狀態,所以迎合游客的口味,對餐廳運營者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在菜式傳播乃至傳承的過程中,一家熱門餐廳會比一個個的小家庭起到的作用要大。假設一道菜在餐廳點單的時候很受歡迎,可以輻射到少則幾百,多至幾十萬人,而且本地和外地的其他餐廳也會模仿這道菜,這道菜就越來越火。但一道菜要火,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它口味清淡平衡,粗暴概括的話,口味重、有記憶點的菜會更容易火。
在這樣的傳播路徑下,地方菜的豐富性肯定是會被折損的,但這也是不可避免的過程。
澎湃新聞:書中論及的“濾鏡下的食物”也是個有趣的話題,拍照發社交媒體幾乎已經成為現在前置于吃的必選項,好看大于好吃,擺拍、打卡重要過品嘗菜色本身,寧愿犧牲最好的賞味時刻,但沒拍就等于沒吃,這會不會嚴重影響餐飲的服務取向?讓餐飲朝著形式大于內容的方向一去不復返?
陳宇慧:是這樣的。餐廳的服務取向現在已經被社交媒體和點評網站“綁架”了,菜的口味沒法通過手機傳播,但好看的菜值得拍照上傳社交媒體,服務出了問題容易被發帖“避雷”,點評網站上的評分也會直接影響餐廳的自然流量。在點評網站上,一家餐廳如果獲得了一個差評,幾乎需要二三十個好評才能把評分拉回來。但一條爆款探店視頻,可能會讓餐廳短時間內爆紅,營業額翻上好幾番。
以前在活動范圍內會有更多社區餐廳,菜式變化不大,價格平易近人,是不想做飯的時候隨意吃一口的好選擇。而現在食客們選擇餐廳的邏輯,經常是先在各種社交媒體上搜索感興趣的餐廳,再看看評價,最后才決定去不去。社交媒體可以決定一家餐廳的生存狀態,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生鮮電商平臺不只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打破了食材和食材之間的關系”,這話要怎么理解?
陳宇慧:從前不管是買菜還是買衣服,都需要和攤主或者服務員溝通這個食材好不好,這件衣服是什么材料的,再稍微還幾句價。隨著電商越來越發達,我們在購物的時候已經大幅減少了和人打交道的環節。現在不需要出門就可以自助下單幾乎任何商品,想退貨也只用在平臺上點幾下,確實非常方便。
但食物尤其是生鮮食物始終是非標品,省略了人和人的溝通之后,對食物的狀態很容易產生迷惑,哪個部位的豬肉更適合炒著吃?圓包菜和尖包菜口味有什么區別?很多時候和攤主的溝通是了解食物的一個重要途徑,對于廚房小白來說更是如此。
對于食物的很多想象也是在菜市場產生的,看到一條非常新鮮的魚,自然就會開始想象中午要如何烹飪它。如果想做個蔥油的做法,那下一步就是在菜市場尋覓最好的小香蔥。生鮮電商平臺雖然非常方便,但很限制我們的想象力。生鮮平臺上的食材照片都像身份證上的標準照一樣,看來看去都差不多,經常會逛上半天也不知道今天最想買的食材是什么,更別提有搭配靈感了。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喜歡逛菜市場的人,對于傳統菜市場不可挽回的衰落是不是尤其覺得可惜?在您而言,傳統菜市場的核心魅力是什么呢?
陳宇慧:便捷,豐富,多變。我把“便捷”放在菜市場魅力的第一步,如果菜市場不能坐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而需要特地前往的話,大部分人去菜市場買菜的頻次就會降低很多。現在大城市的城市規劃好像把商圈、住宅、學校全部分離,各歸各位,菜市場也在被設計好的位置。可能有些菜市場甚為寬敞,但不方便去的菜市場,再寬敞也顯得寂寞。
我也喜歡傳統菜市場里食材的豐富和多變。到了絲瓜的季節,會有農民直接挑著擔子賣自家種的頭茬絲瓜,個頭非常參差,但味道格外甜。昨天剛剛買過的蠶豆,今天再去菜市場就遍尋不見,晚餐已經設想好的菜單不能執行,需要馬上想出其他的應對方案,這樣的狀況在我看來都很有樂趣。餐桌上有些新菜式,生活就不是那么一成不變。
現在很多大城市的菜市場,每個攤位的食材都差不多,甚至一年四季都差不多。在這樣的菜市場里買菜,能做的菜都差不多,那去不去菜市場其實也差不多。
澎湃新聞:預制菜也是這些年討論很多的一個話題,從食物的層面您認為預制菜、料理包的目的是保證食物的下限,而不是追求食物的上限,再往深了說,您覺得這代表著我們的“預制生活”,能就此談談嗎?
陳宇慧:前些年可能很多朋友不那么了解預制菜和料理包,哪怕在餐廳里吃到了用料理包加熱的菜式,也以為是現做的。而預制菜的概念會比料理包更廣,預先處理、預先制備、預先烹飪都是預制菜的一部分,廣義的預制菜無論對于家庭廚房還是商業餐廳來說都是很有必要的。
不過一旦把討論的范圍限定在料理包之后,就會發現這個討論會有很多無法解決的矛盾:首先花錢去餐廳吃到的飯菜,不料想餐廳把料理包加熱就上菜了,這和自己購買料理包加熱之后的成品沒有區別;如果餐廳保證現點現做,那就很難保證每次的出品水準一致,總會有高有低;甚至現點現做導致等餐時間會比較長,在快節奏的生活模式下,人們對于這種耗費時間的等待變得越來越無法忍受;料理包的口味調配是一致的,很難被改變,也會抹殺食材和調料的精細風味,酸菜魚里的酸菜再加熱,都不怎么香了。
這些都是我們的生活現狀:我們既想要效率,又想要穩定,那就只能先保證下限了。如果要追求食物和生活的更多可能,就要犧牲對于效率和穩定性的追求,從根源上拋棄預制方式,這幾乎是不可能達到的。
澎湃新聞:隨著做飯技能的普遍弱化,一方面做飯對很多人來說已經不再是必選項,可以用外賣、外食來取代,也可以用方便食品、速凍食品隨便應付一頓,但另一方面,認真做飯又變成了一部分人生活態度、儀式感的來源,變成了非常治愈的一件事,超越了以前日常家務的性質,這類人在您的粉絲中應該很多,您覺得在今天的生活背景下,做飯為什么能帶來這樣的治愈感?
陳宇慧:在談到做飯帶來的治愈感之前,可能得先看看現在的生活節奏帶來的不得已。很多朋友在工作日的時候用外賣、外食來取代自己做飯,并不是他們不想下廚,而是菜市場的遠去、通勤距離拉長導致不得不如此。周末做飯本來也可以是非常日常的行為,但在忙碌的工作日的襯托下,變得好像有儀式感了。這樣的生活節奏真的好嗎?如果想把做飯作為日常必選項,真的可以做到嗎?
所以在這樣的生活節奏下,認真做飯與其說是治愈,不如說是一種反抗,在不得已的節奏中真正把握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反抗。
澎湃新聞:最后來聊聊“一人食”的話題吧,您在書中以“麻煩”來形容一人食,但同時“一人食”也代表著一種隨著時代變化而產生的更個人化、更自在的生活方式,如何在充分享受“一人食”的自在的同時使之不那么“麻煩”,這是不是餐飲產業鏈條和我們個人都可以思考的問題?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陳宇慧:根據我的觀察,現在很多餐廳的桌均人數都有下降的趨勢,以前有很多大型聚餐,但現在2-4人的小型聚餐會更多一些。當然這里面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影響,但總體來說趨勢是這樣。而且可能很多朋友也有感覺,我們小時候會經常參加大家庭的聚餐,現在從年夜飯開始,這種聚餐范圍也越來越小,參與人數越來越少。不過如果對比這些用餐規模的區別,也能聯想到很多細節的差異。比如人少的時候不會制作/點單大菜,點幾個小菜就夠了;人少的時候考慮的餐廳類型也和從前不同,不必再考慮大型酒樓,和朋友們吃點簡單的家常菜或者小吃都不錯。
隨著生活節奏的進一步加快,以及大城市里距離感增強,人與人的關系愈發疏離,外食中的“一人食”可能會越來越多。這當然是隨著時代變化而產生的更個人化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必應酬不喜歡的親朋,一個人吃飯也更容易決策。但從餐飲產業鏈條上來看,現在的一人食選擇明顯還不夠豐富,除了大量快餐之外,很難想到更豐富的一人食選擇。
比起外食來說,自己在家下廚的“一人食”可能更為困難。就像我在書里提到的,一個人的飯菜是最難做的,無論采購還是切配,下廚的工作量并不會因為用餐人數減少而減少太多。所以一個人吃飯更容易選擇外食和外賣,工作一忙起來就更是如此了。
我想這并不是簡單的建議可以解決的問題,希望有更多的余裕可以好好做飯、好好吃飯,在當下的生活節奏里可能確實是種奢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