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空間的鄉(xiāng)土記憶——讀黃風(fēng)散文集《野水的季節(ji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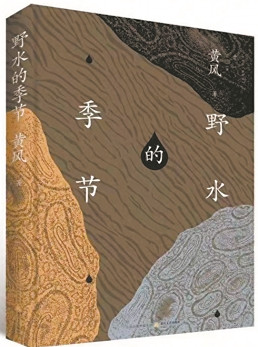
我很少對一本書如此著迷,就像品讀一只宋代建陽窯黑釉茶盞上精美的兔毫斑,總是給人一種自然流暢、恬淡雅致、神奇美妙的感覺,當(dāng)然我說的是《野水的季節(jié)》。該書根植于基層社會生活,以微小的切口、廣闊的視角,關(guān)注鄉(xiāng)村社會變遷與發(fā)展。這部書融歷史性、文化性和情感性于一體,匯集二十一篇浸潤黃土氣息敦厚樸實的文字,作品意象流淌著風(fēng)的雋永與豐沛,其跳蕩的結(jié)構(gòu)、綿密的質(zhì)地紋理,將鄉(xiāng)土生活刻畫得豐滿而生動。文本由個體敘事轉(zhuǎn)化為集體敘事,使之成為我們民族共同記憶的一種精彩呈現(xiàn)。黃風(fēng)的散文可與劉亮程的作品相媲美,其意象運用、情感表達(dá)、敘事方式具有相近的文學(xué)藝術(shù)特征。而在物象轉(zhuǎn)喻生命體的解讀中,黃風(fēng)的散文更貼近亨利·梭羅《瓦爾登湖》中的湖水張力。他的作品暈染出生活細(xì)小的襞褶,不僅托舉起杏花、瓦松、燕子、高粱、大水缸瑣碎而紛呈的詩意,也將窯煙、打谷場、黃土墻以及夏日青蛙的叫聲挺立起來,它們能把黑夜硬生生戳個口子,為懸浮于城市浪潮中的鄉(xiāng)愁提供了錨定的坐標(biāo),也為黃土地上迷茫的人找到根植未來的種子。
《野水的季節(jié)》開篇便是一行揪人眼球的文字:“風(fēng)竄著屋脊,扒在煙囪口上,又貓?zhí)柫艘灰埂!倍潭淌嘧郑捎谩案Z”“扒”“貓?zhí)枴比齻€鮮活的動詞,讓一幅鑲嵌在歲月深處微微泛黃的鄉(xiāng)村情景圖躍入讀者心里。僅這一句,便讓我想起威廉·華茲華斯的一句詩:“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高高飄浮。”倘若把前后連貫起來,會驚覺這竟然是一首珠聯(lián)璧合很美的詩。如此意境幽邃或溫婉清麗的文字,在《野水的季節(jié)》里比比皆是。作者在書中將物性敘事與生命意識交融,對非人類存在物的描寫,呈現(xiàn)出鮮明的生命意識。這種擬人化敘事不是簡單的修辭技巧,而是隱喻鄉(xiāng)土社會中物我共融的認(rèn)知方式,以物性敘事既活躍文學(xué)的自主性,同時借以傳達(dá)作者樸素的思想情懷。
文學(xué)的價值不僅在于反映現(xiàn)實,更在于通過語言的藝術(shù)重構(gòu),使我們能夠以新的方式看見和理解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書中收錄的散文充滿了童趣,在詩性表達(dá)方式的基礎(chǔ)上,疊加進(jìn)方言俚語,這些詞匯如同一個個文化密碼,承載著特定地域的生活經(jīng)驗。作者將民間傳統(tǒng)修辭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既有視覺形象的直觀性,又帶著孩童特有的擬人化想象。譬如,描述強(qiáng)勁的風(fēng),“將院中空閑啃得滿是牙痕”;再譬如,描寫人,“女人的嗓門又大開了,能開出坦克來”“把話當(dāng)棒槌扔出去”。這種從鄉(xiāng)村生活中生長出來的意象,賦予作品一種民間歌謠般的韻律感,帶著泥土的溫度,和孩童般質(zhì)樸的營造力,在寫實之外獲得了詩性美的升華。
黃風(fēng)的文字會給予自然萬物神圣的靈性,或者說超越于自然的力量和人格魅力。譬如《兩頁書》中,講述果園里的一口老井,那股“飄揚著白胡子”的白氣,“像土地公抽了一口煙不吐,張大嘴享受著由它散去。”老井被描述為具有生命節(jié)律的存在,它深植于農(nóng)耕文化四季輪回的土壤中,體現(xiàn)了農(nóng)耕社會人們對于傳統(tǒng)生產(chǎn)方式的依賴與敬畏。當(dāng)老井被推土機(jī)“活埋”了,它帶來的疼痛不僅是對于古老文明的碾壓吞噬,還抹掉了一整個鄉(xiāng)土世界的記憶回聲。在童謠“二月二,剜小蒜;狼一半,狗一半”的簡單韻律中,復(fù)雜的社會變遷和文化傳承恍惚獲得了釋然的情感魅力。作者以這種創(chuàng)新的獨特語言質(zhì)地,和富有生命力的敘事,構(gòu)建起既具體又超越的文學(xué)世界,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幅幅充滿活力的鄉(xiāng)村圖景。這些圖景介于現(xiàn)實與幻想之間,筑起令人愉悅的美學(xué)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方言土語的狂歡、民俗信仰的遺存、道德倫理的規(guī)訓(xùn)與鄉(xiāng)村文化的嬗變相互交織,形成了一部微縮的鄉(xiāng)村史詩,其字里行間滲透著對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化、生產(chǎn)方式、鄉(xiāng)俗民居的人文觀照與深刻思考。作者又擅用短句,富有節(jié)奏感的流暢語言,宛若潺潺溪流,或者多樣化的音樂,強(qiáng)化了文本的韻律,有效地傳達(dá)出作品的主題內(nèi)涵。譬如,“干鬼爺名副其實的干,尤其是一張瓦刀臉,干蹦蹦的顴骨能當(dāng)痰盂,并且能敲出裂紋來。”文中鄉(xiāng)土敘事的短促節(jié)奏,融入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意識提煉與創(chuàng)新,既保留了地方色彩,又通過文學(xué)語境使其獲得生動鮮活的可理解性。
黃風(fēng)的散文往往會在多重感官體驗中,拓寬拓深敘事空間,以感官書寫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xué)拓?fù)鋵W(xué)。譬如《古鶴下街N號》的一段文字:“我的耳朵早開小差了,專注的不再是剃刀聲,而是那咕嘟的肉聲,被線一樣串了,一串一串的。我的嗅覺從鼻孔鉆出,有時攆著一縷香氣,在晦暗的屋壁上窮追不舍。”這段文字中,作者運用了聽覺、嗅覺與視覺等全息感官敘事,通過擬人化和通感手法,使文本敘述獲得了近乎神話的敘事品質(zhì),銚子里裊裊升騰的肉味,與父親垂涎游弋的眼神,構(gòu)成清苦歲月里一幀生動而奇異的素描。這種感官書寫形成的獨特文學(xué)拓?fù)鋵W(xué),橫向的空間維度上,是那鍋“咕嘟咕嘟”的燉肉;縱向的維度上,卻是“我”的視線隨著“一串一串”的肉香,在屋壁上一直窮追不舍。作者通過敘述者的感官體驗,將現(xiàn)場的時空坐標(biāo)縫合起來,使讀者的閱讀體驗升華為一種絕妙的身體感知。
書中《八月的禾場》卻是將勞動敘事,賦予了儀式化編碼。隨著“呼隆隆聲響起,后面的攆著前面的,蹚出一條直趟趟的道來”。作者對秋收的勞動過程描寫,具有明顯的儀式化特征。文中插入隱匿了人物形象的對白,讓余音如蛛網(wǎng)般纏繞在讀者的心里。從田間收割“熟得像老姑娘了”的高粱的老農(nóng),到滿載莊稼浩浩蕩蕩的馬車,再到禾場上“起山”的人、一垛垛“勾肩搭背”的莊稼垛子、趕鳥人、場把式、扇車手等,作者將生產(chǎn)勞動一層一層儀式化的敘事策略,使文本超越了單純的技術(shù)描述,進(jìn)入了人類文化學(xué)的闡釋空間。尤其是場把式趕著三頭驢碾場的情景,以及扇車手啟動扇車時對它“從頭到尾邊看邊摸”,之后一聲吆喝“開扇啦——”整個禾場一下子活了起來,活的不僅僅是人與物,活的更是骨子里向往美好生活的精氣神。當(dāng)禾場上的莊稼轉(zhuǎn)變?yōu)椤皦烆^”一樣的糧食,整個過程更是充滿了儀式感:場把式手中的鞭花反復(fù)耍成“8”字,扇車手“打”扇車時搖把與手之間形成節(jié)奏美的互動,在“耍”與“打”不斷重復(fù)的揮汗勞動中,獲得了某種舞蹈般的節(jié)奏感,勞動被描摹為一種莊嚴(yán)的表演和文學(xué)轉(zhuǎn)喻,而勞動者的日常則被賦予了形而上的美學(xué)意義。
多變的鄉(xiāng)土?xí)r空象征性結(jié)構(gòu),不僅深化了主題內(nèi)涵,提升了敘事層次,同時也增強(qiáng)了作品的感染力。譬如,在《一道老菜的“流水志”》中,作者給予了這道老菜深刻的社會意義。在時間維度上,“歲末歸來,年啪啪甩袖凈過身上風(fēng)塵”,而一道“涼拌綠豆芽”的老菜,便承載起冬去春來的農(nóng)耕時序。文章以“女人”培植綠豆芽的過程作為微小敘事切口,隱喻鄉(xiāng)村生活簡樸中獲得的滿足感與幸福感,以及辭舊迎新樸素的時間觀,這與城市追求“年”的氛圍和機(jī)械性的時間形成鮮明對比,暗示鄉(xiāng)土中傳統(tǒng)的價值觀、生產(chǎn)生活方式與自然節(jié)律的和諧關(guān)系。空間結(jié)構(gòu)同樣富含象征:“女人”擔(dān)心綠豆芽長得慢,但是她聽不到豆芽生長的聲音;而孩子入睡時,不僅可以聽得到豆芽的生長聲,還把它帶入夢中。這種在情緒渲染上連通與阻隔的辯證意象,將物質(zhì)空間轉(zhuǎn)化為心理空間的隱喻,折射出代際間的精神隔膜,以及過去與未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若即若離的矛盾與統(tǒng)一。
《野水的季節(jié)》通過多層次的文學(xué)手法,將具體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轉(zhuǎn)化為承載文化記憶的文學(xué)事件,并以此為媒介,探索人與自然、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個體與社會的復(fù)雜關(guān)系。鄉(xiāng)土作為一種文學(xué)意象,既是具體的存在,又是傳統(tǒng)文化象征。作者以敏銳的感官捕捉力和豐富的文學(xué)想象力,將鄉(xiāng)土敘事轉(zhuǎn)化為文學(xué)版圖的一種圖騰,使技術(shù)描述升華為生命敘事,這正是這本書最可貴的創(chuàng)作特質(zhì)。在城市化快速推進(jìn)的當(dāng)下,《野水的季節(jié)》以文學(xué)書寫,保存了正在消失的生產(chǎn)方式與生活經(jīng)驗,使其獲得超越具體時空的美學(xué)價值與文化意義。
生活往往會讓我們的記憶褪色,但是那些承載著我們記憶的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永遠(yuǎn)不會褪色,它是照亮我們生生不息的生命火炬。《野水的季節(jié)》所煥發(fā)出來的榮光,是億萬華夏兒女的共同記憶,可以增強(qiáng)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也為我們留存了一本值得珍藏的鄉(xiāng)土中國精神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