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當(dāng)下詩歌現(xiàn)狀與未來的對(duì)話 ——批評(píng)家羅振亞訪談

羅振亞,1963年出生,黑龍江訥河人,南開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南開大學(xué)穆旦詩歌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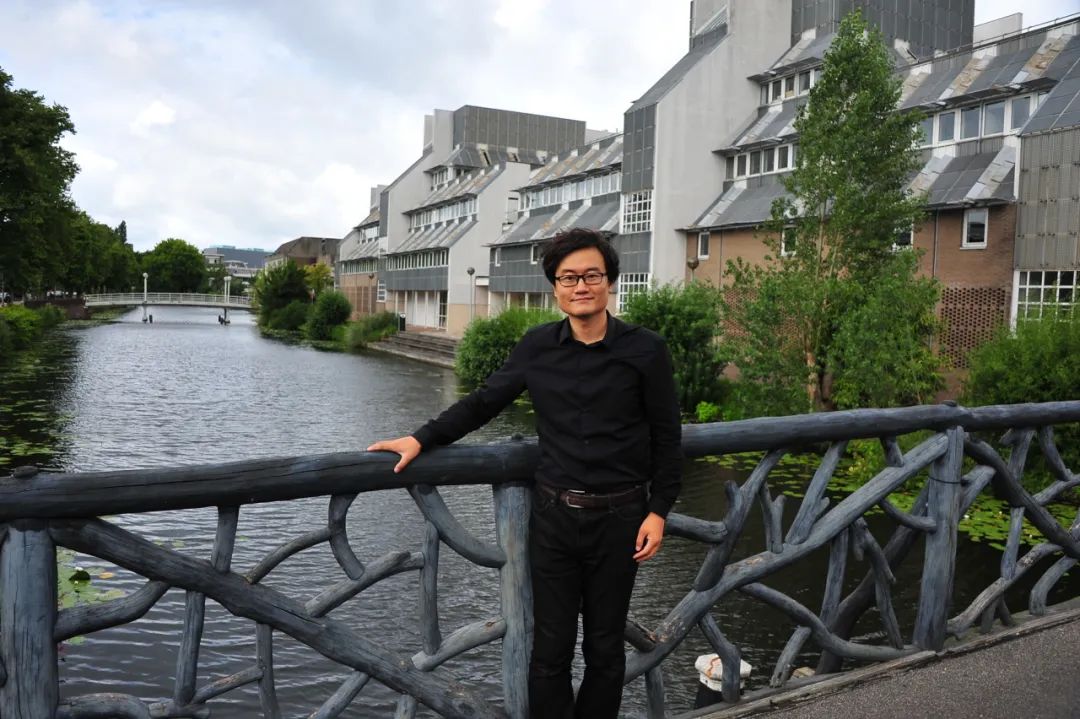
盧楨,1980年出生,天津人,南開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盧 楨:羅老師您好,非常榮幸有機(jī)會(huì)與您交流關(guān)于新詩的話題。我曾讀到劉波兄對(duì)您的一個(gè)訪談錄,主題大致是百年新詩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今天,站在新詩又一個(gè)“百年”的開端,我想把話題集中在當(dāng)下的詩歌現(xiàn)場(chǎng)。對(duì)于二十一世紀(jì)詩歌,學(xué)術(shù)界似乎已經(jīng)形成了某種認(rèn)同,說它是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詩歌的某種延伸,并在“個(gè)人化寫作”及“歷史想象力”等維度上持續(xù)掘進(jìn),貢獻(xiàn)出了諸多特色文本,但整體而言,它還未能提供出新的審美取向與思想質(zhì)素。對(duì)此您有什么看法?
羅振亞:謝謝盧楨的邀請(qǐng)。的確如你所說,新世紀(jì)詩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因?yàn)樵姼枞舨缓同F(xiàn)實(shí)、蕓蕓眾生“對(duì)話”,其生命和前途就無從談起。所以大部分詩人都有意識(shí)地走“及物”路線,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開,詩中常充滿濃郁的人間煙火之氣,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象、事態(tài)和情境,鮮活、清晰地閃現(xiàn),仿佛演繹的就是人們身邊已經(jīng)發(fā)生的或隨時(shí)都可能發(fā)生的一切。瑣屑的生活細(xì)節(jié)被人性光輝照亮后,玉成了一種精警的思想發(fā)現(xiàn)。所以我認(rèn)為詩歌“及物”的深化、細(xì)化,進(jìn)一步打開了存在的遮蔽,驅(qū)散了烏托邦抒情那種凌空蹈虛的假想和過度泛濫的浪漫因子,使得當(dāng)下的詩歌更具有真切感和包容性,也使若干年前重建詩與現(xiàn)實(shí)精神關(guān)系的困惑迎刃而解,詩歌寫作倫理的品位同步獲得提升。
盧 楨:您提到的“及物”,我理解為詩人與世界的對(duì)話意識(shí),以及文本內(nèi)在的對(duì)話意識(shí),這兩方面都步入了一個(gè)逐漸細(xì)化的流程,新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也得到了強(qiáng)化。包括您在內(nèi),很多批評(píng)家都指出二十一世紀(jì)新詩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從黯淡到“紅火”的變化,尤其是您把這種變化命名為“生態(tài)逆轉(zhuǎn)”。這一“逆轉(zhuǎn)”的出現(xiàn),是不是就源自您所說的“及物”之深化呢?
羅振亞:首先來說,咱們現(xiàn)在談到的“及物”,應(yīng)具有對(duì)生活物象的穿透力和深刻度,這樣的“及物”才是有效的。如果是凌空蹈虛,沒有觸及生活與生命的內(nèi)核,而滯留于外物的表象,那么誤讀現(xiàn)實(shí)本質(zhì)的代價(jià)和后果,就是文本會(huì)在不自覺間向隱秘情緒和瑣屑現(xiàn)象的鋪展滑動(dòng),多元化的寫作景觀被悄然置換成小情小調(diào)的抒放,使“及物”變成了書齋中的表演,與生命感動(dòng)和思想提升無緣。并且,我所提到的詩壇“生態(tài)逆轉(zhuǎn)”,其動(dòng)因也不能完全歸結(jié)為“及物”,因?yàn)椤凹拔铩眱H是一種題材立場(chǎng),文本的成功,最后還是要依賴詩藝自主性的建構(gòu)。你可以感受到,二十一世紀(jì)詩人仿佛遵守了某種約定,他們的技藝思想更加自覺,注重各個(gè)藝術(shù)環(huán)節(jié)的打造,其生活經(jīng)驗(yàn)向詩性經(jīng)驗(yàn)轉(zhuǎn)化的表達(dá)方式愈發(fā)多元,處理生活的詩歌運(yùn)思能力普遍提高。可以說,二十一世紀(jì)詩歌的新變?cè)从谠娙藗兊摹凹拔铩边x擇、本體自覺與個(gè)人化寫作落地等方面的重構(gòu),更和詩人們的寫作“換筆”休戚相關(guān)。
盧 楨:您所說的“換筆”具體是指什么呢?
羅振亞:“換筆”可以理解為一個(gè)比喻,既是詩人藝術(shù)思路的轉(zhuǎn)換,也可以直接理解為詩人的寫作由傳統(tǒng)的筆耕手寫向鍵盤打字的過渡,從書齋式寫作向網(wǎng)絡(luò)媒體時(shí)代的過渡。網(wǎng)絡(luò)的出現(xiàn),引發(fā)我們寫作方式、思維方式和作品傳播方式、讀者閱讀方式的改變,進(jìn)而以本質(zhì)性的變革影響到整個(gè)詩壇的生態(tài)。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一旦擁有自由空間,就會(huì)努力沖破規(guī)矩與禁忌的藩籬,在探索中俘獲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這也是新媒體為漢詩寫作帶來的最重要的品質(zhì)。網(wǎng)絡(luò)寫作者大多身處民間,他們對(duì)現(xiàn)存秩序的沖擊,和網(wǎng)絡(luò)攜帶的狂歡自由、多元包容的品質(zhì)遇合,決定了他們常常祛除或淡化功利目的,把重心放在藝術(shù)可能性的尋找打造上,走實(shí)驗(yàn)和前衛(wèi)的藝術(shù)路線。事實(shí)上,二十一世紀(jì)活躍的伊沙、沈浩波、朵漁、軒轅軾軻、安琪、江非、茱萸等詩人,大多活躍于網(wǎng)絡(luò)并逐漸成為詩壇主力,構(gòu)成了挑戰(zhàn)主流詩歌話語的基本陣容,并構(gòu)成了催生某種藝術(shù)可能性的潛質(zhì)。
盧 楨:我注意到您近期經(jīng)常提到新媒體語境,以網(wǎng)絡(luò)載體和數(shù)字文化為核心的賽博美學(xué),強(qiáng)勢(shì)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使得無論是詩人還是研究者,都感受到了數(shù)字技術(shù)與媒介融合施與詩歌的機(jī)遇。這樣一來,詩歌與小說、戲劇、游戲、影視等多重媒介載體頻繁互動(dòng),使得“文體跨界”似乎成了當(dāng)下詩歌寫作的一條求奇出新之路。
羅振亞:對(duì)于新詩的文體跨界問題,還是要辯證審視。我認(rèn)為它的正面價(jià)值是毋庸置疑的,它推倒了阻隔詩與其他文體之“墻”,至少為詩歌的持續(xù)發(fā)展打開了一扇可能的窗口。要知道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發(fā)現(xiàn)某種可能性,比讓某種已有可能性成熟更為可貴,詩歌的文體跨界以自身和其他文體界限的淡化、模糊,換取了各文體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合效果,它在促成文學(xué)要求和表現(xiàn)方法的內(nèi)在協(xié)調(diào)、加強(qiáng)其他文體靈動(dòng)性的同時(shí),也提高了新詩適應(yīng)、包容、表現(xiàn)生活的寬度、幅度和能力,使題材疆域的拓展獲得了豐富多維的技術(shù)保證。但也必須承認(rèn),“文體跨界”的提法是理論界迫不得已的尷尬表現(xiàn)。這些年,無論是散文的詩化、小說化傾向,還是小說的詩化、散文化傾向,抑或是詩歌的小說化、戲劇化傾向,批評(píng)圈概用“文體互滲”或“文體跨界”的術(shù)語一冠了之,實(shí)際上是無法以更貼切、內(nèi)在、精細(xì)的方式言說的托詞,一遇到棘手問題即掏出“文體跨界”的“萬金油”,做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含混解釋。我認(rèn)為文體跨界的前提是要以新詩文體為主,合理容納其他媒介載體或文體的長(zhǎng)處。如果完全不顧新詩的文體特點(diǎn),再建爐灶,為了跨界而跨界,不僅不能為新詩開啟未來,而且只能是無功而返。
盧 楨:我們談到了詩人的“換筆”,談到了“文體跨界”,這些都與新媒介的載體功能有關(guān)。此外,我覺得詩壇還要留心“新媒介的話語權(quán)力”問題。媒介經(jīng)濟(jì)對(duì)詩歌命名、詩歌事件的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眾的注意力,一個(gè)個(gè)“標(biāo)題黨”牽涉出的轟動(dòng)效應(yīng),會(huì)使人們只關(guān)注事件而忽視文本。雖然您剛才列舉了不少新媒介時(shí)代的代表性詩人,但我感覺,新媒介文化并沒有為詩歌帶來明顯的整體性藝術(shù)提升。
羅振亞:你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所謂新媒體時(shí)代的詩歌寫作,正如硬幣的兩面,它在改變傳統(tǒng)的書寫方式、為新詩發(fā)展帶來機(jī)遇的同時(shí),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就像你所說的,“事件”大于“文本”。我記得于堅(jiān)在《“后現(xiàn)代”可以休矣:談最近十年網(wǎng)絡(luò)對(duì)漢語詩歌的影響》一文中說過,網(wǎng)絡(luò)“最高尚純潔”“最深刻有效”,也“最惡毒下流”“最淺薄無聊”,既藏龍臥虎,又藏污納垢。他一連用了多個(gè)“最”,雖有斷語之嫌,但也揭示出一些問題。新媒體時(shí)代的詩歌寫作,游戲自動(dòng)化傾向非常嚴(yán)重,常“拔出蘿卜帶出泥”,和一些優(yōu)秀文本面世相伴生,各網(wǎng)站、平臺(tái)也充斥著大量粗制濫造的贗品、“垃圾”。寫作難度的降低、追新逐奇愿望的慫恿和因近于虛設(shè)的把關(guān)機(jī)制,助長(zhǎng)了不少寫作者的盲目自信,加上許多網(wǎng)站、平臺(tái)或自媒體生命短暫,頻繁斷續(xù),使得他們根本不考慮藝術(shù)的相對(duì)穩(wěn)定性,無暇或不屑顧忌文本的審美維度,以娛樂功能的無限度張揚(yáng),碾壓、弱化教化與審美功能,鐘情于口語的隨意輕松,幾近被口水淹沒,再加之作者頻繁變換身份,來去匆匆,作品空有速度而無純度,有數(shù)量而無質(zhì)量,淘汰迅疾,這些都不利于相對(duì)穩(wěn)定的大詩人和經(jīng)典文本的產(chǎn)生。因此我理解作家在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換筆”,這是二十一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和文化界不可遏制的趨勢(shì),新媒體寫作的確立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它帶來了詩壇的活力,但并未造成詩壇生態(tài)的完全理想化。經(jīng)典詩人與文本的缺失、匱乏,導(dǎo)致詩壇依舊是繁而不榮。一個(gè)時(shí)代的詩歌是否繁榮的標(biāo)志,是看其有沒有相對(duì)穩(wěn)定的偶像時(shí)期和天才代表,如果有,那個(gè)時(shí)代的詩歌就是繁榮的,如果沒有,即便詩壇再怎樣群星閃爍,恐怕也會(huì)顯得蒼白無力。
盧 楨:看來詩壇缺乏經(jīng)典詩人與文本的態(tài)勢(shì),也就是您點(diǎn)出的“只見星星,不見月亮”,還要維持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了。不過,二十一世紀(jì)詩歌已經(jīng)走過了二十三年,雖然“十年一代”的時(shí)間劃分早已無法準(zhǔn)確界定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階段,但以十年為一個(gè)周期,對(duì)二十一世紀(jì)詩歌的兩個(gè)十年進(jìn)行比較,或可把握運(yùn)轉(zhuǎn)其中的脈動(dòng)規(guī)律。比如,近期新詩寫作似乎掀起了一股向傳統(tǒng)文化致敬的熱潮,重啟新詩與中華古典詩學(xué)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這會(huì)不會(huì)是新詩發(fā)展的一條新路?
羅振亞:新詩與古典詩學(xué)的聯(lián)系實(shí)際上從未中斷過,說新詩在百年成長(zhǎng)過程中發(fā)展越近成熟,距離舊體詩詞、傳統(tǒng)文化自然就越遠(yuǎn),絕對(duì)是一種錯(cuò)覺。比如我們剛才一直提到的“及物”,在中國(guó)古代詩歌史中,體現(xiàn)“及物”志趣的詩人比比皆是,近些年倍受大眾喜愛的杜甫即是典型代表。與同站在“云端”寫詩的李白不同,杜甫的詩總和人生關(guān)涉,具有一種現(xiàn)時(shí)現(xiàn)事元素突出的“當(dāng)代性”特質(zhì)。也就是說,他是置身于人群之中、之內(nèi)寫詩,經(jīng)常將親歷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帶入詩性空間,這可以理解為傳統(tǒng)詩歌關(guān)注現(xiàn)時(shí)現(xiàn)事的“及物”品格,也凝結(jié)了傳統(tǒng)文化中知識(shí)分子“悲天憫人”的精神特質(zhì),這對(duì)二十一世紀(jì)詩壇無疑是一種深度的喚醒。傳統(tǒng)詩歌的“當(dāng)代性”品格不斷敦促著今天的詩人,促使他們?nèi)フJ(rèn)真調(diào)整詩歌和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距離。也正是在與古典詩歌的凝視中,二十一世紀(jì)詩歌將日常情趣與生活當(dāng)作精神資源的追求,無疑進(jìn)一步深入地敞開了存在的遮蔽,加大了介入現(xiàn)實(shí)真相和時(shí)代良知的力度和幅面,恢復(fù)了漢語語詞和生活、事物之間原在的親和性,這或許也是近幾年來詩歌再度回溫的重要的邏輯支點(diǎn)所在。
盧 楨:今天,我們經(jīng)常會(huì)提到推動(dò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而古典文學(xué)傳統(tǒng)在當(dāng)前新詩中的延續(xù)與新變,確實(shí)激活了很多詩人的創(chuàng)造力。像您所總結(jié)的,詩人承襲了古典詩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觀照,在新詩領(lǐng)域掀起了“杜甫熱”。同時(shí),我們也看到比興手法、古風(fēng)情境、古典意象不斷滲入新詩的文本肌理,使新詩與古詩之間的通道愈發(fā)清晰了。
羅振亞:是的,很多學(xué)者包括我的一些學(xué)生也都注意到了這個(gè)問題,文化傳統(tǒng)與新詩現(xiàn)實(shí),這之間可做的點(diǎn)實(shí)在太多,可謂當(dāng)前新詩研究的一個(gè)“富礦”。我想再沿著你的話補(bǔ)充幾句,中華傳統(tǒng)文化對(duì)新世紀(jì)詩歌構(gòu)成的是精神思想和藝術(shù)技巧的綜合性輻射,像古典詩歌凝練含蓄風(fēng)格統(tǒng)攝下的多元并舉,像儒、釋、道一統(tǒng)傳統(tǒng)觀念的共時(shí)性塑造,都對(duì)當(dāng)下詩歌具有正面價(jià)值的引發(fā)和滲透。我們真應(yīng)該靜下心來,細(xì)致考辨其間的運(yùn)作規(guī)律。
盧 楨:與您談了很多新詩現(xiàn)狀與未來的問題,我想換個(gè)更為輕松的話題。上您的課時(shí),您經(jīng)常鼓勵(lì)我們不要只做詩歌批評(píng),也可以嘗試著去創(chuàng)作。您說過,寫過詩的人再去評(píng)論詩歌,無論是理論視角還是語言感覺,肯定都會(huì)與那些沒有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的人不一樣。就我的了解,您二十歲時(shí)便開始寫詩,從您近幾年寫作的《和老爸聊天》《妻子的頭發(fā)》《在海景房窗邊想起村前那條黃土路》《孩子 我們已沒有資格談?wù)摴枢l(xiāng)》等文本中,我們讀出了一個(gè)眷戀故土、珍視親情的詩人羅振亞形象。您的詩歌往往是“退回自己”或者說是“返歸內(nèi)心”的,內(nèi)在的精神性異常突出。可否請(qǐng)您談?wù)勛约旱脑姼枘兀u(píng)家解析自己的詩歌,想來蠻有意思。
羅振亞:“退回自己”出自我寫的《牡丹吐蕊時(shí)不去園內(nèi)看花》一詩,退回自己的內(nèi)心,強(qiáng)調(diào)的是詩歌寫作要有感而發(fā),不要無病呻吟。我很清楚自己不是那種能夠完全靠想象力馳騁詩壇的寫手,沒有思想或情緒的促動(dòng),我基本上不硬去寫詩,即便寫也寫不出來。或者說,詩是我寄托、抒發(fā)對(duì)親人和這個(gè)世界情感的一種最佳方式,最痛快或最幸福的時(shí)候我都會(huì)想到它。我確信在抒情性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能夠活下去的只能是思想或情感,任何僅僅在技巧層面的經(jīng)營(yíng)都是第二位的、靠不住的,沒有情感驅(qū)動(dòng)而硬去抒情,非但寫不好,還可能構(gòu)成對(duì)詩歌的傷害和褻瀆。或許我的詩歌使命觀念過于傳統(tǒng),我始終認(rèn)為最優(yōu)秀的詩歌都是直指人心,以樸素晴朗的姿態(tài)示人的,古今中外的名篇早已證明這一點(diǎn)。那種在詩歌里面故作高深、裝神弄鬼、佶屈聱牙者,雖然不能說不是一種探索,但恐怕永遠(yuǎn)也不會(huì)打動(dòng)人。當(dāng)然,我也越來越覺得以往那種將詩歌和生活、感情、感覺掛鉤的觀念不無道理,但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因?yàn)樵姼栌袝r(shí)候更接近于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學(xué);所以詩里面如果有一些理趣的融入,可能會(huì)強(qiáng)化詩歌生命的筋骨和重量。
盧 楨:我想,您所說的“理趣”是需要“誠(chéng)”與“真”來維護(hù)的。您最近出版了一部散文集《習(xí)慣溫暖》,這應(yīng)該是您的第一部散文集吧,它對(duì)您意味著什么?
羅振亞:人上了一定年紀(jì),心底難免會(huì)有許多滄桑感受,加上心境愈發(fā)沖淡達(dá)觀,它們和自由的文體散文之間有著天然的相通。所以大約十年前,我在寫作、研究詩歌的同時(shí),就開始了散文創(chuàng)作,這才有了最近這本《習(xí)慣溫暖》。散文與詩都和心靈最接近,我的散文也常有“我”的形象閃現(xiàn),出自生命的發(fā)生機(jī)制,有時(shí)使所抒之情和所敘之事都在不自覺間帶著自己的體溫、呼吸和個(gè)性,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精神成長(zhǎng)的歷史瞬間和片段。只是不同于可以依賴心性進(jìn)行寫作的詩歌,散文在心性之外還需要大量的見識(shí)與文化支撐,難怪很多人認(rèn)為散文屬于老年人,也難怪瓦雷里說詩歌是跳舞,散文是散步。記得閱讀我的碩士導(dǎo)師呂家鄉(xiāng)先生的散文集《溫暖與悲涼》時(shí),我說仿佛是在看“一位智者的思想散步”,至于自己的散文能否進(jìn)入崇尚的那種境界就不好說了。今天我們的交流很愉快,謝謝盧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