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每個時代都有難題,知識分子既清醒也困惑
2020年,批評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堯60歲,他寫出了人生中第一部長篇小說《民謠》。五年之后,他又寫出了第二部長篇《桃花塢》。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難題,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既清醒也困惑。我想,赤子之心對我而言是重要的。”在《桃花塢》面世之際,王堯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獨家專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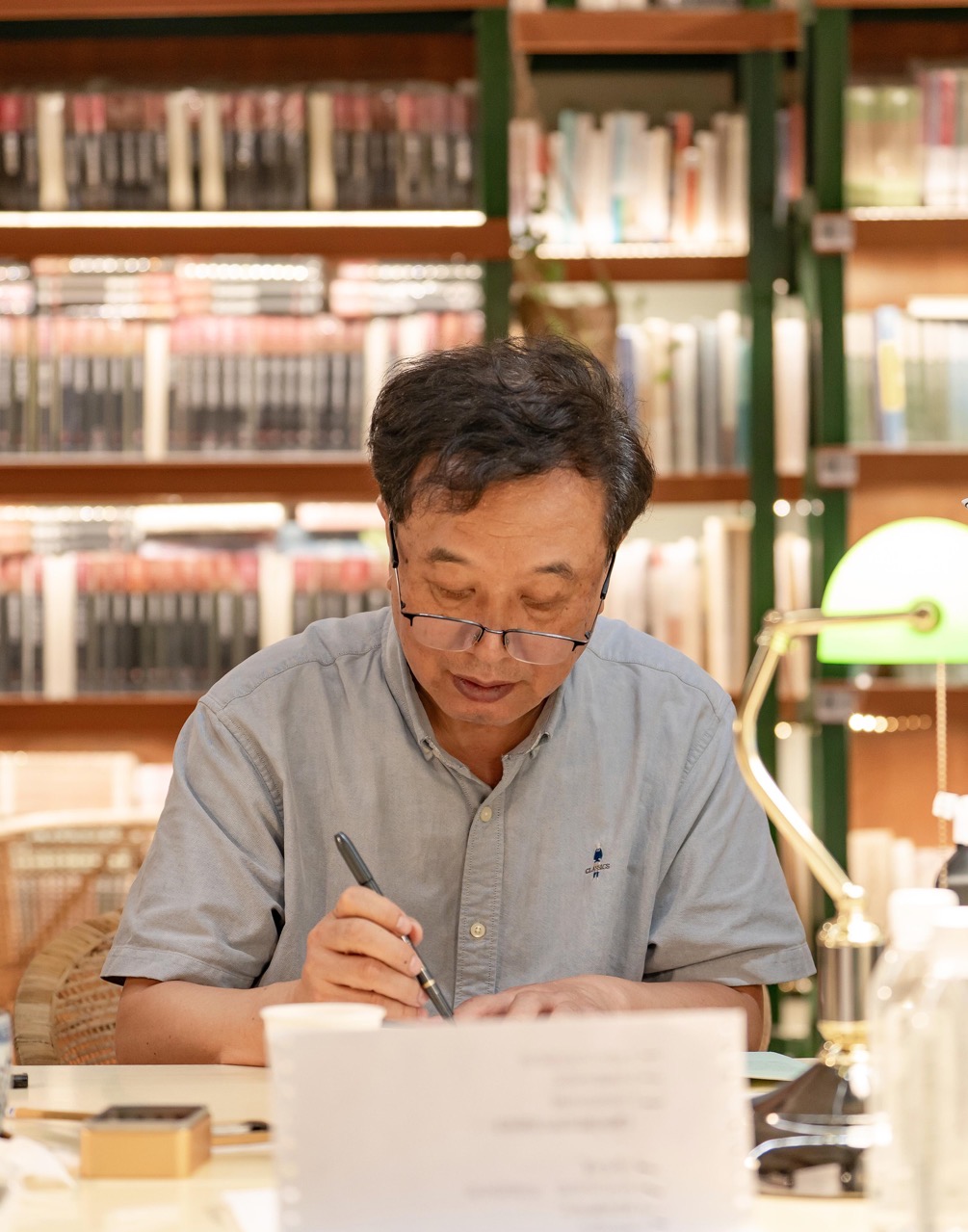
王堯
《桃花塢》首發于《人民文學》2025年第七期,即將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單行本。故事將主要背景設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從“不再是桃花源”的蘇州桃花塢開始,講述了抗日烽火中的日常與情感,以及不同知識分子的艱難抉擇與精神成長。
王堯心里一直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細節:日本兵的飛機從小鎮上空飛過時,他的奶奶帶著還是幼子的父親躲在桌子底下。盡管這個畫面來自奶奶和父親的口述,但王堯一直想象著母子倆在桌子底下的深情,“那個小孩一定哭了,母親擁著他。這就是戰爭創傷記憶。”即使后來去日本訪問,面對友好的日本朋友,他腦中還閃出了這個細節。
六七年前,王堯到南方一所大學演講,重點講西南聯大先生們的崇高、卑微和困境。他當時問了一句:如果回到那個年代,我是聯大的先生或學生,我會如何自處?作為一個從未在發言、演講時落淚的人,那天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先是哽咽,然后熱淚盈眶,失語近一分鐘。再后來,當他寫下《桃花塢》幾個字時,他想要寫一部抗戰小說,從蘇州寫到昆明。
【對話】
敘事和論述一樣迷人
澎湃新聞:60歲之后,為什么開始喜歡寫小說了呢?
王堯:我第一次接受你采訪,好像是《民謠》在《收獲》發表后。我記得你在專訪中說王堯在60歲寫出了《民謠》,讀到“60歲”時,我心里咯噔一下,有點傷感,忽然間已屆花甲之年。
曾經有朋友說我60歲寫小說是老房子著火了,這火種是少年時采集的。和許多人一樣,我有作家的夢想。我在村莊讀過一些小說,老師中也有寫小說的。從我那屆開始初中升高中要考試,作文題目是《讀書務農,無上光榮》。我做了高中畢業后回鄉務農的準備,又偷偷地寫小說和電影劇本,幻想通過創作改變高中畢業后的命運。
大學畢業后,我留校當老師,在學術體制里成了研究文學的教授,而不是創作小說的作家。在寫作學術論著時,我無法抑制自己的創作沖動,經常寫散文隨筆,有時也把論文寫成學術隨筆。2001年在臺灣東吳大學客座,我寫了《民謠》的第一句話。從東吳大學回來后,我和時任《當代作家評論》的主編林建法先生策劃了“小說家講壇”活動,此后與很多作家有了密切的交往,他們的識見、文本和經驗再次激發了我寫作小說的欲望。此后我時不時去寫早就開頭的小說。教授的特長是論述和實證,通過文本闡釋世界;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敘事和虛構,去建構一個文學世界,無論這個世界是大還是小。
澎湃新聞:所以“寫”早已悄然開始。你會覺得60歲寫出第一部完整的小說“晚了”嗎?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州大學講席教授”“江蘇省作協副主席”等等title下,交出新小說時會感到有壓力嗎?
王堯: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在什么歲數寫小說,既然60歲之前沒有寫出小說,那只能說60歲是我寫作小說最合適的時間。很多同輩人在青年時期就寫出了優秀作品,我很欽佩他們。我的前期準備太長了。剛剛說到的這些頭銜,只是學術體制、文學體制內的符號,不必輕忽,也不必在意。我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時,沒有這方面的壓力。寫作《桃花塢》時,我最大的壓力是能不能寫出自己期待中的小說。
澎湃新聞:《民謠》的開頭是:“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桃花塢》的開頭是:“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樂意識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橋上張望的少年。”我發現兩個故事的開頭都有一個“等待的少年”,為什么這么寫呢,和你的個人記憶有關嗎?
王堯:我在意小說的開頭,如果開頭寫不好,我感覺后面無法寫順。《民謠》的開頭與我少年的記憶密切相關,讀高中之前,我經常坐在碼頭上東張西望,或者在那兒發呆。但這個開頭又遠不是我記憶中的記錄,我對小說調性、敘事技巧和結構脈絡的理解是從這一句開始的。也許兩部小說都寫了少年的成長故事,就出現了“等待的少年”。《桃花塢》和《民謠》的寫法不一樣,一刻的等待和一生的張望是一個漫長的時空和內在的張力,《桃花塢》的基調是這樣確定下來的。
澎湃新聞:近來不少大學中文系教授寫起了小說。你認為“研究小說”“評論小說”會給“創作小說”帶來怎樣的影響?我想到西方的大學教授比如索爾·貝婁、戴維·洛奇也是小說大家,在你的觀察里,中西方大學教授寫小說有何異同?
王堯:教授和作家身份的合一,其實是新文學的傳統。現在大學里寫小說的教授大概有兩類,一類是做了教授后寫小說的,一類是寫了小說后被聘請到大學做教授的。
研究小說、評論小說對小說創作的影響,簡單說是產生了學術與創作互補的效應。小說寫什么?通常說的是寫故事。學養、文化和思想對一個小說家而言太重要了,我們常常忽略學養、文化的重要性。在西方的大學,有一批學院派作家,我個人很喜歡索爾·貝婁、戴維·洛奇的小說,索爾·貝婁小說里的人物很多都陷在生活的危機中,這給我啟示。戴維·洛奇的文學批評著作《小說的藝術》也是我喜歡讀的書。我沒有比較過中西方文學教授寫小說的異同,但我感覺我們的文學制度和教育體制將教授和小說家分得太清晰了。
澎湃新聞:有學者注意到,你的學術研究喜歡講文學史,包括各種八卦、掌故。而你的小說文本也充滿細節。其中有你一以貫之的某種寫作觀嗎?
王堯:哈哈,其實我的文章或演講幾乎不講八卦,有時會講掌故。這與我的文學史寫作觀念有關,我希望文學史有故事,有細節,是活生生的文學史。這就是我剛才說到的,既要論述,又要敘事。我現在的學術工作,是在寫論述體文學史和敘事體文學史。我覺得敘事和論述一樣迷人,在寫作中我是個對細節癡迷的人。
寫作創造了一種生活
澎湃新聞:比起《民謠》,寫《桃花塢》時的心境和狀態有了哪些變化?
王堯:從《民謠》到《桃花塢》,小說調性的一個大的變化便是少了《民謠》中少年的躍動,《桃花塢》是一個美好而悲傷的故事。我雖然一直保持著不錯的精神狀態,但逝者如斯的滄桑感還是留在了我的文字中。寫《桃花塢》時,我從容和松弛許多。
澎湃新聞:我很喜歡小說里周惠之這個女性人物,她總能把日子過得優雅。很多人的文化在紙上,在高談闊論中,但她的文化在生活里,她讓衣食住行和寫文章、畫畫一樣都是藝術。塑造這樣一個人物,背后是否也有你對生活本身的理解?
王堯:不少讀過的朋友說自己最喜歡周惠之,說她是桃花塢大街地母式的人物。我也很喜歡周惠之,她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包括說話的腔調。
我設想《桃花塢》的調性是典雅、繾綣、悲傷、詩性、內斂,這些調性在周惠之身上成了品性。生活是美好而悲傷的,人為美好而活,但總會與悲傷相遇。周惠之既受過新式教育,又有傳統美德,她知性、感性,寬闊、敏感,她溫暖而悲憫地看待人與世界。我順著人物的命運寫她失去記憶,寫她失蹤。
我在生活中是個溫和的人,但小說里的這一筆太殘酷了。我不忍她離去,失蹤之后的她仍然是小說里的靈魂。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回到桃花塢大街,我也在尋找她。方后樂在去昆明途中曾經在車站廣場看到有個女人像他媽媽,他奔跑過去。我也是那個奔跑尋找周惠之的人。
澎湃新聞:這五年,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王堯:讀書、教書、寫書,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我承擔了不少社會角色,專業之外旁騖很多,這常常讓我煩心和疲倦。但在與各式各樣的人物交往中,我對社會和人的理解也多了不同的角度,在小說中我喜歡結構相對復雜的人物關系與此有關。
緩解的方式就是抽時間散步,坐下來看書寫作之前,先泡杯茶抽支煙,享受獨處的樂趣。我也喜歡在辦公室和學生、同事喝茶聊天,一起吃快餐,談學術創作,說東西南北。確實太忙碌了,出去參加學術會議,我基本上在會議結束后返回。出國訪問,仍然是我打開窗戶看世界的方式之一。
2021年出版《民謠》單行本時,我母親還健在。她戴上老花眼鏡說,這是你寫的《民謠》。她身體有恙,但能正常生活。沒有想到這一年的10月14日夜間,母親突發心梗去世。這對我打擊很大,直到現在我還沒有適應母親的去世。如果對比《民謠》中“我”的母親和《桃花塢》中方后樂的母親周惠之,應該能發現我母親的去世對我寫作的影響。我和我母親的關系,就像方后樂和周惠之的關系。
澎湃新聞:所以,你也是“那個奔跑尋找周惠之的人”。讀《桃花塢》時,我就感覺方后樂對母親周惠之的思念非常動人。你認為生活會如何影響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
王堯:一般意義上說,沒有生活,就沒有小說創作,盡管小說也建構了另一種生活。這個時代的變化也具體反映在生活中,格式化和分層化的特點很明顯。有許多生活我已經不熟悉了,甚至隔膜了。所以,創作是從自己熟悉的、有感的生活出發的。我喜歡世俗生活,有空也去菜場買菜,偶爾也做飯菜,《桃花塢》的煙火氣與這有關。作為一個讀書人,直接影響創作的是“思想生活”,它決定了小說的面向和內涵。
澎湃新聞:在你的理想中,寫作和生活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王堯:首先在生活中想象,然后在想象中生活。這個順序當然會顛倒,也可能是交織并置。我畢竟這個年紀了,自然明白不能以寫作的方式去改變生活方式,寫作中的詩性和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交織一起。但不管怎樣,寫作創造了一種生活。
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
澎湃新聞:有關蘇州桃花塢,小說寫這里曾如《燼余錄》所言遍地是桃花,后來桃花沒有了,但“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對于中國知識分子,想象有時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出路,你怎么理解這種“想象的力量”?
王堯:“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是祖父回答父親桃花塢為什么沒有桃花的話,方后樂心存這句話在桃花塢長大,又帶著這句話離開桃花塢。在方后樂看來,祖父的這句話是方法論,對他的成長起了至關緊要的作用。
我想說的是,“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首先表達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信念,這個信念對多災多難的民族和個人而言太重要了。它當然也是對精神出路的想象,這種想象的力量伴隨著對理想的追尋,成為一種精神動力。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方后樂以及他周圍的人物。
澎湃新聞:《桃花塢》寫到了不同知識分子在抗日烽火中的選擇,有的“關心”,有的“介入”,也寫到了許多歷史中真實存在的知識分子,比如章太炎、魯迅、朱自清、聞一多等等。我因此聯想到你的散文作品如《滄海文心:戰時重慶的文人》《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紙上的知識分子》《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為什么一直對知識分子的處境非常關注?
王堯:桃花塢是寫歷史的小說,不是“歷史小說”。小說由1937年蘇州淪陷后的逃難開始,回溯到方后樂父親方梅初的少年生活,正是這條線索,派生出魯迅、幾位共產黨早期政治人物、章太炎、朱自清、聞一多等歷史人物,從而與方后樂的成長關聯起來。他們是歷史中的靈魂人物,因為小說人物的關系,他們成了小說中的人物。這些歷史人物的“私密場景”,是依據當時的“場景”想象和虛構出來的,是大歷史中的小細節。我想寫出歷史的縱深感。
這些年來我的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總與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史相關。現在寫知識分子的小說不多,知識分子問題比較復雜,如果不考察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或者精神譜系,很難理解中國現代史,也很難理解從現代延續到當代的思想文化問題。我這一代接受教育,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從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很活躍,其中有回到“五四”的思潮,現代史上的知識分子身影一直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生活和學術生活中。
真的,我無法繞開知識分子問題去研究和寫作。
澎湃新聞:文章寫歷史,但有心的讀者能讀到它對當下的關切。比起過去,你認為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堯:我在前面說,如果回到那個年代,我是聯大的先生或學生,我會如何自處?現在再補充一句話:如果西南聯大的先生或學生生活在今天,他們會如何自處和選擇?我對歷史的追問是和對現實的關切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先賢們的奮斗,我們今天才能夠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才能向前發展。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難題,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既清醒也困惑。中國變化了,世界變化了,現在是一個多種問題和矛盾并置、交織、錯落的狀況。我想,赤子之心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一個流行了許久的話題——“文科無用”?
王堯:我覺得要超越有用和無用看文科。現在什么“科”都有危機,不只是文科。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文科,社會會怎樣,世界會怎樣,人類會怎樣。我是相信人文學科的力量的,但在看到人文學科外部處境的同時,需要檢討人文學科的內部危機。
澎湃新聞:身處文學現場幾十年,你對它有著哪些觀察和反思?
王堯:這是所有問題中我最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在前年寫過一篇文章,《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與文學性危機》,談文學的困境與問題。在文學的大歷史中,幾十年即使重要,但也只是歷史的瞬間。如果有所反思的話,我想缺少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作家特別突出的問題,我們缺少對世界和歷史的大觀照,寫作的功利主義彌漫在各個環節,學術研究也是如此。
《桃花塢》中的方后樂將魯迅當作自己精神導師,小說末尾在回答黃青梅畫了什么時,他說:一棵是桃樹,另一棵也是桃樹。他是在向魯迅先生致敬。我想,文學場中的人都應該向魯迅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