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作家網(wǎng)專(zhuān)欄《有態(tài)度》第七期 李琬 | 異質(zhì)性、技藝與共鳴機(jī)制:皮村詩(shī)人的勞動(dòng)書(shū)寫(xiě)
主持人語(yǔ):
叩問(wèn)群體寫(xiě)作的意義存續(xù)之門(mén)
故土,他鄉(xiāng);鄉(xiāng)村,城市——形形色色的現(xiàn)實(shí)抵達(dá)之處,一系列包蘊(yùn)文學(xué)、人類(lèi)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多元所指的新名詞應(yīng)運(yùn)而生,輾轉(zhuǎn)生長(zhǎng),直至有一天,凝結(jié)出面目清晰的群落姿態(tài)。這種從新興漸趨成熟的歸屬和嬗變,形表于西海固作家、皮村作家、北漂詩(shī)人等作家群的涌現(xiàn),經(jīng)由其實(shí)踐,為重新審視寫(xiě)作之于歷史、之于現(xiàn)實(shí),之于個(gè)體、之于群體,乃至之于生命本質(zhì)的聯(lián)系,提供了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體認(rèn)視角。
文學(xué)巨匠卡夫卡反思文學(xué)藝術(shù)與社會(huì)、與人性的關(guān)系時(shí),曾將文學(xué)比喻為“一本書(shū)”,他說(shuō),“一本書(shū)就像一把利斧,劈開(kāi)我們冰封的內(nèi)心。”——反觀一幕幕生生不息的文學(xué)現(xiàn)場(chǎng),何嘗不在接連叩問(wèn)著意義存續(xù)之門(mén)?當(dāng)文學(xué)成為載體,使某一群人的書(shū)寫(xiě)凸顯無(wú)可替代的特質(zhì);當(dāng)層出不窮的個(gè)體乃至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級(jí)群落爆發(fā)出前所未有的自覺(jué),對(duì)意義的追問(wèn)便顯得尤為迫切。本期“有態(tài)度”專(zhuān)欄特約深耕作家群內(nèi)部、堅(jiān)持長(zhǎng)期觀察的作家、評(píng)論家,以若干作家群及群體寫(xiě)作現(xiàn)象為原點(diǎn),闡發(fā)深度思考。
——欄目主持:杜佳
異質(zhì)性、技藝與共鳴機(jī)制:皮村詩(shī)人的勞動(dòng)書(shū)寫(xiě)
李琬
近年來(lái),許立志、陳年喜、王計(jì)兵等 “新工人”作者的詩(shī)已經(jīng)贏得了來(lái)自社會(huì)各圈層的廣大讀者,改寫(xiě)著時(shí)時(shí)面臨固化、陳腐風(fēng)險(xiǎn)的當(dāng)代詩(shī)歌創(chuàng)作面貌。最近出版的皮村文學(xué)小組詩(shī)集《大口呼吸春天》,延續(xù)并更新著這種勞動(dòng)詩(shī)學(xué)視野。詩(shī)集中收入的陳年喜、范雨素、小海、繩子等十五位詩(shī)人作品,又一次向我們展示了最貼近當(dāng)下時(shí)代脈搏、最能牽動(dòng)社會(huì)感覺(jué)神經(jīng)末梢的勞動(dòng)者書(shū)寫(xiě)。
不同于一部分讀者對(duì)勞動(dòng)者或新工人詩(shī)歌的抽象、凝固的想象,這些工人作者的作品雖然有很大程度上的共性,但也同樣呈現(xiàn)了豐富駁雜的異質(zhì)性。首先,這些詩(shī)人的身份就是多種多樣的。總體上看,這些新工人作者都是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加入第二、第三產(chǎn)業(yè)的勞動(dòng)者,不過(guò)有的是在傳統(tǒng)工業(yè)、建筑業(yè)中工作的工人,比如礦工陳年喜、泥瓦匠徐良園、酒廠工人繩子,而另一些則是育兒嫂李文麗這樣從事服務(wù)業(yè)的勞動(dòng)者以及在新興的平臺(tái)經(jīng)濟(jì)中謀生的人,如外賣(mài)員、網(wǎng)約車(chē)司機(jī),還有一些則是小海這樣身份更加流動(dòng)、多樣的打工者,他有著多種職業(yè)經(jīng)歷(從工廠到二手服裝店員),呈現(xiàn)出物理空間上更為自由的、波希米亞式生活狀態(tà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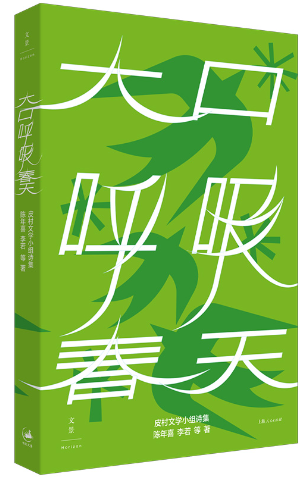
詩(shī)集《大口呼吸春天》書(shū)影
總體說(shuō)來(lái),第二產(chǎn)業(yè)的工人筆下有更多關(guān)于技術(shù)工作細(xì)節(jié)的描繪,并常常混合著勞動(dòng)本身帶來(lái)的艱辛、痛苦(連同痛苦后獲得緩釋與凈化)的身體感受。如繩子寫(xiě)到的“何淑剛拎著一根幾十斤重的閥桿/從第一階到一百零一/藍(lán)色的閃電并不會(huì)讓他停留或猶疑”(《機(jī)油味的藍(lán)蜻蜓》),或者王景云的“傳送帶,這個(gè)奔跑的風(fēng)/無(wú)論時(shí)間在哪里升起/一旦電開(kāi)關(guān)閉合/工人這棵曠野之息的草/就立刻重復(fù)機(jī)械性的動(dòng)作/停不下來(lái)/任由風(fēng)操控”(《車(chē)間,有奔跑的風(fēng)》);而第三產(chǎn)業(yè)的工作者則寫(xiě)到了更多樣的社會(huì)交往和日常生活、娛樂(lè)。
另外,異質(zhì)性還表現(xiàn)在他們的書(shū)寫(xiě)主題和風(fēng)格都各具特色。誠(chéng)然,如張慧瑜為《大口呼吸春天》作的序里寫(xiě)到的那樣,“新工人詩(shī)歌最重要的特色是把生產(chǎn)、勞動(dòng)、創(chuàng)造作為書(shū)寫(xiě)對(duì)象,讓隱匿的勞動(dòng)過(guò)程變得可見(jiàn)、可感,因?yàn)槿諒?fù)一日的勞動(dòng)和工作是他們最直接的生命體驗(yàn)”,不過(guò),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作者的寫(xiě)作范圍不止于此,除了勞動(dòng)、工作,他們的寫(xiě)作內(nèi)容往往是帶著勞動(dòng)者的目光去看待生活世界中的一切。
這些勞動(dòng)者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工作性質(zhì),都仿佛一層濾鏡,讓他們更多、更深地和彌散在人類(lèi)生活中的病痛苦難待在一起。比如,劉玲娥的《在內(nèi)分泌科》就描繪了醫(yī)院里病人發(fā)出的痛苦呼告。李明亮的詩(shī)中走動(dòng)著他的許多親人的身影,流動(dòng)著素樸而深長(zhǎng)的親情和同情。在《摸黑掃地》《自制綠豆芽的過(guò)程》等詩(shī)中,李明亮也寫(xiě)到了在相對(duì)困窘的物質(zhì)條件和居住狀態(tài)下,對(duì)待自己狹小家屋的認(rèn)真、耐心,對(duì)即便十分有限的情趣、審美性的追求,展現(xiàn)出充滿自尊的日常生活態(tài)度。而在李文麗的詩(shī)中,我們讀到了女性對(duì)于情感關(guān)系的不滿和反思,如《如果還有來(lái)生》這首詩(shī)里,“我”感嘆自己需要的是一個(gè)能夠體貼、給予安慰、遇事和氣商量,而非不善于表達(dá)愛(ài)意、粗暴而容易動(dòng)怒的伴侶。盡管其語(yǔ)言直白、粗樸、散文化,但讀來(lái)仍具有強(qiáng)烈的身體感和現(xiàn)實(shí)性。因此我們看到,雖然都是勞動(dòng)者的詩(shī),但它們的表達(dá)內(nèi)容早已超過(guò)了單一、狹窄的范疇。
與書(shū)寫(xiě)主題的多樣性相關(guān)的是,這些作者的寫(xiě)作技藝和詩(shī)意強(qiáng)度,從平均程度來(lái)看也取得了較高水準(zhǔn),驅(qū)散了人們對(duì)于“新工人詩(shī)歌是否具有足夠的審美性、藝術(shù)性”這類(lèi)問(wèn)題的擔(dān)憂。可以說(shuō),工人作者和那些受過(guò)更多“學(xué)院”教育或身為知識(shí)分子的作者相比,在詩(shī)歌技藝的“起跑線”上并無(wú)本質(zhì)的高低。不僅如此,一部分新工人作者的詩(shī)還因使用大量溢出陳規(guī)和日常生活世界的“非詩(shī)意”語(yǔ)言(如“電阻”、“螺孔”、“罵天罵地罵工頭”、“噪聲的純金打成”的“耳環(huán)”等)而顯現(xiàn)出更強(qiáng)烈的陌生化特質(zhì)——穆旦曾主張,詩(shī)應(yīng)該摒棄“舊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用“非詩(shī)意”詞句寫(xiě)作,從而保留鮮活、粗糲的經(jīng)驗(yàn)質(zhì)感。這些作者的詩(shī),多多少少實(shí)踐了這種非詩(shī)意的寫(xiě)作方法,最大程度地深入、提煉了生活的真實(shí)。
當(dāng)然,各個(gè)作者在詩(shī)藝上的成熟度不盡相同。粗略說(shuō)來(lái),比起《大口呼吸春天》中的其他作者,陳年喜、小海、繩子、王志剛等作者的確展現(xiàn)出更高的技藝水準(zhǔn)和更為明晰的個(gè)人化風(fēng)格。譬如繩子的一些短詩(shī),就在某些地方讓人想到美國(guó)作家卡佛的詩(shī)里那些簡(jiǎn)潔、冷硬有力的表達(dá);他的組詩(shī)《勞動(dòng)是身體里最黑的部分》以一個(gè)個(gè)切片,鮮明、完整地描繪了工廠的場(chǎng)景和經(jīng)驗(yàn),并達(dá)到了讓人驚異乃至震撼的思想深度和強(qiáng)度。而對(duì)于其他一些詩(shī)人而言,如何獲得真正有個(gè)人特征、遠(yuǎn)離陳詞濫調(diào)的詩(shī)歌語(yǔ)言,仍然是一個(gè)持續(xù)存在并不斷生長(zhǎng)的問(wèn)題。
在這些作者對(duì)勞動(dòng)生產(chǎn)情態(tài)和勞動(dòng)者生活狀況的具體描繪中,我們也能發(fā)現(xiàn)一些更為微妙而深刻的社會(huì)變化。勞動(dòng)過(guò)程固然充滿艱辛、讓人疲乏,但讓勞動(dòng)者失望的主要不是身體的疲憊,而是他們似乎很難從工作中感受到尊嚴(yán)和價(jià)值感。他們辨認(rèn)出的自我處境是“鋼筋水泥的欲望大樓里圈養(yǎng)著我們的廉價(jià)青春”“糧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們關(guān)心”(小海《中國(guó)工人》),而這些價(jià)值感的流失,也許不僅是某項(xiàng)具體工作和某種特定職業(yè)所造成,恐怕也與體力勞動(dòng)者的社會(huì)地位、社會(huì)形象相對(duì)而言受到壓抑、貶損的整體狀況有關(guān)。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工人常在詩(shī)里寫(xiě)到動(dòng)物和植物的意象,并借助這些形象傳遞共情和認(rèn)同。對(duì)比“七月派”詩(shī)人牛漢筆下那些或具有受難者意味、或充滿強(qiáng)悍生命力和搏斗精神的動(dòng)植物,新工人作者寫(xiě)到的動(dòng)植物往往是卑微、脆弱的,如老鼠(李明亮《中秋節(jié),在出租屋打死一只老鼠》)、蚯蚓(徐良園《蚯蚓兄弟》)、野草(王景云《流水線上的稗草》)等。這也反映出,無(wú)論他們對(duì)生活有怎樣正面的期待和追求,卻總感到自己是不被重視、在社會(huì)生活中缺乏力量的人。
除了勞動(dòng)過(guò)程對(duì)人的消耗,這些詩(shī)人也比較密集、頻繁地寫(xiě)到當(dāng)下分工狀況下,親人之間越加普遍的、長(zhǎng)時(shí)間的被迫分離——“媽媽/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不在的時(shí)候/讓冰冷的電器/替我照顧你”(李若《替我照顧你》),“丈夫像一塊石頭/被留守,生死不知,病如頑石”(程鵬《運(yùn)往深圳的孤獨(dú)》)。無(wú)法合理地利用、占有自己的時(shí)間,是所有這些勞動(dòng)者的生活中無(wú)法忽視的問(wèn)題。這些詩(shī)句,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為當(dāng)下的工作、生活方式提出一些校正建議。
與此同時(shí),我們也看到,與那些更加“專(zhuān)業(yè)化”、更有余裕、有更為通暢的“正式”發(fā)表渠道的詩(shī)人相比,對(duì)于這些工人作者來(lái)說(shuō),詩(shī)歌寫(xiě)作的意義,也不是(或主要不是)贏得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某個(gè)位置、樹(shù)立某種語(yǔ)言的風(fēng)格和寫(xiě)作上的自我形象;寫(xiě)詩(shī),在他們勞累、充滿重復(fù)動(dòng)作和相對(duì)乏味的生活中,更多地顯現(xiàn)為某種具有升華、救贖意味的工作和行動(dòng)。郭福來(lái)在《我的詩(shī)篇》中寫(xiě),“現(xiàn)在/我的詩(shī)篇寫(xiě)在工廠/一堆堆僵臥的鐵管、方鋼/沉睡在車(chē)間、庫(kù)房/它們了無(wú)生氣,渾渾噩噩/像人一樣困惑迷茫/經(jīng)過(guò)我的焊接和打磨/突然間變得像鮮花般漂亮/不,更像優(yōu)美的/詩(shī)句一樣”。我們也可以這樣來(lái)理解這幾行詩(shī):經(jīng)過(guò)詩(shī)的“焊接和打磨”,原本無(wú)生機(jī)的人工物質(zhì),連同詩(shī)人對(duì)生活的感覺(jué),都煥發(fā)出了新的光彩和意義,躍動(dòng)著創(chuàng)造與尊嚴(yán)的輝耀。
這些詩(shī)歌之所以引起大眾關(guān)注、被越來(lái)越多讀者所閱讀和傳播,一方面是因?yàn)樗鼈兲峁┑男迈r、具體的經(jīng)驗(yàn)以及這些詩(shī)句所散發(fā)的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yàn)樯鐣?huì)和人口結(jié)構(gòu)在幾十年來(lái)的自然變遷。由于分工的精細(xì)化和大多數(shù)工作的高度機(jī)械化、技術(shù)化的發(fā)展,也由于白領(lǐng)階層和工人階層的收入差距相對(duì)縮小,實(shí)際上大部分腦力勞動(dòng)和體力勞動(dòng)的傳統(tǒng)界限正在模糊。倦怠的情緒在不同職業(yè)的工作者中都普遍存在;人與人愈發(fā)疏遠(yuǎn)隔絕的原子化體驗(yàn),正被工人和白領(lǐng)所共享。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工人階級(jí)”的定義,便是除自己的勞動(dòng)力以外一無(wú)所有、只能把這種勞動(dòng)力出賣(mài)給資本以換取自身生存的階級(jí),而城市里越來(lái)越多的各行業(yè)勞動(dòng)者都正在落入這一定義之中。因此,這些新工人詩(shī)歌能夠喚起十分廣大的情感共鳴。它們并不只是被中產(chǎn)階級(jí)讀者帶著審美距離消費(fèi)并為感動(dòng)的文化產(chǎn)品,也實(shí)際上在連接著看似互不相干的人們,在擾動(dòng)、刺痛著我們所有人的心緒,在不斷激發(fā)著各階層讀者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觀察和省思。它們不僅以感性的方式宣泄著、紓解著勞動(dòng)者的倦怠、苦痛和困惑,也啟迪著人們繼續(xù)冷靜地思索和探尋:在這個(gè)時(shí)代,究竟該如何擁有一種更為健康、良好的生活。
作者簡(jiǎn)介:

李琬,1991年生于湖北武漢,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著有詩(shī)集《他們改變我的名字》、散文集《山川面目》《咔嗒》。曾獲拾壹月詩(shī)歌獎(jiǎng)、揚(yáng)子江青年詩(shī)人獎(jiǎng)、南方詩(shī)歌獎(jiǎng)·青年詩(shī)人獎(jiǎng)。評(píng)論發(fā)表于《文藝爭(zhēng)鳴》《上海文化》《澎湃新聞·上海書(shū)評(píng)》等刊物和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