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霞推出兒歌集《北斗在天》:用聲韻和歡樂,抵抗生活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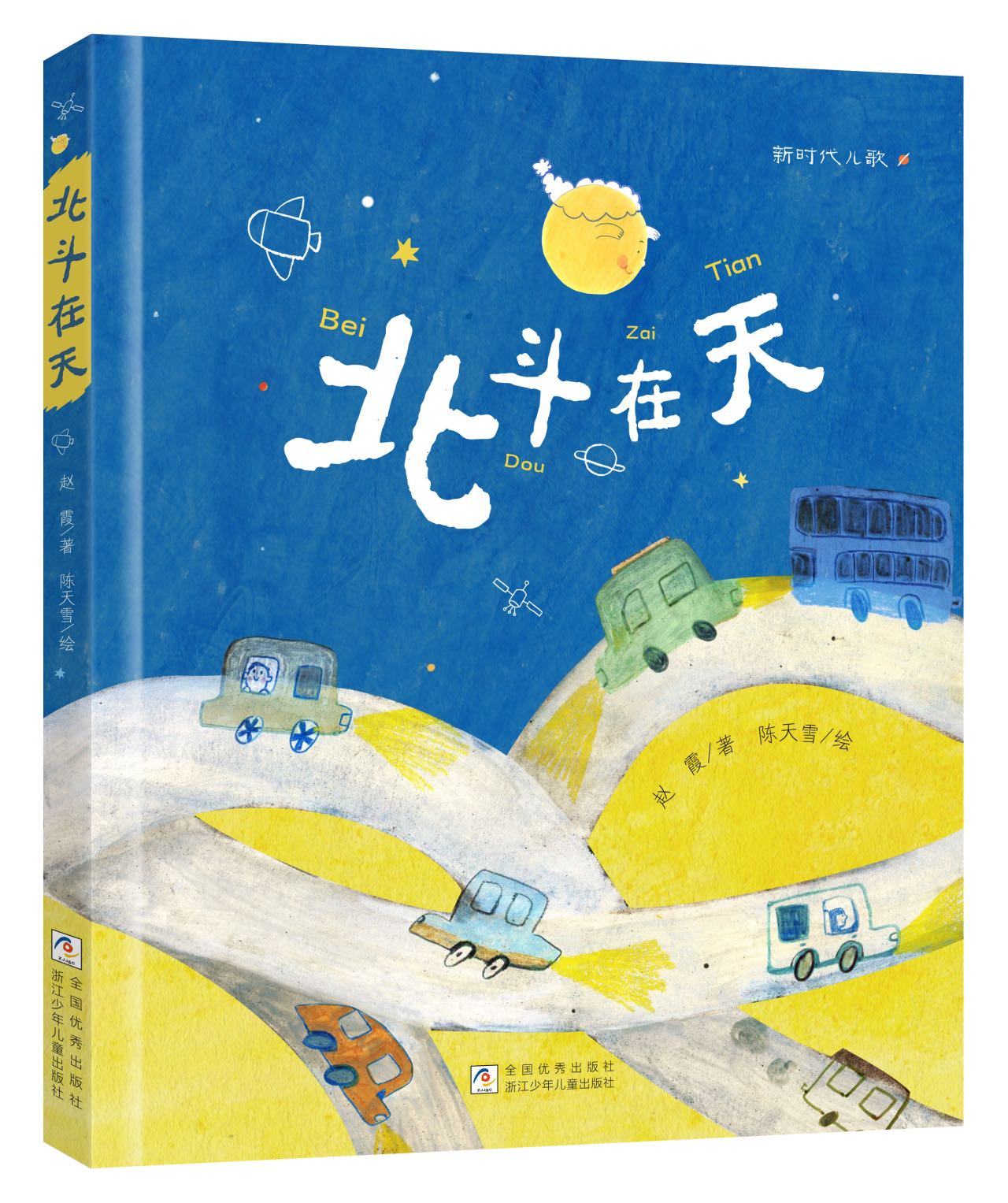
“山青青,樹青青,荷花菱花水中映;紅蜻蜓,藍蜻蜓,外婆頭上停一停……”
當婉轉的兒歌回響在耳邊,那些有關童年、故鄉的鄉愁便涌上心頭,喚醒生命中最美妙的時光。
翻開兒歌集《北斗在天》,就好像走進時光的相薄,過往的記憶與天馬行空的想象交匯成奇妙的歌行,留下一場場未完待續的夢。
寫下這些兒歌的趙霞,是一位兼備詩心、詩情的母親,也是浙江省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主任、浙江外國語學院教育學院教授。
她長期深研兒童文學,切身感受到兒歌在孩子成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因此沉浸于兒歌迷人的韻律和滋味,試圖創作一些糅合傳統與當代美學、富有時代氣息的兒歌作品,“我想通過兒歌傳遞生活的趣味,同時探索兒歌的容納如何繼續向寬,向廣,如果可能的話,也繼續向深,呈現更豐美的‘游戲’,更豐富的‘好玩’。”近日,趙霞以筆談形式接受潮新聞專訪,她說,希望進一步找到兒歌新與舊的結合點,更好地關注、表達當代的觀念和情感,一起讓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在今天煥發新生,迸發出更強的活力。
以下是采訪實錄:
潮新聞:為什么給新作起名為《北斗在天》?您為何想寫這樣一本作品?
趙霞:《北斗在天》是收入書中的其中一首兒歌題目。寫這首兒歌時,我的心里想著兩個“北斗”,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我想它們是一體的,但還不確定怎么在歌謠里把它們自然地合到一起。有一天,重讀《詩經》的間隙,這些歌行忽地來到腦海,一氣而成。我想我是受了《詩經》的啟迪,包括四言的體式——我熱愛這部經典,多年來,翻讀它一直是我享受的一種放松和愉悅。同時,這個作品恰好也傳遞了我關于兒歌的一些新的關切和思考,包括當代兒歌創作中如何實現“古”與“今”、“舊”與“新”、“傳統”與“現代”的融合。這部兒歌集中的不少作品,都是這種嘗試和努力的產物。
潮新聞:您在《創作談》中說,兒歌的創作充滿了難度,比如語言清淺容易被當成順口溜或語言詩化、雅化容易失去獨特的情味。您在創作中是如何克服這一問題的?
趙霞:或許談不上很好的克服,只是努力了。要在創作兒歌中繼承、復現傳統童謠的語言韻律和趣味,確實非常難。其天真、天成、純凈、活潑,以簡為豐,意近而遠,似乎都非一時之人力所能達到。因為兒歌的語音節奏和韻律都非常齊整,一不小心就會滑向順口溜體。我在創作兒歌時不知不覺也寫出過類順口溜的作品,后來領悟過來,都丟掉了。其實傳統兒歌中有時也會出現順口溜,但因為這樣的作品在審美層級和感覺上相對降低,今天就不大受到人們關注。傳統兒歌經歷了一個自然篩選的過程,創作兒歌也一樣。十幾年后,幾十年后,哪些當代兒歌還會留下來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來想。
兒歌的語言其實是很有講究的,這種講究,很大程度上是歷經一代代人口頭打磨的結果。可是創作兒歌一旦太過講究語詞,又容易把它朝一般的詩的方向去靠,甚至變成“次詩”,大大影響兒歌的美感。所以又得往回調。就這樣,以兩頭為邊界,不斷調試,努力調到一個當下比較令自己滿意的狀態。這個的過程很艱難,但一點點的推進和領悟,也帶來很大的滿足和愉快。
潮新聞:您在作品中提到與兒子邊散步邊念兒歌的經歷,想要了解一下,您和孩子日常最喜歡閱讀哪一類童謠作品,為什么?您最想通過兒歌傳遞什么?現在回看,您和孩子相處的經歷如何影響您的寫作?
趙霞:孩子小的時候,我和他一起讀了不少兒歌,什么類型和風格都有。相對來說,他更喜歡比較好玩的兒歌。比如繞口令中的“顧老頭,本姓顧/上街打醋帶買布”,顛倒歌中的“石榴樹,結櫻桃/蘋果樹上結辣椒”,還有莫名其妙的“嘟了嘟了/上樹摘桃”。也說不上講些什么,就是好玩。我想,在這些兒歌里,語言聲音和意義的狂歡,為孩子提供了活潑奔放的趣味,也提供了生機勃勃的宣泄。
如果說我想通過兒歌傳遞什么,首先也是這種好玩的滋味和感覺。《上學謠》《下滑梯》《娃娃哭》《屋檐下》《蘋果樹》《天上開了點心店》《夏天的夜晚》《螞蚱》《小鴨》等篇,并不講什么特別的意思,就是童年好玩的游戲。我的孩子現在上四年級了,他讀《天上開了點心店》,嘴里做出“嗞啦”的響亮口水聲。這是現在他表達認可和喜歡的含蓄方式。我希望在兒歌里和孩子一起,搖晃著,出神著,高高興興地笑著。
但我同時認為,對兒歌這種樣式的當代發展來說,它的容納還要繼續向寬,向廣,如果可能的話,也繼續向深。當然這些都得在充分保留它的“好玩”藝術的基礎上。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應該為我們呈現更豐美的“游戲”,更豐富的“好玩”。《小牛》里有個孩子的聲音,對“往東走/沒人留/往西走/沒人留/往南走/沒人留/往北走/沒有留”的小牛說,“東西南北走一走/走到我家有人留”。我想,它可以只是一個孩子對一頭小牛的喜愛和真心實意的歡迎,也可以是一種情感和情懷,向著所有流浪的生命打開——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有“走到我家有人留”的溫暖和依靠。還有《你的和我的》。我的好朋友錢淑英博士上幼兒園的孩子讀完這首兒歌,媽媽問他,覺得怎么樣?他說:好多玩具啊!其實兒歌里并沒有提到玩具,但孩子總是能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敏銳地感受,準確地表達。就是這種“好多”的感覺。“我”和“你”在一起,世界變得更大,快樂變得更多。我想,當代兒歌可以進一步探索怎樣更好地關注、表達這些很當代的觀念和情感。
潮新聞:《北斗在天》汲取了傳統童謠的藝術養分,并融入了飛船、火箭、高鐵、衛星導航等科技意象,作為兒歌的寫作者,您認為該如何將現代事物與兒歌藝術巧妙結合,從而加強兒歌的當代生命力?從聲音到意象,寫作者如何為兒歌賦予可見性?
趙霞:這本集子第一部分“高高山上有只船”中的六首兒歌,基本都是以現代科技為素材,但采用的形式又特別傳統。我在思考,兒歌的“新”與“舊”,兩者之間的結合點可能在哪里?很愿意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試驗。比如《高鐵高》這首,起初嘗試了很多種別的體式,始終感到不滿意。那段時間,日里夜里都念著它。有一天午休,躺下前還在痛苦地自我否定,醒來的一瞬,忽然想到了傳統童謠的連鎖調形式,一節一節,前后相銜,不就是一列高鐵的形態?趕緊起來寫:“高鐵高/走大橋/大橋闊/走平川……”。一邊寫,一邊感到這個形式用在這里確實比較稱手。除了“連鎖”帶來的形象感比較貼切,連鎖調可以換韻,也正好呼應列車開行中空間的持續轉換。隨著歌行的展開,高鐵的形態感、運動感,以及隨著列車的開行不斷展開的地理、視覺和心理空間,都慢慢出來了。直到最后,“高原高處云連天/高鐵開向云里邊”。這個收尾,我琢磨許久,用的“ian”韻,韻腳二字合在一起,正是“天”“邊”。天高云遠,無窮無盡,正合我想表達的意思。
兒歌如何扎根現代生活的土壤,生出新的枝葉,煥發新的光彩,還有許多事可做。我在這本兒歌集里做了一些探索的嘗試,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兒歌作者一起來參與試驗和創造。
潮新聞:您在《創作談》中提到,值得探索一門屬于兒歌的音韻學。從學者的視角去看“音韻”和從作者的視角去看“音韻”有何不同?深入音韻學研究有何難點?您現在研究進度怎么樣了?
趙霞:確實有這個念頭,但也還只是念頭。一些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傳統歌謠,我曾仔細琢磨它們的聲韻安排,妙處很多。形式上的整齊只是最初淺的表象。除了最可見的節奏停頓和尾字押韻,更為關鍵和困難的是整體的聲韻諧調,字與字、詞與詞、行與行之間,內外聯結,前后回應,上下振蕩,聲音又與物象、意境、情感之間構成巧妙、貼切的呼應。然而,每當我試圖用某種概括來整理一首歌謠的聲韻規律,又常感到無望。兒歌就像小孩子一樣,乍看多么齊整好看,卻也頑皮。經典傳統歌謠的聲韻,往往既整齊,又靈活,你剛覺得好似把到了它的聲音脈膊,它卻倏地變律,跳躍開去。于是你又得重新去定位,當然一會兒工夫,它又跑開了。而且不同的歌謠,聲律的排布頗有些隨興而至,各各不同,其中還要考慮古音與今音的變化。我初步認為,如果要談兒歌的聲律,肯定不是格律,而是古律;不是拘著說,是像說話那樣自在地說,但還要說得好。這個“好”字可難。我老家有個鄰居,前些年過世了,很有講話的本領。任什么話到了他嘴里,明明又白又俗,但不知道為什么,聽著就是順溜,生動,入耳。我想他可能屬于很少的一類天生就有很敏銳的聲韻感覺和天賦的人。
兒歌也需要這種聲韻上的敏銳度。哪樣的聲音可以恰到好處地與特定的物象構成完美的對應,怎么朗朗地整齊,怎么巧妙地變化,不論整齊還是變化,還都要自然、口語、童趣,其中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之多。實際上,從音韻學的角度看,談這些也還是淺,還要深入。
所以要探討兒歌的聲律,我覺得非常難。但是一首兒歌站在那里,笑盈盈的,像個古靈精怪的小孩,真是讓人著迷。我現在能做的,是就單個作品來做盡可能細致的研讀,從量變開始,慢慢累積著,看是否可能走向質變的那一端。
事情總是這樣,說得容易,寫起來,寫斷手。話說回來,真有一首好作品等在前面,“寫斷手”的努力,也值得的。
潮新聞:兒歌的讀者的是兒童,寫兒歌的卻是大人。作者寫作中應該如何呼應兒童情感,同時通過兒歌實現文化傳承與兒童教育的作用?童年是一個人一生中的重要階段,對于作家來說,兒時的記憶如何影響他的寫作?
趙霞:你談到了從過去到今天兒童文學寫作的恒久困境,也是兒童文學寫作最根本的難度所在。兒歌也不例外。成人作者如何能夠真正理解、表達兒童的情感?今天的腦科學研究證明,當我們長大成人,大腦某些結構就發生不可逆的、根本性的變化。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童年回憶本身都可能是不可靠的,經過重新加工的,那么,我們對兒童對象及其世界的理解和表現,哪怕基于自己親身的童年記憶和經驗,有可能是可靠、可信的嗎?有的激進的西方兒童文學研究者甚至以此質疑歷史上全部兒童文學寫作活動的意義。
關于這個問題,我的理解是,某種程度上,一切寫作都不避免地是一種他者行為,“他者”的關系,既是作者與讀者之間,也是作者與其書寫的對象之間,哪怕這個對象是曾經的自己。也許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真正完整和徹底的意義上理解另一個人,包括不同階段的自己。在寫作中,不存在一個被原樣復現出來的對象,惟有作者在寫作這一刻所努力抵達的真誠、真實和深刻,后者才支撐起了寫作行為的根本意義。就此而言,兒童文學寫作的這個困境,跟其他文學在根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在兒童文學寫作中,理解兒童始終與理解自我、理解世界的問題密不可分。簡單地觀察、想象兒童是什么樣、怎么做、怎么想的,并不能保證一個兒童文學作品的成功。把自我和世界融入兒童,或者,把兒童融入自我和世界,從兒童身上照見自我、世界的一切,從自我和世界的深處看見兒童的影子,以這樣的方式理解兒童,表達童年,那種當下時刻足夠坦然、深刻的誠與真,才可能帶我們走向兒童文學真正的藝術腹地。
兒童文學與其他文學一樣,審美的功能在首位,這個功能完成好了,文化和教育的功能,也自會實現。不過,因為在兒童文學的兒童和成人之間,成人顯然站在文化的上手,容易不知不覺地產生驕矜,要自覺地認識和實踐這一點,也就格外地難。
回到兒歌的問題。兒歌的創作,既要時時念著兒童,又不能只有兒童。兒歌怎樣能夠做到說的話不只是給孩子的,對作者自己,對老熟的成人讀者,甚至對文學批評家,也一樣真誠、深入,有生命的質感和重量?一想到這個問題,我常常汗顏。
童年確實很重要,關于它究竟在人的一生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影響,從科學層面看,目前我們的了解其實還是很少。但文學提供了大量生動、深刻的例證,舉不勝舉。我也受小時候的影響和滋養,年齡越長,感受越深。童年和故鄉,是最根本的兩種鄉愁。兒童文學作家往往深陷于童年的鄉愁。
潮新聞:從早期傳唱的童謠到現在的兒歌,這種文學載體有沒有發生變化?兒歌發展的過程中,核心不變的東西是什么?
趙霞:從傳統童謠到創作兒歌,有明顯的承繼,也有鮮明的變化。總的說來,創作兒歌比傳統歌謠更有自覺的童年意識,在生活世界的觀看、呈現和理解方面更具現代性,藝術形態也相對更為多樣。我在創作談中也提到,當代創作兒歌在兒歌意象、意境的煥新方面,或可做出新的探索和貢獻。
但我相信,的確也有“核心不變的東西”。是什么呢?現在讓我說的話,大概是兩個。一是經由兒歌這種樣式得到探索和實踐的漢語的獨特表達力,包括清淺至極中的趣味,日常至極中的詩意等。二是經由兒歌中的童年身影和景象得到展示、呈現的生活和生命之美,那種輕盈、朗亮、渾樸、幽默、溫暖和善意的融合,讓人感到,這個世界和生活本身是一場巨大的饋贈。
潮新聞:當下進入了一個日新月異、快速變遷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作品涌現,擠壓兒歌的生存空間,這是否意味著兒歌正在面臨某種危機?這一文學體裁會消失嗎?您覺得什么樣的兒歌是好的兒歌?在今天,它還有哪些特殊的價值?好的兒歌對兒童的成長、價值觀的形成有何益處?
趙霞:相比童話、兒童小說等體裁,兒歌在體式上算是小類。小類不必求大,但也不會消失。我相信,兒歌是與童年相伴生的文體。
去年夏天,我們參加學校的旅行,途中,大巴車上不同年齡的幾個小孩子漸漸湊到一起,念起校園里風行的自編歌謠:“奧特曼/飛得慢/飛到凌晨三點半……”“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有飛機……”“降龍十八掌/帶你去天堂……”其淘氣怪異,顛撲越禮,大人們聽得尬而不語,他們卻個個笑得不能自止。
我一直認為,這其實是一向以來童年自我娛悅和解壓的方式之一,一種在語言中放肆的松解,在游戲中顛覆的快樂。每個孩子,就跟每個成人一樣,都承擔生活分給他們的重量。用聲音和笑的抵抗,讓這些重量變得可以承受,甚至在某些時刻變得不值一提,并沒有什么問題。我想說的是,它之所以會呈現為兒歌的形態,很可能也證明了在這個古老文體的節奏和體式中,有著某種可與童年構成彼此回應、加強的天然力量。
所以兒歌的創作才顯得如此重要。兒歌藝術應該是多元的,孩子自己的許多歌謠也應該得到應有的理解和許可。但與此同時,童年對歌謠的親近和喜愛無疑可以借優秀的兒歌繼續擴大和上升,向著更完整的世界和生活,也向著更廣闊的生命和情感。作為兒歌創作者,需要以優秀的作品來承擔兒歌為了孩子的使命,同時也承擔為自己所屬的這一創作領域贏得藝術尊嚴的職責。
兒歌是不會消失的,不論在兒童還是作家的手里。每個時代,只要有孩子,就也會有自己的童謠。舊的留下或不留下,新的繼續長出來。每一代人都住在前人語言的園子里,同時努力為自己和將來的孩子們造起新的房屋。這座屋子,是用母語的聲音和韻律織成的生命最初的巢穴,一個孩子住在里面,感到歡樂,安適,美好。這是我對當代兒歌的藝術未來懷有的一種向往和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