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與成長書寫 ——評許諾晨作品《完美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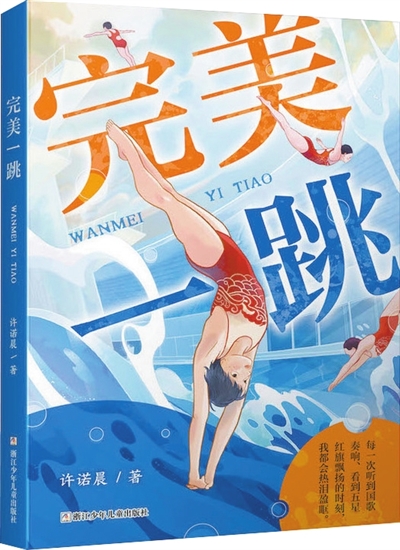
《完美一跳》許諾晨著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2024年5月版
文學雖然是一種借助虛構手法來描摹和反映真實現實世界的藝術實現,但“真”,卻是文學的審美價值追求得以實現的基礎和前提。作家對對象世界真實、合情合理地理解、反映和闡釋,才能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身臨其境的信任感,對作者講述的故事產生“相信”和共鳴。文學,要與鮮活的現實生活有效連接。
文學會因為時代環境的變化,經歷一次次蛻變和更新,但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人的命運、精神和靈魂的關注,不會改變。由此,現實主義創作永遠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舞臺。只是,在創作活動更進一步的發展中,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可以如何探求新的可能?作家們切入現實的方式還有哪些?如何言說、以怎樣的方式言說“當下”?
中國國家女子跳水隊一直有“夢之隊”之稱,這支“無敵之師”,在中國代表團參加過的歷屆奧運會、亞運會和世界級跳水比賽上奪得過無數金牌和獎牌。也因為中國國家跳水隊的“幾乎不可能”的輝煌戰績,跳水運動在中國有著極高的關注度和影響力。應該說,關于跳水運動的新聞報道已經是汗牛充棟了,但關于跳水運動的文學作品卻寥寥可數。
究其原因,跳水運動是一項非常專業的競技運動,其訓練的科學性、運動評價的專業度、對這項運動的界別和相關發展歷史的諳熟,如何像“鹽溶于水”一般,不著痕跡地融入敘事的重重編織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著實是對作家的莫大考驗。
然而,時代和讀者期待著一部關于跳水運動的文學作品——不僅僅在于數量稀缺。在記者們的書寫中,競技體育的世界里,故事主角都是成功者。書寫者們站在確定的終點回溯,為勝利者的勝利增添必然的論據;然而,許多勝利之外的人和故事會被遮蔽、被折疊。
時代與讀者期待這樣一部書寫競技英雄的文學作品——它應該符合文學性的根本邏輯,即撫摸生活的全部細節,將抽象的“偶像”還原為一個具體的“人”,也還原其成長過程中的軟弱、逃離、心傷,在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中回歸生活本身,體察人的生存境遇和成長體驗,注入具有永恒價值的人生哲理。這樣的一部文學作品,應該強調生活的切近,人物的親和,以及人物情感的真切還原,不刻意貼近時代的宏大主題,不刻意書寫崇高。當然,時代風云會作為人物的背景出現,構成人物的生命追求、對意義求索的重要部分。
顯然,《完美一跳》正是一部調和了時代感、現實性、文學性,包括競技體育的科學性的具有沉甸甸分量的文學作品。
文學是對現實的想象和塑造,以構造現實和創造現實。那么,什么樣的現實可以轉化為兒童文學的文學素材?成長,不僅是兒童的永恒追求,也是兒童小說的永恒話語和藝術母題。成長是一種生命存在狀態,更意味著精神的磨礪與蛻變,無疑是觸及少年兒童精神層面的最佳形式。
作為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完美一跳》巧妙地從“成長”這一維度著手,真實再現了趙淼和林欣兩位小跳水隊員的成長過程——既有現實生活世界,更有精神世界。趙淼和林欣兩位小運動員的身后,其實糅合了多位跳水世界冠軍的人生體驗。比如,因為家境貧困,所以渴望出人頭地,改變家庭命運;為了鍛煉體能,和男隊一起訓練,還有早上5點鐘開始的晨跑,400米的跑道跑10圈;比如,因為天賦與勤奮,小將的橫空出世;又比如,如何跨越心理障礙,超越那個“總是贏了自己的人”;還有,小有成績后的懈怠,導致大賽前的狀態不佳;以及,在似乎不可能的情況下,以最后的完美一跳,逆轉了比賽……
少年兒童的文學接受有別于成人讀者,他們更傾向于將文學作品看作是生活的延伸,更易受作品的影響。文學不是理論,但作用于人的心靈,在審美的體驗與感受中,在他人的經驗中認同、洞察、移情、感悟,體驗生活與感悟成長。可以說,最早練體操、后改練跳水的趙淼,從開篇因為不會游泳而“不敢下水”,到最后站在世界跳水最高領獎臺上的成長歷程,為每一位閱讀的孩子提供了激勵人心的成長敘事——那就是,哪怕是世界冠軍,也不是生就的,而是練就的。
溯源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中國的兒童文學是在中國現當代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生長和演進的,總體上與中國現當代的歷史進程保持著密切聯系。兒童文學的藝術聚焦往往集中在現實課題上,展現社會生活與時代風貌;塑造的文學形象,蘊含、濃縮一個時代的精神核心與時代理想。
然而,堅守現實主義的寫作立場,卻非常考驗作家對于現實的把握和書寫能力。與現實超短的審美距離,讓作品很容易就會為現實而現實,浮于表面,甚至成為時代或宏大主題的生硬“圖解”。
如何在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技巧,尤其是現實主義兒童文學的創作技巧上發揚和包容,以與時俱進的文學審美,保持與社會生活的同構順應?
可以說,從事創作之初,許諾晨就展現了自己對故事情節、敘事節奏的掌控能力,《完美一跳》也一樣。這或許是這本明明有著明顯的宏大主題書寫的作品——比如,指向對國家、民族的集體關切,指向主流書寫,指向崇高精神力量——獲得諸多兒童讀者喜愛的原因。
小說畢竟是一種敘事文體,依靠故事情節的發展來表達文本的深層內涵。情節是支撐小說架構的重要部分,沒有情節,故事不可能往前推進。尤其對于兒童文學作品而言,情節是重中之重,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感抒發和價值的評判可能很難與兒童建立起閱讀的聯系。
就《完美一跳》而言,故事的生發有著獨特的張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比如趙淼,在剛剛改練跳水時,對水的畏懼;在一次晨跑時,因身體透支而哮喘發作;在初露崢嶸時,因為母親的病,一度起了要離開跳水隊的念頭;在奪得國內跳水錦標賽的冠軍、入選國家隊之后,一度懈怠,開始愛美和注重打扮,訓練成績一度搖擺,為即將到來的世界大賽之旅抹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
可以說,故事中人物命運的起落,高度喚起了讀者閱讀的興趣;同時,在情節所展現的沖突中,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更加凸顯,人物形象更為豐滿。
再看敘事的流暢度。作品敘事的流暢度,并不僅僅在于敘事節奏的明快,還在于作家對作品敘事邏輯性的整體把握,即怎樣的“因”造就了怎樣的“果”,怎樣的“果”埋藏了怎樣的“因”。小說家能否創作出優秀作品,取決于其對人物意識活動的洞察力。人物的意識決定了人物的行動,造就了人物的命運,這就是情節線的邏輯性。所以,經驗性的材料之間,其實并不一定具有邏輯的聯系——表面上息息相關,但本質上并不互為因果,硬要堆砌、混雜,化解故事的邏輯力量,缺乏吸引讀者深入其中的力量。而優秀的作品,會將一樁樁日常生活圖景,都變成頗富內涵、活力和意味的細節。
此前,在對許諾晨作品《白日焰火》的評論中,我曾經提到不足,“典型人物性格的塑造,不僅需要連接特殊的社會環境,在可視性和普遍性的人物行為方式塑造之外,還需借助心理活動的刻畫,實現其性格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可喜的是,許諾晨一直在磨礪自己的寫作技巧。在《完美一跳》中,她深挖人物的內在性,讀者可以隨時捕捉到人物的狀態尤其心理狀態;塑造人物時,也特別注重人物心靈世界的內在構造。所以,該作也是一部從心靈出發的生活敘事——客觀敘事拉開情節的帷幕,但濃烈的情感一直伴隨著作品。
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頂級運動員如何完成對一個“總是贏了自己的人”的心理魔障的超越。競技體育,冠軍永遠只有一個。可以說,世界一流水平的運動員,大賽之中比的就是心態、心理的穩定。趙淼的恩師陳泓,從國家隊退出,來到省隊當教練,就是因為陳泓進省隊的第一次比賽,以總分不到十分的差距,輸給了同門的運動員郭蘭,從此,無論是國內的比賽還是國際大賽,郭蘭成了壓住她的一座五行山。沒有人不承認陳泓的優秀,可她就是千年老二。魔咒般地,趙淼在省隊的一次邀請賽上,輸給了東海隊的明星運動員陸思,陸思成為了趙淼心理上的“五指山”。全國跳水錦標賽決賽的前夜,陳泓把自己的過往掰開了、揉碎了,“血淋淋”地展現在弟子趙淼前。最終,“她腦海里終于不再想著怎樣才能超越陸思,只想完成這個動作”,趙淼完成了對自己的“心理魔障”的渡越。
作家應該擁有對世界的獨特理解,并把這種獨特理解訴諸文字和故事;由此,文字和故事得以確立獨特性的存在,作品的優秀從而具備了前提性的條件。
所以,作家通過對對象——主人公自我成長經歷的書寫,同時也傳遞了作家對成長的生命體驗和感悟。成長母題因而溝通了作家與讀者,實現了作家對讀者的不自覺的精神引導,實現了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的審美意識的交融與合流。
筆者曾經在一篇評論中論及,現在年輕作家的作品,文字流利明快、濃郁的生活氣息是極大的特色;但另一層面,比起老一輩作家,其文字的深層意蘊和可咀嚼的空間似乎淡了些。但現在筆者進一步的感受是,文學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精神活動,所有的作家,以其主觀去面對和反映客觀現實時,都會千差萬別,而所謂的客觀現實,無一例外會被打上個體主觀的烙印。代際的不同、生活環境的不同、人生歷練的不同、審美傾向與創作觀念的不同,既是個體的不同,更是代際的溝壑。比如,50后、60后作家,筆下總是帶有寬闊的敘事結構和解構分析社會的傾向;70后作家,擅長從生活流的層面探入人物細致入微的心理世界;而新一代的85后作家,明快的節奏感和鮮明的時代氣息,也許正是其作品的藝術特征和文化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