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文藝》2023年第4期|溫亞軍:幸福之家(節選)
編者說
父親早逝,為了兩個弟弟能繼續念書,母親有病可醫,林秀不得已嘗試給有錢人代孕,賺的錢給家里蓋了房子,供兩個弟弟念了書,娶了媳婦——那時他們一家人相親相愛,配得政府贈與的“幸福之家”的牌匾。可現在,兄弟分家了,老娘老了。當官的二弟一心往上爬,傳銷式經營保健品的三弟,只想從她身上賺錢。林秀因不孕被家暴,老娘住院,手足之情失卻倚靠,唯有年輕時相親對象張磊在她身邊……小說語言簡約典雅,意蘊無窮,結構渾然,是藏于無形的經營。題材關注人倫和孝道的崩塌,也表達了作家對女性命運的思索。
幸福之家
溫亞軍
一
昨夜下了場透雨,扯長溝的槐樹林里肯定生出不少地軟。那個林帶里的青苔厚實,是地軟的溫床。林秀在超市上的是夜班,白天除正常補覺外,沒其他事,她想晚睡一會兒,趁著太陽還沒升高,換了身衣裳,來到扯長溝鉆進槐樹林撿地軟。好多年沒來扯長溝了,樹林空地上青苔少得可憐,倒是狗尾巴草異常茂盛稠密,占了地軟生長的空間,偶爾在草叢里能撿到幾個,還沒長開,羊糞球似的縮成一團,半天也難撿滿一把。林秀想起老輩人常說,羊糞是地軟的菌種,如今沒人養羊,這么好的狗尾巴草沒有羊來吃,當然也留不下羊糞,這就斷了地軟的菌種。轉遍了槐樹林,林秀只撿了兩三把地軟,露水卻把褲腿打濕了,鞋子更不用說,已經灌滿了露水,走起來咕嘰咕嘰地叫,怪難為情的。再說,太陽已升當空,夏天的日頭毒,只要從樹梢空隙里漏下來,稍微有一絲照到地軟,它就會縮回去,躲貓貓似的不見了蹤影。
林秀抖了抖提袋,瞅瞅袋底可憐兮兮的這點兒地軟,心里還是挺知足的,回去好好洗洗,夠給老娘蒸幾個地軟包子了。老娘不光有慢性胃病,還有哮喘、帕金森一系列老年人容易患的疾病,長年吃藥也不見好,動不動沒有胃口,幾天不吃一點兒東西。地軟夠新鮮了,說不定能刺激一下她的胃口。提起老娘,林秀不知怎么描述,心里五味雜陳,可她時常還是惦記著老娘,凡事都為老娘著想,不然,哪天老娘要是走了,后悔也沒有用。“子欲養而親不待”,她不知道這話是誰說的,但意思她是懂的,她不想做那“親不待”的“子”。想到這里,林秀嘆了口氣,忽然間情緒低落下來。
午后補足了覺,趁二弟和他的婆娘不在家,林秀帶著蒸好的地軟包子回了娘家。說是娘家,對林秀來說,只有娘,沒有家了。
林秀瞅著二弟家大門外邊新掛的“幸福之家”牌匾,有電腦屏幕一般大,應該是黃銅做的,陰刻著“幸福之家”四個大字,用紅漆描過,下面還落上了“縣委、縣政府”等字樣,標有授牌的日期,比起原來那塊巴掌大小的木頭牌子,是有了天壤之別。可這個類似企業、單位門口掛的大銅牌子,怎么看著都太晃眼,沒有原來的木頭小牌子樸實。先不說這個牌匾,就是這個“幸福之家”的榮譽,與家里有當兵入伍的“光榮軍屬”一樣,上面只有“幸福之家”四個字,是當年村上領導去鄉里開會捎回來的。至于是不是縣上授予的,無法說清,過去二十年了,找誰論證去?再說,也沒這個必要。反正,林秀無法確定,她只知道,換成現在的這種銅質牌子,是老二的行事風格,他以前恨不得把所有的榮譽都寫在臉上,現在更進一步,差點兒刻在臉上,讓這些不可多得的榮譽能夠閃閃發光,為自己掙得更多耀人眼目的光芒。說句實話,這個家里能讓老二炫耀的東西實在不多,這一塊二十年前所得的牌子,老二自然不會放過了。而在林秀的眼里,那塊木牌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只是“幸福之家”那四個字曾像明燈一樣,擁抱過她,溫暖過她,在她最艱難的歲月里,輕輕撫慰她,因為這樣的撫慰,她才在絕望和無助中挺起了腰桿。那不是現實的榮耀,而是充滿力量的家庭氣息,溫潤的,飽滿的,和煦的,甚至是明媚的。
很久了吧,“幸福之家”只成一塊小木牌子,陳舊、黯淡,“幸福之家”上的“幸福”已經是一個沒有了味道的詞罷了。而這個“家”,也早已不是牌子上所指向的家了。
當年能評上“幸福之家”,按老娘當時的說法,多半是林秀的功勞。那年父親突然病逝后,家里的頂梁柱倒了,望著四處漏風的兩間瓦屋和三個未成年的子女,老娘除了哭,無能為力。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怎樣把三個孩子養大,不讓這個家倒塌,才是最現實的。已經有媒人在打老娘的主意,將物色好的男人悄悄地透露給老娘,被淚水浸泡得六神無主的老娘,哪有再嫁的心思,她把憂愁的眼神時時刻刻往女兒身上投放,林秀感覺到了排行老大的責任,果斷地放棄學業,全身心地投入搖搖欲墜的家里。她幫助老娘擋住上門的媒人,小小的人兒過早地下田播種、收割,回家做飯、洗衣,成為老娘最得力的幫手,與老娘一起硬撐起了江家的門面。為了兩個弟弟繼續讀書,將來有所作為,林秀鼓動老娘農閑時一起去給蓋房屋的人家篩沙子、和灰泥,打短工掙兩個弟弟的學費。那些年,說不苦是假的,林秀何曾成長到能夠堅強地把一切扛下來的地步,有個艱難痛苦的過程,她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肩膀并不比兩個弟弟強壯,但每次看到老娘滿含熱淚的目光,那種孤獨無助的神情,她小小的腰板就往上挺,藏在心里的那份虛弱和崩潰感就如同搖搖欲墜的枯葉,風一吹,便沒了蹤影。她不僅僅是為了媽,更是為了兩個弟弟,他們學習都很勤奮,從來不讓她和老娘操心,尤其是老二,父親在的時候還有些懶散,愛跟林秀較真兒,動不動兩個人為一些小事爭執起來,現在突然間就懂事了,再沒跟老娘撒過嬌,每天放學扔下書包會扯著老三跟在林秀和老娘后面忙前忙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三比較貪玩,以前放學后總是尋不著蹤影,在父母的喊叫聲中天黑透了才一身臟亂地摸回家。自父親去世后,老三也變乖了,不再偷跑出去玩,很少再闖禍了。兩個弟弟幾乎一夜之間成長了,她林秀又怎能不更快地成長起來呢?正是一家人齊心協力,度過了最艱難的那幾年,同時也贏得了四鄰羨慕的目光。林秀還記得從村里拿回“幸福之家”的牌子時,她握著那塊木頭做的粗陋牌子,臉上的笑容像春風吹拂的花朵,每一瓣花瓣都因為溫暖和煦而熱烈地綻放。她知道那不只是一塊牌子,而真的是幸福,是幸福的見證,因為一家人的愛,一家人的互愛。
可那些艱難而充滿了愛的日子,后來怎么就消失了呢?
林秀已回想不起來當初“幸福之家”木牌具體的模樣了,不過木頭的質地是柔和的,不像二弟家門口掛的這塊金光閃閃的銅牌,即使是灼熱的陽光照在上面也一樣閃著冰冷的光芒。自從林秀出嫁,走出這個門,這個用她“賣身”的錢蓋起來的,有六間房的兩層樓,就沒一間屬于她了。出嫁前的閨房已被老二的婆娘改成他們兒子的學習室。想想“學習室”這個詞,挺高端的,像個大單位似的。林秀偶爾回娘家來留下住一夜,學習室自然不能再為她開放,只能擠在老娘的那半間屋。就這,老二的婆娘還不高興呢。當初蓋這棟樓的時候,林秀只想著兩個弟弟今后要找媳婦,得蓋氣派些,一門心思為兩個弟弟著想,為了這個家,一點兒都沒想她自己,如今落到此種境地,只能說是自己活該。
每每想到此,林秀心里忍不住酸楚難過,難過之后,還得默不作聲地把那泛起來的酸楚慢慢地擦抹掉。
果然,老娘看到閨女來了,先是一驚,趕忙伸頭往外面瞅瞅,把門掩上,手足無措的樣子,像是碰觸到了不該碰觸的東西,眼神飄忽著,把嘴幾乎貼到林秀耳朵上,悄聲問道,你咋又來了?聲音里透著焦慮與擔憂。
林秀快有一個月沒來看老娘了,聽著這話她很生氣,把老娘推開,故意扯開嗓門兒喊道,我咋就不能來了!后面的話她不想再重復,為啥她就不能來了?這不是娘家嗎,這兩層樓還是她出錢蓋的呢!
老娘又要把嘴往上貼,被林秀制止了。林秀緊皺著眉頭,也沒了好臉色:光明正大地說,別偷偷摸摸的。我又不是賊!
唉,你這是讓我為難。老娘的神色有些尷尬,沒了剛才的緊張,耷拉下臉,還扭向了一邊。
林秀嘆口氣,把地軟包子掏出來,硬塞到老娘手里說,吃口包子吧,剛蒸出來的,還熱乎著呢,地軟餡兒,可香了,想必你多年沒有吃過了吧。
老娘這下沒扭捏,咬了一口包子,竟然抹起了眼淚。
林秀抱住老娘的一條胳膊,搖了搖說,別難過,知道你在兩個兒子、媳婦之間難做人。我也不愛來這兒,看著心里難受。可我就你這么一個牽掛,不來看看,睡覺都不踏實。
地軟包子可口,老娘很快吃完一個,拿起第二個,被林秀攔住了。她怕老娘吃太飽,不去老三家吃晚飯,又得挨老三婆娘數叨,吃也數叨,不吃也要數叨。這個月逢雙,老娘歸老三家管飯。林秀不想給老娘增加煩惱,找了個借口,說地軟太少,她加多了碎粉條,不好消化,得少吃點兒,其他幾個放冰箱里,明兒熱一下再吃。老娘沒有反對,只是從冰箱里又把包子拿出來,攥在手里有些舍不得,最后放進了桌斗里。林秀不好再放回冰箱,任她去吧,幾個包子而已。
本來想問一下老娘,替她問過老三家沒有,林秀想把老三家的小閨女過繼給自己,好讓他們再生一胎。老三一直想要個兒子呢。可看到老娘躲躲閃閃心不在焉,問了也是白問,倒不如自己直接去說,免得繞來繞去。但老三家她是不情愿去的,她受不了那兩口子,可她稀罕他們的小閨女倩倩,尤其是那雙大眼睛心疼人呢。
沒有給倩倩帶零食,林秀不好上門。幾日后,林秀買了一大袋薯片、酸奶、果凍之類的小吃食,算好老娘在老三家吃晚飯的當口,她來看老娘,順便也看看兩個侄女。老娘一句話也不說,生怕三兒子兩口子責怪。老三兩口子倒非常熱情,放下手中的碗筷,像迎接貴賓似的,將林秀扯到沙發上,卻沒說一句讓吃飯的話,直接進入他們的推銷模式。老三近些年搞傳銷,專門給親人朋友推銷食用菌——說是食用菌的提取物,不同的食用菌顏色略有差異的片狀物。在老三的口中,食用菌雖說是保健品,不是藥物,但絕對包治百病,有腫瘤的治腫瘤,沒腫瘤的滋陰壯陽,補氣血,補鈣,補維C,人體內缺啥補啥,補足了提高身體的免疫力,百病不侵,是真正的人間極品。林秀的不孕不育在老三這兒自然首當其沖,食用菌簡直就是為懷不上孩子的女人定制的。你想啊,它能清除人體內的各種贅物,打通各種臟器之間氣血流通的通道,就像山谷中的風能隨意流淌一樣,擁有一個好的身體環境,還怕懷不上孕?前幾年林秀抵不住三弟的軟磨硬泡,吃了三個療程,指甲蓋那么大五六種顏色的菌片,每種顏色吃八粒,一吃一大把,飯量小的絕對可以當一頓飯吃了。她花了近三萬元,肚子卻依然空空,才堅決不再吃了。據老三的食用菌老師分析,林秀本來快懷上了,就差一個療程,這一放棄,前功盡棄,那逐漸土肥水滿的土壤也會因此再次干涸枯竭。在姐姐面前,老三這幾年倒是很有韌性,一直在做姐姐的工作,給她羅列了不下百例成功的典范,林秀堅如磐石,受過一回騙,不再上當,任老三說死說活,在她面前畫多大的餅,繪出多么夢幻的圖景,她就是不松口。老三悻悻罷手,卻終不愿徹底失去這個客戶,不似之前念經一般見面就叨叨個沒完,隔三岔五會見縫插針地給林秀再上一課。老三婆娘是賣保險的,與老三有著同樣的執拗,每次見到林秀都要從頭到尾普及一遍保險知識。人有保險少安危。年輕沒保險,老了很可憐。保險保險,保了沒險。現在的人,誰沒投個保那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活得有質量,人險、壽險、財險,像陳列商品一般,樣樣險種一一羅列,每次都不重復,甚至還讓林秀參保懷孕生子……這是林秀不愿來老三家的另一個原因。她真的是經不住這兩人無休無止地念各種歪經。
兩個侄女倒挺乖巧,姑姑總會給她們買好吃的,愿意多親近,卻沒機會,姑姑被自己的爸媽快撕成兩半了,輪不到她們插嘴。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地看著被爸媽輪流扯著的姑姑,眼神滴溜滴溜轉幾下,也乏了,坐到一旁撕開姑姑買來的零食袋,認真地吃起來。林秀心思全在孩子身上,老三夫妻兩個的話像風一樣,在她身邊搖蕩幾下就自行散開。說得時間長了,總有倦怠的時候,林秀趁著老三夫妻話語間的空隙,掰開兩個人的手,站起來假裝活動身子,突然沖到倩倩跟前,把她抱起來親了又親,故意提高嗓門兒問倩倩,小心肝,姑姑稀罕死你了,你愿意給姑姑當女兒嗎?
倩倩想都沒想,就著滿嘴的零食說,愿意!給姑姑當女兒天天有好吃的!臉正對著林秀,嘴里的零食碎末噴了她一臉。
林秀笑著,騰了一只手去擦臉。
老三婆娘反應很快,沒等林秀的笑聲揚起來,騰出來的手剛摸到臉上,就從沙發上跳起身沖過來給了倩倩一巴掌,罵了句,不要臉的東西!叫你這么賤。顯然是沖著林秀來的。倩倩沒防備這個突如其來的巴掌,哭了。林秀愣了愣,血往臉上沖,還是忍了下來,沒有接老三婆娘的話,一邊哄著哭鬧的倩倩,一邊回頭看沙發上的三弟,看他聽到自己媳婦這樣罵她會有啥反應。誰知老三像沒聽見似的,此時已經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手機游戲上,身子正隨著游戲的速度而左右搖晃。林秀把倩倩放下,沖到老三跟前,輕輕踢了他一腳,她沒用力踢,怕他惱怒。
老三沒理睬,依然沉浸在游戲之中。林秀又踢了一下,這次稍用了點兒力道,老三大概感覺到疼,終于把目光從手機里拔出來,卻問她,怎么著?想通了,那就再吃一個療程,還是三個療程?
老三婆娘在一旁哧哧冷笑,誰也沒看,扯開還在抹淚的倩倩,挖苦道,別凈想美事,啥事都得靠自己,天上掉餡餅的事兒就不要想了,旁人是靠不住的。
像是接老三的話茬兒說老三,林秀卻清楚這話還是沖著她來的。她就納悶了,不就是沒買她的保險,沒再續老三的食用菌,怎么忽然間就變臉了呢?老三像是掀了掀眼皮,有些話還是聽到耳里,卻什么話也沒說,耷拉下眼皮,繼續全神貫注于他的游戲。
林秀耐不住這種難堪,推開要扯她走的老娘,沖進夜幕里。她太天真了,這些年發生的好多事,足以讓她認清老三了,可她心里居然還殘存著對老三的一絲期望,以為他多多少少會把過去的那些生活記憶,像她一樣存放在心里,似暗夜里的燭光一般哪怕只散發出一點兒微弱的光亮。其實這不過是她的一廂情愿而已,就算過去他們家有過那樣一束微光,也早在時間的推移中消失殆盡。無論老二還是老三,過去只是他們艱難不屑的存在,而無一絲溫情可言。至于過繼小侄女,林秀讓老娘說過,她自己只是旁敲側擊地提過,并沒有正經拿到桌面上來說。老三自然不會把她的話當回事,他的腦子里塞滿了食用菌,已經擠不進任何東西。老三婆娘的指桑罵槐——不,就是直接罵她,不過是更深刻地暴露了對林秀的不屑與歧視,赤裸裸的歧視。
林秀有時候想,或許是因為自己以前做過不該做的事情,讓老二、老三漸漸對她心生嫌隙吧。她難道不是為了當時的這個家,為了兩個弟弟?父親突然離世,她是老大,讓兩個弟弟繼續讀書將來有出息,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至于她自己,從未想過在一個破敗的家里除了扛起來的責任還能有什么出路。當時農村的日子太難熬了,僅憑種幾畝地,養幾頭豬、幾只雞,是供不出兩個學生的,就是解決溫飽,還得看老天爺的臉色,那年又碰上大旱,糧食減產,老娘想著讓老二退學出去打工掙錢,怎么說也是男孩子,再細弱的肩也能扛一點兒重量了。老二那時才十五歲,看著很細弱的樣子,去哪兒都算童工,根本沒人敢用,就是用,跟成年人相比,掙的錢肯定是大打折扣。林秀知道老二愛學習,她不愿老二失學,既然老二退學也不夠打工的年齡,還不如她出去掙錢呢,她已滿十八歲,說不定還能有條出路,改變家里的困境呢。
老娘是不想讓林秀外出的,可在家周圍打零工掙來的幾個錢,連糊口都難,老二、老三的學費哪一次不是東挪西借湊出來的,再往后,還要怎么去騰挪?老娘再不舍得也敵不過殘酷的現實,只得同意林秀外出打工。那年,林秀與一幫年齡相仿的女孩,擠了三天火車到了東莞,咬牙花三百塊錢辦了個初中畢業證,進入一家紡織廠,在看似輕松的流水線上,拼的卻是體力,每天十二個小時的工作量,常常追著織機跑著,才能勉強完成自己的工作量。她在東莞租住的是二十多人的大宿舍,什么樣的人都有,雜亂不堪,導致她睡眠嚴重不足,經常在流水線上跑著跑著就打起瞌睡,有幾次差點兒釀成大禍,被工長舉報后開除了。林秀每月給家里寄錢,除了兩個弟弟的學雜費,她還得負擔多病的老娘醫藥費。所以她一刻也不能松懈,又進了其他幾個工廠,情形大同小異,不用多動腦子,體力卻跟不上。那個時候在東莞,林秀與成千上萬的打工妹做著最簡單的夢,掙著沒有什么厚度的錢,奔忙在各種流水線上。那些沒有多少厚度的錢,總是還沒捂熱就寄給了老娘,她不敢忘記自己出來打工是為了什么。
在東莞,除了做夢,機會還是有的。林秀絕不去干出格的事,一起住的姐妹,有的去了洗浴中心,還有的去了發廊,她們一直想把林秀拉下水,說她長得水靈,不趁眼下臉蛋值錢去掙大錢,簡直是浪費。浪費是可恥的。眼看著同宿舍的姐妹一個個地搬走,林秀心里很著急,可她不愿走她們的路。但一個人的人生,不是自己說了算的。林秀二十歲那年春天,她剛從老家過完年回到東莞不久,老娘的老毛病又犯了,因為拖著沒及時去醫院,老娘的慢性氣管炎發展成間歇性哮喘,得住院治療。住進縣醫院沒幾天,押金用完了,醫院不再給治療,林秀的兩個弟弟為給老娘治病,放學后到醫院附近撿廢品賣錢。沒想到撿廢品的都有地盤,兩個弟弟被驅趕時與他們打了起來,差點兒被打成殘廢。林秀得知消息,趕回來看到醫院躺著的三個親人,卻束手無策,除了哭,她沒別的辦法。在這個世界上,哭是最沒用的。林秀抹干眼淚,重新返回東莞,去找以前的姐妹,想干掙錢多的營生。但她有底線,絕對不能突破,姐妹沒法幫她,讓她自己去想辦法,運氣好的話,說不定能傍上高枝呢。
林秀不是在電線桿上看到的那種廣告,而是以前她工作過的廠子有個男人直接找她,給她提供了一條掙錢快的路子。之前,林秀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代孕,猶豫了很久終于答應那個男人后,她才發現,在醫院附近的電線桿上,有不少這種廣告,只是她以前沒有在意。她答應做這個,也是為了家里的老娘,還有兩個被打傷的弟弟。她把自己想得很無辜,所以被那個男人帶去見主家時,她沒有罪惡感,居然有種莫名其妙的——就義感。
主家當然是個老板,沒看到真面目,整個過程他都戴著面具,所以林秀沒法判斷他的真實年齡,更無法看清他的長相。她甚至想著,憑自己的一雙大眼睛,肯定能生個漂亮的男孩。可是天不遂人愿,林秀好不容易熬過嚴重的孕吐期,四個月的時候她被帶去做了檢查,她懷的卻是個女嬰。主家讓她放棄女嬰,做引產手術,如果她不愿再孕,仍然付給她當初商定的代孕金。林秀哭過,后悔過,也動搖過,可她沒法不按主家的規劃行事。流產是痛苦的,養好身體再孕的過程,更痛苦,但林秀什么也不顧了,她也不想別的,這只是她的一份工作,一條她沒想要走卻還是走了的路。她咬著牙堅持再孕,終于為主家產下一個健康的男嬰,得到了相應豐厚的報酬,遺憾的是她沒見上男嬰一面,還在產房就母子分離了。可是,誰也無法抹殺林秀能夠生育的功能,上帝都不能。但上帝卻讓她做了一個夢,一個噩夢。
拆掉兩間舊瓦房,給家里蓋棟樓,是林秀那幾年的最大愿望。村子里蓋樓房的越來越多,更顯得林秀家的兩間瓦房破敗不堪。剛去東莞那幾年,林秀掙不到錢沒能力,眼下有了足夠的錢,她想著蓋個三層高樓,把鄰居家的兩層樓比下去。老娘卻不這么想,她眼里裝著已經長大成人的兩個兒子,心里自有她的盤算,可說給林秀的卻是另一番話:樓不能高過鄰居,一定要與他人平等相處。就是說做人做事要低調,不能太顯擺。林秀想想也對,自己掙的錢不光明正大,理不直氣不壯的,還是不要太張揚,免得別人說閑話。其實,她看透了老娘的心思,只是,她沒有反對,她沒覺得老娘的想法有錯。老娘是為兩個兒子打算,蓋兩層六間房的樓,將來兩個兒子結婚生子了,如果哪天過不到一起,要分家也好分,從中間一分為二,兩個兒子一人三間,誰也不會有意見。設計時就按兩家設計的,兩個樓梯,兩個廚房。反正,林秀將來是要出嫁的,蓋樓時,她根本沒為自己著想,她當時只給老娘提過疑問,兩個樓梯、廚房肯定多余。像我們家這種情況,肯定會一起過日子的。說這句話時,她很自信,想到那塊拆瓦房時收起來的“幸福之家”木牌子,這么和和睦睦的一家人,怎么可能分開呢。老娘當時沒回答她的疑問,只是咧嘴稍微笑了一下。這一笑,后來想想,道盡了人世間的些許無奈。
二
樓蓋起來了,林秀完成了一件大事,想著該松口氣了。但她的人生大事才剛開始,老娘張羅著給女兒尋婆家了。林秀望著慈祥的老娘,竟然撒起嬌了,說,我的娘啊,樓剛蓋起來,我的被窩都沒暖熱,你就要往外趕我了。那時中秋已過,天氣轉涼,加上陰雨連綿,新蓋的樓房里顯得潮濕陰冷。老娘拉著女兒滿是傷痕的手,心疼地說,秀啊,你看你為這個家都熬成啥樣了,手糙得能打磨墻上的膩子了。媽也舍不得你,可也不能耽擱了你,做女人的總有這一天,不能把你熬干了再放手啊。
林秀沒往深處想,老娘源源不斷的淚水到底是疼惜她還是因為別的。她收起好不容易才湊足撒嬌的勁頭,回到現實之中,攀住老娘的肩頭,跟著也哭了。沒有多么心酸,一切都成為過往,眼下只有付出后知足的哭,才能宣泄出她們的幸福。老娘的情緒里又何嘗沒有這種幸福感,兩個兒子將來娶媳婦的婚房有了,而且是寬敞、高大、明亮的樓房,這是個大籌碼,不愁沒女人嫁過來。接下來的頭等大事,就是該考慮把功勞最大的閨女風風光光地嫁出去。哭夠了,老娘又說,媽最疼的就是你了,這個家如果沒有你,媽都不敢想能撐到現在。你爸在地下絕對想不到,他狠心丟下我們孤兒寡母,竟然能把光景過到鄰居們前面。眼瞅著我閨女蓋起的這兩層樓,做夢似的,我夜里睡不著,就想著能把你爸叫醒,讓他睜眼看看,這樓可是秀兒丫頭蓋的,給她倆弟弟蓋的。也讓他瞅瞅,這四鄰八村,哪個閨女能比得過我們的秀兒!娘跟林秀一樣,自始至終都沒有想到這六間房的兩層樓,是不是該有她和林秀的一部分,她是娘,兩個兒子的家就是她的家,而閨女,說到底是要潑出去的水。
為秀兒尋婆家,別的好說,但家里一定要有樓房,兩層、三層都行,必須讓我閨女住上樓房,媽才覺得對得住你。老娘一遍又一遍地說。
當時,林秀覺得老娘的這個要求也不算過分,甚至心想,老娘是用這種方式對她進行彌補,畢竟她是耗費了自己幫家里,其實是幫弟弟們蓋起了樓房。那么,就用婚姻附屬的條件來彌補這份虧欠,才合情合理。
事實上,給女兒尋婆家,一點兒也不比給兒子找媳婦省心。林秀的能干有目共睹,加上林秀長得像她的名字一樣又俊又秀,在此之前早有人上門提過親,只是林秀為改變家庭境況一直在外奔波,沒把個人的事放在心上,一旦老娘要給她說這個事情,她馬上打斷,一點兒也不給滋生的土壤,更別提陽光和水分了。眼下,從表面上看,家庭境況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可內心里,林秀卻沒有了底氣。除過心虛,她時常還有種罪惡感,為自己生的那個莫可名狀的兒子,更為自己將來的丈夫。她拗不過自己內心,更拗不過命運。所以,她現在得毫無保留地提供給她婚姻的土壤、陽光和水分了。再不提供,就說不過去了。
給林秀提親的人中,她見過面的,中意點的是上河村的張磊,長相普普通通,臉還有點兒黑。家里算是有棟兩層樓,三間房,以前用樓板紅磚蓋起來的那種,磚茬露在外面,當時叫一磚到頂。張磊有個外號叫三石頭。一見面,瞅個問話的空當他給林秀坦白,他有個外號:三石頭。林秀當時覺得這個外號很恰當,“磊”字不就是三顆石頭嗎?三石頭也很坦率,見第一面就把自己外號都交代了,不藏著掖著,是個實誠人,將來不會有什么花花腸子。林秀想找個實誠的男人,結婚生子后,一旦自己在東莞的事情敗露,這種男人一般不忍心拋妻舍子。自從給家里蓋了樓,林秀一顆負重的心輕松了不少,生活的壓力不再成為她躬身向前的動力,她以為會生活得自如了。可當她開始為自己的婚姻考慮時,才發現自己心里被種了草栽了樹,在東莞的那段日子,反而是奔忙在流水線上的日子讓她安慰和自足,而給人代孕的經歷,卻像無數根刺,埋伏在身體的不同角落,讓她一想起來,便周身刺痛。她也很奇怪,當時決定去做時,只想著掙錢,而當付出得到了相應的報酬后,反成了胸中塊壘,她卻不踏實了,蓋樓的豪氣煙消云散,心里時常泛起不安。
所以,她要找個踏實的男人結婚。三石頭——張磊是最佳人選。
老娘卻看不上三石頭。他家里一磚到頂的舊式兩層樓,勉強說得過去,關鍵是張磊長得差強人意。臉黑就黑吧,還很普通,沒棱沒角,眉眼之間沒有一點兒能讓人打起精神的靈氣,怎么配得上如花似玉的林秀?再說了,不會手藝技術,也沒個正經職業,不跟著年輕人出去打工,整天守著家里的五畝六分地,幫父母在地里刨食,農閑時在一家超市打短工,掙下仨瓜倆棗,還不夠他的煙酒錢,將來肯定不會有啥出息。老娘想到前些年的自己,那日子多難啊,要不是林秀,她怎么撐得起這個家?好不容易林秀在外面打了幾年工,掙下了這棟樓,咋也不能讓閨女再過以前的日子。其實,老娘心里已有了最佳人選——鄉村教師嚴義海。當時,林秀的二弟林發已從地區的師范學校畢業,在另一個村小學當教師,在老娘眼里,教師是最好的職業,工資雖然不多,可穩定,也不用風吹日曬,出多大的力氣,緊著點兒,每個月的吃喝用度自然是夠的,關鍵是這個職業受人尊敬,大人小孩見了都尊稱一聲老師,總覺著高人一等。老娘有高人一等的兒子,覺得不夠,還需要高人一等的女婿。再說了,嚴義海長相也周正,當然比自己兒子要差半截。沒人能比得過自己的兒子,每個老娘都是這樣想的。林秀的老娘也不例外,她已經讓林發打探過了,嚴義海家里有兩層樓,雖是舊樓,可人家去年給樓的外墻貼了瓷磚,看上去跟新樓沒啥兩樣。
林秀與嚴義海接觸過幾次,發現他除了不像個教師,什么都像。嚴義海不善言辭,有點兒惜字如金,多說一個字,像是從他口袋里多掏一塊錢,他把口袋捂得很緊,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松手。這樣的人當老師,肯定是墨守成規,別想叫他多透露一句書本之外的其他知識,那可是他花了錢學來的,不會輕易傳授給他人的。林秀的認知中,教師就得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哪能像個學生似的,問一句才答一句,自己都沒有激情,拿什么來點燃學生。看看二弟,才當了幾天教師,說什么都能引經據典,羅列出一大套道理來,比起先前的木訥內向,簡直判若兩人,令林秀打心眼里佩服。說句實話,林秀倒也不覺得嚴義海的不善言辭有什么問題,她佩服二弟,不等于就希望嚴義海跟二弟一樣能說會道。她只是說不清對嚴義海的感覺,嚴義海不是嘴笨,他是不說,不說自己,也不問林秀,一副聽之任之的樣子。單從表情和眼神里,林秀看不出嚴義海實不實誠,沒法給他下定義。在她心里拿他跟三石頭做比較,三石頭也不是很能說的那種人,神情憨直不冷漠,但他顯見是想把自己更多地坦露出來,讓她來了解他的。他跟林秀聊天說到以前隨大流出去打工時,因為不夠油滑而備受欺負,他雖然氣憤,但言語里并沒有對那些人和事的謾罵、譏諷,更多的是憐惜人生活的不易。這種平和、淡定很是打動林秀,她在那一刻也安靜下來,沒那么焦慮和惶恐了。
如果從家境、職業、外形,嚴義海占絕對優勢,但感覺這東西沒法說,林秀在比較之后還是覺得三石頭占了上風,這到底是不是傳說中的心動,也就是戀愛,林秀不能確定。成年后,她的心理生理發育都很齊全,卻沒戀愛過,沒嘗過戀愛的滋味兒。這些年來,她的心里只有家,改變家庭狀況,這是她背負的責任,別的她根本無暇顧及。現在,她的人生到了下一站,終于要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她卻猶豫了:選誰好呢?
林秀知道,她的猶豫并不表示她真的沒有自己的選擇。對嚴義海和三石頭,老娘有自己的比較,林秀的心動就顯得很輕微,她就是有兩張嘴,也說不過老娘。何況,老娘還身懷絕技,如果不遂她的愿,就哭。老娘的哭,穿透力極強,自己根本沒有抵抗力。想想老娘與自己受的這么多年罪,她怎么忍心與老娘作對!林秀一直瞞著自己在東莞代孕的事情,至于帶回來的這筆錢,她早編好了一套說辭,稱與幾個要好的姐妹,抓住機遇,合伙販賣了幾次生絲,賺了一大筆。她們見好就收,在生絲價錢出現下滑時退出來分錢各回各家。人一生中有許多話必須爛在肚子里,林秀明白這個道理,給最親的老娘也不能透露半句自己的往事。有些話不能說出來,也即意味著她在好多事情上必須對現實妥協。
所以在個人問題上,林秀不想抗爭,最后決定聽從老娘的安排。
當然,要嚴義海做自己的男人,也沒什么不好。話少也許是好事,林秀可以把它理解為穩重,以后的林秀也不需要過多交流,她需要對自己的過往守口如瓶。有一刻,她甚至惡狠狠地想,嚴義海要是個啞巴,豈不更好。
林秀不再猶豫,把自己交給了嚴義海,可以用一個快生銹的詞來形容:義無反顧。
……
節選,全文刊載于《廣州文藝》202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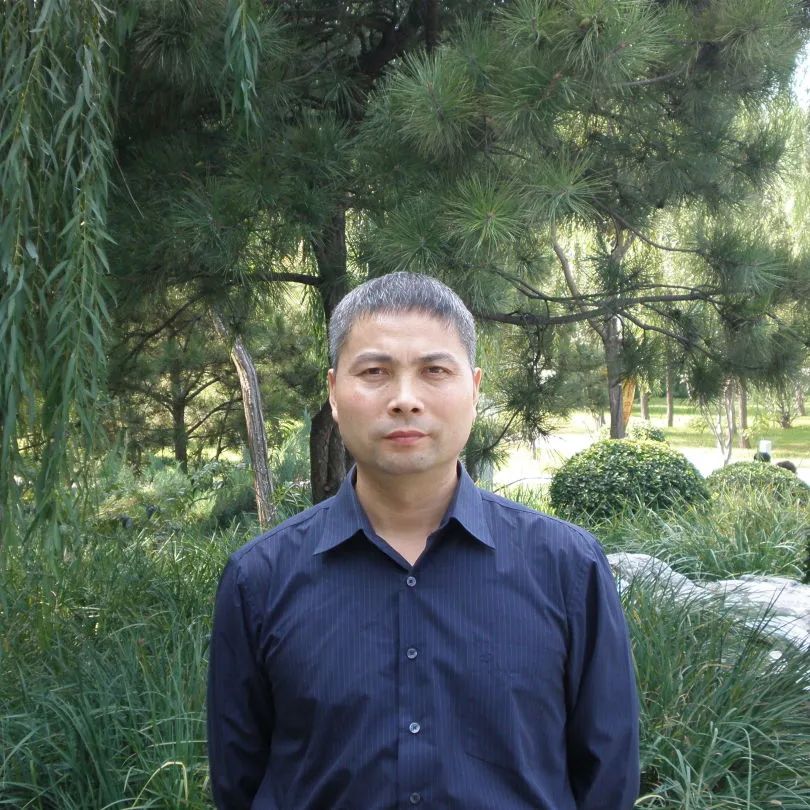
溫亞軍,1967年10月出生于陜西省岐山縣,1984年底入伍,現居北京。著有長篇小說《西風烈》《偽生活》等七部,出版小說集二十多部,《溫亞軍文集》(五卷)。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一屆莊重文文學獎,首屆柳青文學獎;《小說選刊》、《中國作家》、《上海文學》等刊物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日、俄、法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