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廣宏:流派研究如何再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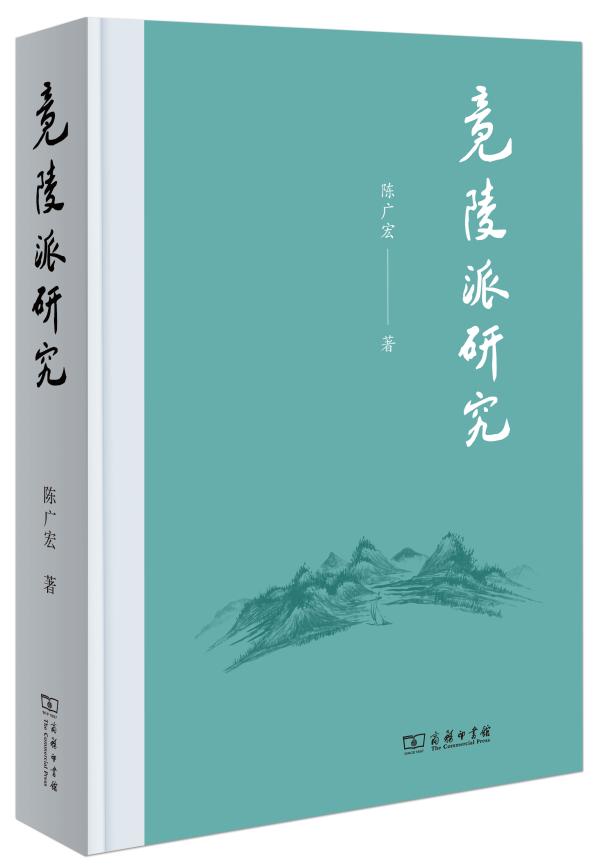
《竟陵派研究》,陳廣宏 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12月版。本文系《竟陵派研究》一書后記。
此次重版的《竟陵派研究》,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作業,該如何修訂,其實頗費踟躇。二十年來,自己關注的領域雖不斷有所轉移,然對于晚明文學及其流派研究,難免因偏愛而仍有留心,不少從事相關研究的同行特別是年輕學者,也常常樂意與我分享他們的看法,這又促使我時不時地回過頭去,重新檢點曾經耕種過的園地。目前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在可見處,將時間的指針撥至當下:最為明顯的,莫過于將所掌握的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從2005年增補到2020年,并對新世紀二十年該領域研究史做出簡略的檢討。當然,趁此機會,于所有引用文獻檢核一過,補訂并更新了一些引證資料,個別章節做了增刪,全書文字也略有潤改。不過,框架結構未變,論述的角度、觀點未改,即便自悔少作,畢竟不是重起爐灶新寫一書,不如就此留存一個樣本,作為我們這一代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受訓練的見證。
現代人文學科建立以來,文學流派研究一向被視作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或闡釋文學發展的一種視角、方法,其研究范式的構建,因而直接關涉整個文學史體系的格局與內涵。在另一方面,相比較文學史而言,它可以是更為基礎、更為本原,因而也是更為原創的研究,或許能更為靈敏地感受到面臨的困境而即時予以調整、更新。時至今日,我們重又行進至學術范式轉換的十字路口,流派研究如何再出發,尋求新的突破,同時也是為文學史研究探索新的空間,積聚的焦慮更顯迫切。
在古代文學的傳統中,詩文流派被認識并非具有很長的歷史,明確以體派標示的,大抵南宋才出現,因文學思想交鋒而立門庭、爭宗主更是明代中晚以來的事。當清前中期郭起元以《明詩派說》反省“明之中葉為尤甚”的以派言詩的現象時,看上去“詩派”已被單獨拈出,作為被考察、論說的對象,卻畢竟不曾拉開距離,而將反對響應風從而成派者作為對明代詩學問題的回應,批評其“聲名盛而實學衰,標榜多而性靈少”,令“詩道之降而日下” ,故而僅僅透露出明清學術轉捩的消息。不過,如他強調不容以一二人之好尚盡一朝之詩,仍執著于知人論世的方法,還是成為我們今天反思鏈索的一個端點。
如果說,傳統社會士人觀照詩文流派的視點更多地落在因人的各種關系而形成群體,因時代風會轉移而變化氣質,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那么,現代學術首先試圖究明的,是流派之所以成其為流派并相互區隔的標準,其性質、范圍的確然界定。故近現代以來,判定詩文流派成立的兩個核心要素皆已受到關注。一個是作為流派發起者或宗主的文學思想及主張,包括其理論自覺的程度及其影響力。在這方面著先鞭的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開啟了一種文學思潮史的寫法,以梳理各時代不同派別所呈現的文學評論為主線,其中尤詳者為形態相對完整的明清三大詩說——“這三者在中國的詩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觀念構成及傾向成為甄辨異同的重要標志,相關探討還明顯影響到中國本土的批評史研究。
另一個是流派代表作家創作上的風格形態,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張大東在《國聞周報》上連載長篇之論《中國文學上之“體”與“派”》,運用西方文學論的認識框架,將與style對譯的“文體”或“風格”,作為作品上判定個性之表現。由此出發,以一種歷史的眼光,發現“模仿”與“創作”(即“因襲”與“創造”)的“互相為利之用”,構成遞演遞進之張力,而這種基于個性的風格形態,亦因而成為“縱的文派之所由立” ,顯示了頗為辯證的思考。
從研究體制來看,流派研究作為一種中觀研究,其走向成熟又有賴于作家研究與文藝思潮研究各自的進展:作家研究作為個案研究,是流派研究的基本構件,當作家論從傳統的印象式批評、文苑傳敘論轉換至運用傳記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手段,分析一個作家的成長過程及其獨特的精神與藝術風貌,它所建立的坐標幾乎是全方位的,如余冠英先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為劉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撰寫書評,闡釋該著中如何說明作家個人作品的特色和它轉變的根由時,曾據其從屈原到李商隱十多位作家的論述,總結有如下的考察因素:1.時代精神,2.地方色彩,3.民族特性,4.階級背景,5.社會風氣,6.生活體驗,7.思想宗派,8.家庭環境,9.文學傳統,10.知識范圍,11.遺傳,12.個性 。所列豐富、全面的層次結構,就其認識閾內,至今難有糾補,無疑體現那個時代對科學思維的追求。
文藝思潮研究往往以史的敘述作為流派研究的經脈,它更側重思想、理論的歷史語境及其發生發展的具體進程,并不孤立討論作家作品,而是清理出貫穿各時代的總體文學思想或表現傾向,并注意尋繹其與政治、宗教、學術、習俗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內在關聯,在一種長時段的觀照下,力圖在眾多紛雜的現象中歸總出深層的精神結構與審美結構。因而至少在宏觀層面,能為流派的考察提供某種背景裝置。這種研究,無論其方法、樣例,在四十年代亦已成就。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撥亂反正,在學術、文化等領域均表現出于“五四”精神、“五四”模式的重新發現。就流派研究而言,如程千帆先生為指導博士生設計的“唐宋詩歌流派研究”系列,即展示重要信號——那意味著接續學術現代化的歷程,在上述作家研究、文藝思潮研究已經達成的地基上重新構建模板;此后,遼寧大學出版社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各自推出“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叢書”,表明引起學界較為廣泛的響應,并形成相對穩定的共識。這一熱點的出現,也成為文學史研究的某種突破口。文學史研究重又回歸實證的立場,回到朗松所說的“達到客觀的事實”為第一要務 ,并且有了文學社會學的加持。概而言之,在那個標記我們成長的年代,所謂“明變求因”,幾乎構成大家研究習得的認識論框架及學術合法性的由來。
平心而論,那個時代的學術可以說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的知識短板是顯著的。當初此書算是本人的第一部學術專著,魯鈍如我,于所受學術訓練既未能做到練達無礙,檢點起來,失當處不少。迄今又強烈感受到時代發展、知識更新之迅猛,無論文學、史學,皆已面貌大變。一種已經積淀下來的模式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是否仍存在盲點,被統一性敘述篩汰的那部分歷史該如何處置,這些恐怕是我們須不斷自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做一種解構的工作以去蔽,或許才是邁向“事實”的有效途徑,故而史學批判的重要性日顯。有鑒于此,本書確亦仍有其作為批判的案例的價值。
感謝王水照先生為拙著題簽。回想起本科在讀時,曾擔任王先生專業課的課代表,轉瞬四十年匆匆而過,老師耄耋之年仍賜字鼓勵,感恩莫名而又感慨萬端。感謝賀圣遂先生一直以來的關心、支持,鮑靜靜總經理的精心策劃,責編周祺超的辛勤付出。門下姚雅馨、張芾、周榮諸生服其勞,或查核引證文字,或整理參考文獻;金美羅、多田光子、許建業、欒曉明諸學侶以及老同學王崗教授助力收集海外及港臺相關研究動態及圖像資料;內子郭時羽一如既往地佐理審校:并此申謝。李夢生先生是我多年來的師長,學養深湛,在業界素有聲望,此次慨允擔任本書外審,至感高誼,謹致謝忱與敬意。
陳廣宏
辛丑臘月于抱樸守拙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