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常故事里的人間溫暖 ——評(píng)吳洲星的《碗燈》和“水巷人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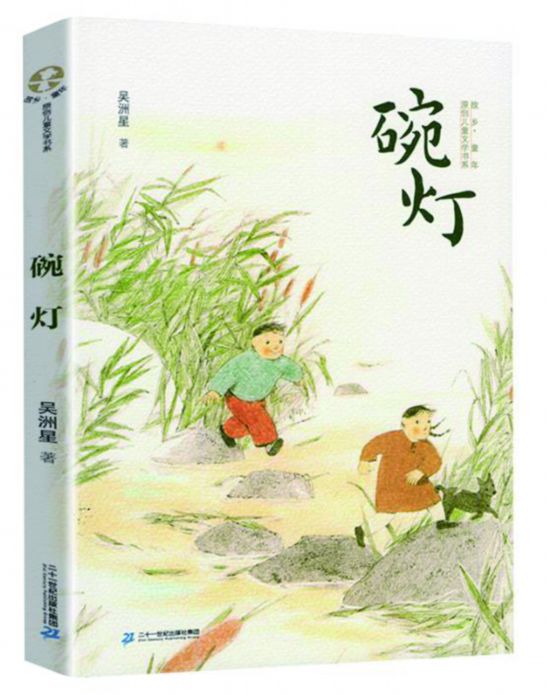

自吳洲星大學(xué)畢業(yè)出版第一本長(zhǎng)篇小說(shuō)到現(xiàn)在,11年時(shí)間出版了三十余種作品,其中差不多一半是長(zhǎng)篇,這樣的數(shù)量十分了得。
作家有不同類(lèi)型,但概而言之無(wú)非是兩類(lèi),一類(lèi)作家只寫(xiě)自己熟悉的、與自己心性相近的故事,另一類(lèi)作家卻不僅限于此。借用戲劇術(shù)語(yǔ),即分為“本色”和“性格”兩類(lèi)。“本色”和“性格”本身并沒(méi)有高下之分,本色演員和性格演員都可以產(chǎn)生經(jīng)典作品,作家也一樣。我樂(lè)意用“性格作家”或“職業(yè)作家”來(lái)定義吳洲星。她雖然年輕,但已稱(chēng)得上是一位視寫(xiě)作為事業(yè)的執(zhí)著的寫(xiě)作人了。
吳洲星此次推出的《碗燈》和“水巷人家”系列五冊(cè),故事發(fā)生的背景都在江南水巷。時(shí)間上,《碗燈》講述的是民國(guó)故事,“水巷人家”系列則相對(duì)比較模糊,總的來(lái)說(shuō),都可以“過(guò)去的”江南水巷故事稱(chēng)之。《碗燈》里的小碗、燈兒,《白雪豆腐》里的小齡、《菩薩的孩子》里的寶壽、《鴨背上的家》里的草生、《漂流的紙船》里的小滿(mǎn)、《鐵花朵》里的鐺子,都是過(guò)去年代江南水巷再尋常不過(guò)的人物。乞討、挨餓、學(xué)戲、念書(shū)、與流浪狗相伴、狂廟會(huì)、做豆腐、賣(mài)豆腐、養(yǎng)鴨、放鴨、游泳、搖船、瞎子算命、拜菩薩,去鐵匠鋪學(xué)徒、把無(wú)力撫養(yǎng)的孩子送往尼姑庵等等,都是過(guò)去年代江南水巷隨處可見(jiàn)的尋常故事。唯其尋常,唯其普通,所以可信。在這些尋常故事里,我們又總能看到小主人公們面對(duì)磨難、坎坷、困境時(shí)的勇氣和擔(dān)當(dāng)。
而這中間,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散溢在字里行間的人間溫暖,有小伙伴之間的彼此溫暖、親人之間的彼此溫暖,還有非族類(lèi)非血緣兩代人之間的彼此溫暖。點(diǎn)點(diǎn)滴滴,隱隱顯顯,無(wú)處不在。這種溫暖是普通人生存和生活下去的信心、動(dòng)力和希望。
為了孩子的未來(lái),瞎子爸爸下決心將小滿(mǎn)送到周老師家寄養(yǎng)。“小滿(mǎn)一聽(tīng),一下子就哭了:‘爸爸,你不要我了?’瞎子臉上笑著,心里卻一陣陣發(fā)疼,說(shuō):‘爸爸怎么可能不要阿滿(mǎn)?只是爸爸老了,不能再照顧你了。’‘那我照顧爸爸。’小滿(mǎn)眼淚汪汪地說(shuō)。‘阿滿(mǎn)要上學(xué),要去念書(shū),’瞎子摸摸小滿(mǎn)的頭,‘阿滿(mǎn),你不想上學(xué)嗎?’小滿(mǎn)不作聲了。”第二天,瞎子外出算命,忽然聽(tīng)到有人叫爸爸。“小滿(mǎn)‘啪嗒啪嗒’地跑過(guò)來(lái),她跑得很急,天一亮她就跑回水巷來(lái)了。她回來(lái)的時(shí)候瞎子已經(jīng)出門(mén)了,小滿(mǎn)就一直等著,等了一天好不容易才等來(lái)了瞎子。‘阿滿(mǎn)……’瞎子的聲音有抑制不住的激動(dòng)。‘爸爸爸爸……’小滿(mǎn)撲到瞎子的懷里。‘爸爸,我好想你。’小滿(mǎn)聲音哽咽地說(shuō)。‘爸爸也想阿滿(mǎn)。’瞎子說(shuō)。”瞎子爸爸再次把女兒小滿(mǎn)送回到周老師家,從此便消失了蹤影,整個(gè)水巷沒(méi)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父女情深,感天動(dòng)地。這是《漂流的紙船》(“水巷人家”之一)中的尋常故事。
流浪兒?jiǎn)“托⊥氡华?dú)居剃頭匠老秦收留領(lǐng)養(yǎng),兩個(gè)孤獨(dú)的人走到了一起,彼此關(guān)心,彼此幫助,彼此撫慰,讓昏暗困苦的生活有了一抹亮色。小碗在老秦的呵護(hù)下,一天天長(zhǎng)大,學(xué)會(huì)了剃頭,學(xué)會(huì)了生計(jì),學(xué)會(huì)了感恩。老秦病后初愈想洗個(gè)熱水澡,小碗燒好熱水,為老秦剃頭、澆水、搓背。老秦好不享受,不由想到自己小時(shí)候給父親洗澡撓背的情景。小碗換上了第三桶熱水,輕輕地推了推老秦。“‘小碗,你要跟我說(shuō)什么?’‘嗯……’一個(gè)小小的手指頭在他的背上游下來(lái)。‘這是什么撓法?’老秦覺(jué)得有點(diǎn)癢,咯咯笑起來(lái)。手指頭繼續(xù)在背上游走。‘喲,你這是在我的背上寫(xiě)字呀?’老秦明白過(guò)來(lái)了,笑起來(lái),‘今天學(xué)堂里學(xué)了什么字呀?’小手在老秦的背上繼續(xù)畫(huà),似乎一直在重復(fù)著兩個(gè)單調(diào)的筆畫(huà)。‘你這寫(xiě)的是同一個(gè)字吧?’老秦也感覺(jué)出來(lái)了。小手固執(zhí)又單調(diào)地在老秦的背上畫(huà)同樣一個(gè)字。一撇,豎彎鉤。老秦?cái)傞_(kāi)掌心,也寫(xiě)起來(lái)。一撇,豎彎鉤。寫(xiě)完,老秦的手指頭懸在了那里。‘小碗,’老秦頓一頓,‘你莫不是……你剛才在喊我?’老秦屏住了呼吸,聽(tīng)到背后傳來(lái)一個(gè)聲音,聲音小小的,有些害羞:‘嗯——’老秦終于明白過(guò)來(lái)了,原來(lái)小碗一直在喊他,可他沒(méi)聽(tīng)懂,小碗就在他的背上寫(xiě)了這么個(gè)字。老秦的眼睛濕潤(rùn)了。”整個(gè)故事直至最后,也始終沒(méi)有說(shuō)出“爸爸”兩個(gè)字,但這兩個(gè)字誰(shuí)都知道。沒(méi)有血緣關(guān)系的小碗和老秦,不是父子,勝似父子,這是《碗燈》中的尋常故事。
人間溫暖是“水巷人家”系列的底色。
吳洲星的作品很少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但又總能引導(dǎo)、把握讀者的閱讀,她比較注重人物的性格發(fā)展、故事的邏輯和細(xì)節(jié)的把握處理,這恰是小說(shuō)寫(xiě)作者最不可忽略的基本功。吳洲星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有一個(gè)很清晰的定位,就是寫(xiě)人物及其性格發(fā)展。這使得她的創(chuàng)作與不少只關(guān)注故事、不關(guān)注人物性格發(fā)展的同齡作者拉開(kāi)了距離。《碗燈》中寫(xiě)了小碗、燈兒、老秦、慧心等人物,小碗和燈兒是流浪兒,老秦是獨(dú)居剃頭匠,慧心是滴水庵的尼姑。作品中的小碗和老秦、燈兒和尼姑分別走到了一起,而小碗、老秦和燈兒、慧心之間又彼此有了來(lái)往和交集。從本質(zhì)上說(shuō),這四個(gè)人的內(nèi)心深處都是孤獨(dú)孤寂的,都是缺乏撫慰關(guān)愛(ài)的個(gè)體存在,都是社會(huì)底層的討生活者。當(dāng)孤獨(dú)孤寂的人遇到同類(lèi),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會(huì)產(chǎn)生怎樣的變化?這樣的設(shè)定為人物的性格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探求、刻畫(huà)和塑造的空間。
故事的邏輯就是故事的合理性。對(duì)讀者而言,故事合不合理,意味著故事是否真實(shí)可信,是否符合特定空間里“就該如此”的藝術(shù)設(shè)定。前面提到的《漂流的紙船》中,瞎子爸爸與女兒小滿(mǎn)的別離故事之所以觸動(dòng)人,就在于這個(gè)故事有合理性,符合邏輯。瞎子爸爸再次送女兒小滿(mǎn)回周老師家后不辭而別,這樣做是因?yàn)樽约菏窍棺樱昀象w弱,沒(méi)有文化,無(wú)法為女兒提供一個(gè)豐衣足食、接受良好教育的美好未來(lái)。盡管萬(wàn)分不舍,但又只能如此。而自己所沒(méi)有的,周老師都能提供。周老師有文化有知識(shí),膝下無(wú)兒無(wú)女,視小滿(mǎn)如己出,很樂(lè)意領(lǐng)養(yǎng)、培養(yǎng)可愛(ài)懂事的小滿(mǎn)。對(duì)于小滿(mǎn),她不知曉爸爸的真實(shí)想法和動(dòng)機(jī),只知道周老師夫婦對(duì)她很好,但那是老師的好。她當(dāng)然不能沒(méi)有爸爸,所以才從周老師家跑出來(lái)尋找自己的爸爸。這里的情感沖突和高潮點(diǎn)在于,小滿(mǎn)不知道這是自己與爸爸的最后見(jiàn)面,而爸爸則知道這是自己與女兒最后的見(jiàn)面,可自己偏偏又不能把這一切告訴女兒。在知情與不知情、隱忍與呼號(hào)之間,父女情深久久彌漫。
細(xì)節(jié)的挑選及精準(zhǔn)把握,從來(lái)都是衡量作品成功與否的一個(gè)重要指標(biāo)。吳洲星作品中的很多細(xì)節(jié)都可圈可點(diǎn),前面提到的《碗燈》中,小碗幫老秦洗熱水澡,又在老秦背上寫(xiě)字這個(gè)細(xì)節(jié),就讓人過(guò)目不忘。由于自己是啞巴,他無(wú)法用自己的嘴說(shuō)出“爸爸”這兩個(gè)字,只能在老秦的背上反復(fù)寫(xiě)兩個(gè)字。老秦說(shuō),小碗幫他撓背讓他想起了小時(shí)候自己幫父親撓背,小碗只是用“嗯”來(lái)回應(yīng)他。小碗輕輕推了推老秦,老秦問(wèn)小碗想說(shuō)什么,他感覺(jué)到小碗在自己背上不停地寫(xiě)著相同筆畫(huà)的字,問(wèn)小碗是不是在喊自己,他說(shuō)再喊一聲、再大聲點(diǎn),無(wú)論怎么說(shuō),小碗都反復(fù)用“嗯”的一聲來(lái)作回答,堅(jiān)定而意味深長(zhǎng)。那一刻,老秦的心里“升起一種從未有過(guò)的幸福感”,這就是細(xì)節(jié)的力量。
《鐵花朵》(“水巷人家”之一)中,鐺子給鐵匠師父當(dāng)學(xué)徒,一開(kāi)始感覺(jué)很新鮮好玩,后來(lái)才知道這活計(jì)太累太苦,打鐵鋪一天到晚爐子都是旺的,待的時(shí)間長(zhǎng)了,身上的衣服都被汗?jié)裢噶恕f€頭鈍了,加熱后抻長(zhǎng)一些,叫“拍”;拿鋼片貼在鑊頭面上,燒成熟火后趨熱捶打黏合,叫“鋼”;鋤頭磨薄了,將鋼片燒得蠟樣幾近熔化,趨熱涂抹在同樣紅熱的鋤面上增加厚度,叫“滲”。學(xué)會(huì)這些以后,鐺子以為自己能打鐵了,師父卻讓他先學(xué)拉風(fēng)箱。師父說(shuō):“不是讓你學(xué)拉風(fēng)箱,是讓你掌握火候。什么時(shí)候打熱鐵,什么時(shí)候打紅鐵,都講究個(gè)火候。火候掌握好了,能把兩塊鐵板粘貼得天衣無(wú)縫;掌握不了,鐵板雖然粘上了,可終是兩張皮。”鐺子這才知道打鐵有打熟鐵和打紅鐵之分。有趣的是,師父有時(shí)還一邊打鐵,一邊唱《十女夸夫》:“世上不如打鐵漢,鉗子錘子來(lái)抖威。先打大姐錛刨與斧鋸,后打二姐鑿子錘……”這是一個(gè)鐵匠鋪學(xué)徒眼中的打鐵情景,又何嘗不是底層民眾在艱難困苦環(huán)境下的職業(yè)操守、自我約束和樂(lè)觀面對(duì)世界的人生態(tài)度,同樣是細(xì)節(jié)的力量。
吳洲星的寫(xiě)作正在路上,路雖漫長(zhǎng),但天地寬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