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風景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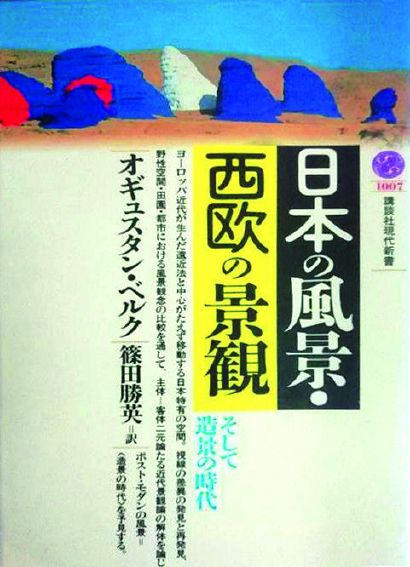
法國地理學者邊留久及其《日本的風景和西歐的景觀》
明治時期“風景之發現”
當代法國地理學者邊留久(Augustin Berque)認為,風景在西歐并不是一開始就被發現的,而是誕生于16世紀都市居民以田園為風景而描繪出來的風景畫中,與近代主體的確立一起出現。即近代的自由的自我獨立的同時,作為客體的自然也獲得了獨立。西歐風景發現是都市居民對農村田園風景的發現,近代風景的誕生意味著將環境客體化的主體的誕生。這種主客二元論支配著啟蒙之后的整個歐洲社會,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開始面臨胡塞爾所說的科學主義危機。為了解決這種危機,20世紀末期的邊留久,試圖在曾經遭受西方近代“風景之發現”影響的非西歐社會的傳統風景表述中,尋找變通的可能性,并最終將目光聚焦在了在處理主客關系問題上采取不同形式的中國和日本的風景觀。
邊留久最初發表的著作《空間的日本文化》首先將焦點放在了日本文化中的空間意識,對產生這種空間意識的日本風土寄予關心。日本的空間是什么呢?產生這種空間的日本風土又是什么呢?其研究成果集結在《風土的日本——自然與文化的通態》中。邊留久在這些著作中所關心的問題是日本特有的“型”。西洋文化中沒有而僅存在于日本的“型”到底是什么?邊留久的這個問題最終導向了對日本文化之型的發現。他認為,傳統日本型文化有兩個主要表現,一個是“場所優越于主體的場所中心主義”;另一個是從主體的中心視角向多中心視角的轉變。邊留久舉例日語中很少出現主語的語法構成來說明日本空間文化中的情景主義和去中心化的特質,還舉了西洋風景表現中的遠近透視法的空間處理方式,強調主體在畫面外觀看風景和景觀的風景觀,這與東方風景表現中的多中心視角的方法極為不同。(邊留久:《日本的風景和西歐的景觀》)
邊留久通過風景考察,承認日本傳統風土觀念中看待事物的固有方式,而且指出其與歐洲和其他地區明顯不同,可謂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產生了一種文化比較論的可能。另一方面,邊留久還這樣描述風景,“風景是風土的感覺性象征性的層面”。只要人還以風土方式生存,觀看并使用語言進行表現,風景就會顯現。也就是說,風景與人類經驗的所有層面相關聯。然而,邊留久并沒有在風景問題上停留于去中心化的議題。因為風景畢竟不是遠眺或俯瞰的對象、事物,而是主體通過感覺知覺而身體性地與世界的關系性存在,所以不得不追問與環境的關系。如果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本身在風景中呈現,那么就要問,是否能夠接受與自己所熟悉的風景不同的其他風景。文化型雖有很多,但人們一般來講對于自己生存于其間的類型抱有特別的關心。如此就出現了一種與去中心化相反的趨勢——再中心化,這也是隱藏在作為日本文明論的近代風景觀中的重要議題。
如果回顧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日本社會,會發現西歐近代主客分離的風景論范式的輸入,改變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多視角主體性的風景體驗,從而導致了日本對本土風景特性的遺忘。因而有關近代風景“發現”的故事,在圍繞日本近代化與“近代的超克”的思想脈絡中被反復討論。象征歐洲文明普遍性的全景式風景觀以其近代主體性的理性姿態,成為明治日本全面歐化政策中的重要性環節的同時,憑借歐洲作為“我思”的“內在的人”的內向顛倒,完成了對風景之起源(空間歷史性)的遺忘,并因此促成日本近代“風景之發現”。
換言之,“風景之發現”并非存在于由過去至現在的日本自身直線性歷史之中,而是存在于某種扭曲的、顛倒了的時間性中,但已經習慣風景的人則看不到這種扭曲。(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內面的人正是活在這種扭曲的時間中的人,且他在空間上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毫不關心,是一個孤獨封閉的個體。所謂內向的顛倒,則是指內在的人在觀賞外部風景時,首先將其作為一個概念,而非實在的“事件”。為了能夠看到作為對象的實在事件,超越論式的“場”必須顛倒過來。即外在于人的實在事物原本現實所處的“超越的場所”,必須通過一種認識的裝置,以透視風景的形象呈現在人類內在視覺的空間場域之上。這是西歐風景之發現的關鍵,雖與傳統日本風景的誕生有所差異,卻在歐洲文明普遍性的勢頭下,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其影響。日本則在一面審視著其與亞洲文明的傳統關聯,一面朝著西方文明的方向邁進。在這整個過程中,風景作為一種隱喻,呈現出日本文明論的風土學譜系的復雜結構。
柄谷行人認為:“‘風景’在日本被發現是在明治20年代(1887—1897)”,“作為風景的風景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也僅限于這樣思考時,我們才可以看到‘風景之發現’包含著怎樣的多層意義。”“所謂風景是指一種認識的裝置”,柄谷行人由此感受到了明治日本風景的發現受西歐近代風景觀影響的明顯痕跡。他指出國木田獨步以文學書寫將“武藏野”風景化的實踐操作,實際上是接受了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西歐文明近代風景觀影響的結果。(《日本的風景和西歐的景觀》)然而,從另外一個側面來講,風景之發現既然是源于“內在的人”的扭曲的內向顛倒,那么這種顛倒有必要回歸正常的平面嗎?換言之,內在的人對風景的普遍性追求,是否必然會摧毀對于風景的特殊性執著?在普遍性追求與特殊性固執之間能不能達到一種平衡?具體來講,在關于日本的風景發現問題上,全面歐化政策和日本國粹主義之間能否實現矛盾的統一?對于日本人來講,這是事關日本文明如何在世界中自我定位的重大問題。
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
論述明治時期日本近代風景之發現時,經常被拿來討論的是明治27年(1894)出版的志賀重昂(1863—1927)的《日本風景論》。《日本風景論》主要由四部分構成:“日本氣候洋流多變多樣” “日本水蒸氣數量巨大” “日本多火山巖” “日本流水侵蝕嚴重”。志賀重昂從看似對物質風貌的地理記述出發,對風景加以精煉,進行詩意的說明。即一方面科學地描述風景,另一方面在其中插入漢詩文、和歌、俳句、山水畫,從而滲入了強烈的傳統風景意識。試圖在保有既存傳統風景的同時,從客觀科學的地理知識構建出新的風景觀。因此,他在《日本風景論》中沒有否定江戶時代的名勝圖繪,而是通過新的科學的擬因果目的論的方法對傳統日本的風景美加以再編,進行圖式化的轉換,賦予其均質的平面性特征。例如他對傳統名勝比叡山的記述:
從京都市經田中、一乘寺……抵達山之西麓,再由大津町至日吉神社,登社十町有花摘社,花摘社到延歷寺中堂二十町,從中萱出發經八町而登頂,頂謂“四名峰”,京都全市、加茂川平原、琵琶湖全景、“近江八景”悉集眉端,宛然一大全景攝影,只有北方被比良岳所遮斷。(小島烏水解說:《日本風景論》)
這種平面的、全景畫的、繪畫性(如畫)的風景觀在《日本風景論》中隨處可見。其特點是,與比叡山相關的宗教話題皆未言及。即使有羅列寺廟和神社的名稱,也不過是發揮了單純路標的作用。毋寧說《日本風景論》具有科學主義的反宗教性格。如此一來,舊有的名勝古跡被剝奪了其宗教的垂直性和特權性,在圖式化的操作中成為無差別的均質平面。可以說,志賀重昂對被剝奪了傳統名勝古跡之特權性的全景投影式風景之發現,有著時代脈絡中“風景論”的近代性特征。志賀重昂將山頂眺望者形容為“并非人間之物,宛若天上人”“從地球以外的星球上眺望地球”。可知《日本風景論》的全景投影的平面中沒有人的身影。雖有作為附屬景觀的人的出現,卻欠缺產生風景的生生不息的人間生活的過程——社會和歷史。
風景不是純粹的自然現象,而是在時間中形成的社會歷史性產物。由此看來,對于所有人類生活景象的漠不關心,都反映出風景論的缺陷。然而,正是這種所謂非人的性格,通過把事實與價值直接統一的方式,導致了自然的道德化(自然的浪漫主義化),道德的自然化(文學的自然主義化)。例如在比叡山和山岳信仰的例子中,被剝奪了宗教的垂直性和前近代的歷史性而形成均質的平面的風景論,便也同時剝奪了科學和文學(藝術)之間的人間的、社會的、歷史的媒介,文學(藝術)從而就直接自動地歸結為科學所進行說明的自然的所與。這種主客分離前提下的自然主義產生的媒介性的不在場和概念的抽象本質,反而將人們的目光引向形成自國國民道德情感獨特性的特殊自然風物之上,形成“江山洵美是吾鄉”的自我認知。它支撐著貫穿《日本風景論》的強烈的國粹主義主張,認為日本的風景美優越于歐美和亞洲諸國。
志賀重昂對于自國風景的客觀描述向國粹主義的情感轉變,呈現出嚴重的封閉性特征。所以在內藤湖南以志賀重昂風景論為引,而導入他有關中國瀟湘八景和日本近江八景的區別時指出:
瀟湘八景與近江八景之間存在相當大的不同。瀟湘八景是江天暮雪、瀟湘夜雨、山市晴嵐、遠浦歸航、煙寺晚鐘、平沙落雁、漁村夕照、洞庭秋月。近江八景是比良暮雪、唐崎夜雨、粟津青嵐、矢橋歸帆、三井晚鐘、堅田落雁、瀨田夕照、石山秋月。瀟湘八景中只有瀟湘夜雨、洞庭秋月兩景冠以固定地名,而且這兩處也是很廣的區域,并非限定一個處所,至于其他六景可以適用于任何地方的景色,不拘固定場所皆可套用。然而近江八景的八景皆只限于其所指之地,尤其是瀟湘八景中的江天暮雪描繪的是黃昏江天白雪飄舞的陰慘景象,而比良暮雪卻是山峰積雪的一派明麗景色,兩者的差異是很大的。瀟湘八景是從洞庭一帶尋常可見的景色中去發現景趣,而近江八景則是要在有限的空間去表現特別的景致。把原本極富通融性、流動性的思考方式轉換成受到制約的思考方式。當中國人的情趣變為日本人的情趣時,我們隨處可見這種變化,從藝術自由的角度考慮,這種變化很難令人滿意。(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內藤湖南通過比較瀟湘八景和近江八景的異同,說明了在風景論問題上,島國日本對封閉地方特性的迷戀。而志賀重昂對日本風景的發現,一方面,采取了西方內在的人的“透明之思”的認識論意義上的自然觀,忽視了自然科學認識得以可能的人類實踐活動,便只好通過直觀的類比的方法將事實與價值無媒介性地直接統一;另一方面,這種直觀是采取了東方詩學上的比興手法表達傳統的道德情感,并將這種道德情感寄托在自身所處空間中的特殊自然風物之上,將松柏、櫻花視作日本風景的特征之一,以日本所特有的富士山象征整個日本的國民性。事實上,這正是志賀重昂日本風景之發現過程中的矛盾所在,即帶有普遍性的西方全景透視風景觀與追求東方特殊空間內的風景表現形式之間的鴻溝,是不能僅僅通過傳統直觀的比興手法就能得到統一的,也不能由忽視地域差異的自然科學普遍意義上的擬因果關系直接得到解決,它需要方法論上的進一步完善。而和辻哲郎在《風土》中的現象學方法則是這種努力的一種可能的方向,盡管這種高級現象學方法終歸還是一種即物主義。
和辻哲郎的《風土》
對于和辻哲郎來講,風土并不是從外部對人類施加影響的自然環境。風土的存在方式(風土性),如同時間的存在方式(時間性)構成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人類存在的構造契機一樣,也是構成人類主體性存在方式的構造契機。如此,風土便是主體性人間存在的表現,而不是作為對象的自然。和辻進入這種風土的路徑,并不是那種說明對象與對象之間因果關系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而是解釋主體性人間存在之表現的人間學方法,即解釋學的方法。
和辻以現象學方法對“我們感知寒冷”進行考察。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寒冷就是物理性的客觀的寒氣刺激主觀的感覺器官,主觀將其作為某種心理狀態而經驗。但是按照現象學方法,感知寒冷是一種意向體驗,并不是朝向寒冷而產生一種刺激—反應關聯,而是感知某物時自身既已在關系之中了,而后在這種關系中發現寒冷。人感覺寒冷的時候,其實已經處于了一定的在地的地理空間中的自然與作為間柄的人間的身體性關聯中,即處于了風土之中了。風土不僅在具體的房屋樣式、穿衣方式和料理樣式中呈現出來,還在生產方式,進而在“共同體的形成方式、意識方式、語言方式”中表現出來。因此,對于和辻來講,從衣、食、住,到文藝、美術、宗教、習俗等所有人類生活都是風土現象,而且是風土中人間的自己了解的表現。所以,所謂風土是指在人間與自然進行身體性交涉中,和他者一起在歷史的變遷中創造出來的文化。此際,人間和自然、文化和自然并不是像西洋近代傳統一樣被視作是對立的。對于和辻來講,風土是在并非作為認識對象的身體的延長線上的“活的空間”。
因此,“沒有離開歷史的風土,也沒有離開風土的歷史。” (和辻哲郎:《風土》)和辻通過強調歷史空間的肉身性,一方面將一切歷史存在物作為一種具有自我完結性的有機整體,而不是將其視作是通向黑格爾目的論式的自由精神的暫定的、偶然的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針對那種在國民之間劃分優劣,或把特定國民視作世界精神的意志工具的終極目的的觀點,從而主張平等地尊重每個民族的個性。如此,“國民就不是因其歷史功績,而是在其通過特殊的唯一的方式實現的生命價值上,即作為國民性實現的生命價值意義上成為世界史的對象。”和辻試圖突破時間性歷史的統一趨勢,尋找歷史空間的多樣性存在的可能。
然而,另一方面,和辻還指出,“所謂風土,一言以蔽之,即是地球上各塊土地固有的,而且是唯一的東西,它能夠在經過敏銳的觀察之后被敘述出來,但卻不會讓人得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結論。”因而,作為日本特殊倫理共同體之風土性象征的日本天皇,因為凝聚了島國日本所有匿名形式的國民價值空間,為塑造道德情感上的高度一致性和一體化提供了特殊的“神話敘事”模型,構建了強調日本國民風土特殊性的風景觀,從而與強調普遍性的西方全景透視風景觀形成強烈對比。
這種基于風土空間之特殊性的史觀,在上原敬二(1889—1981)的《日本風景美論》中也有所體現。上原在《美論》中發現了“日常生活中毫不稱奇易被忽略的”匿名的風景,這種鄉國的自然風物與日本人之間形成了同血連脈的同胞關系,由此塑造的風景、環境,歷經長久年月醞釀出“與神同在” “與君同在”“與家同在”的思想特質,從而構成為日本民族的宿命。(上原敬二:《日本風景美論》)
可以說,匿名的風景支撐著并非近代主體性自我的日本民族共同體意識。而且,上原敘述中提及的“歷史” “長年累月” “民族的宿命”似乎賦予《日本風景論》中所欠缺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時間性歷史,而是體現日本風土的空間性歷史。他這樣概述日本的風景史,“我們心里知道,自‘記紀時代’至今的一切自然觀原封不動地采取某種形式打動我們的心境”。這種歷史意識植根于日本的自然風景之中:“在此論述我國國民自古以來的自然觀的變遷的理由并不是單純出于歷史記述的目的,而是為了使人們知道自然的恩惠并保有感謝之心,國民才能繁榮,與此相反,冒犯自然之恩惠的國民很快就會滅亡的天理。”歷史的重要性在于與自然風土的情感一體化。這是超越人間主體活動的“天理”的產物,是環境歷經長久歲月醞釀出來的東西,“是不能習得亦不能教而使知的存在。是扎根于歷代祖先純潔血統中的自然心”。簡言之,歷史的重要性在于日本人天然生存于其中的自然風景。
***
無論是志賀重昂,還是和辻哲郎、上原敬二,都將日本獨特的風景論作為一種國民性理論進行闡釋,這構成了邊留久所批判的“將他者的主體性無意識地置換為自己的主觀性”的對于風土論的致命歪曲。而且,和辻哲郎雖在《風土》中以文化類型學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風土類型論,區分了季風型、沙漠型和牧場型三種風土類型,卻忽視了它們之間的相遇與交往。另外,和辻過分強調了風土的空間性,而遺忘了風土的時間性維度,從而也就難免落入強調自身固有倫理價值特殊性的窠臼,導致“特殊文化價值觀的特權化”。其中始終貫徹了處于西歐普遍性和日本特殊性的矛盾激蕩中強調自身特殊性的日本主體性覺醒。因此,邊留久認為,為了從和辻這種狹隘的思路中抽身,主體性雖應是人間的風土性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毋寧說,構成風土性之存在論構造的具體要素分為文化身體(客觀性)和動物身體(主體性)。身體的兩種不同屬性制造出動態的同一性。由此作為“國民性論”的和辻風土論所具有的思想史意義擴張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相應地,構成風土論核心的“身體性”中,附加了和辻沒有預期到的由技術和象征帶來的“身體性的外化”等領域的課題。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