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電影爆發(fā)之年:成也市場(chǎng),敗也市場(chǎng)

電影《七十七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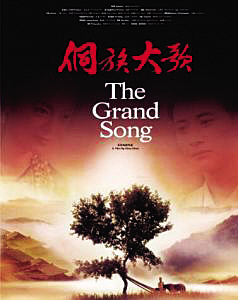
電影《侗族大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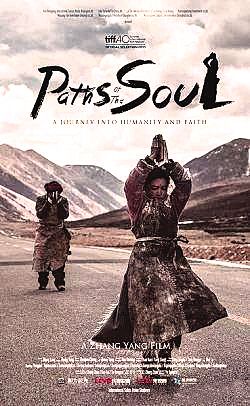
電影《岡仁波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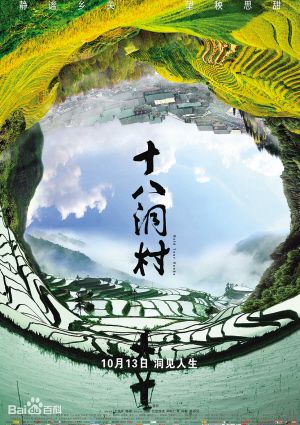
電影《十八洞村》
2017年,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少數(shù)民族電影進(jìn)入到主流商業(yè)院線。現(xiàn)象級(jí)電影《岡仁波齊》的出現(xiàn),極大地鼓舞了民族電影人的士氣。然而,對(duì)于在市場(chǎng)上沉浮的民族電影而言,成也市場(chǎng)、敗也市場(chǎng)。一些民族電影遭遇市場(chǎng)“滑鐵盧”,顯示出市場(chǎng)規(guī)則的冷酷與神秘。
由于在商業(yè)院線頻繁曝光,民族電影迎來了與更廣大觀眾及主流社會(huì)對(duì)話的契機(jī)。民族電影不再是小范圍內(nèi)孤芳自賞的狹小類型,它開始進(jìn)入公眾話題,從而體現(xiàn)出電影作為文化生產(chǎn)的本性。
政策扶持
2017年,“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電影工程”仍舊在延續(xù),年初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進(jìn)行專業(yè)調(diào)研,此前經(jīng)歷過內(nèi)蒙古、東北三省、云南等地的調(diào)研。工程即將進(jìn)入實(shí)踐操作階段。
近年來,國(guó)家財(cái)政對(duì)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的創(chuàng)作一直給予了大力扶持,將其納入農(nóng)村題材影片或重點(diǎn)影片的資助范圍。國(guó)家民委主管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化事業(yè)發(fā)展促進(jìn)會(huì)、國(guó)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影視促進(jìn)會(huì)、文化部主管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化基金會(huì)、文化部與財(cái)政部主管與監(jiān)督的國(guó)家藝術(shù)基金等,對(duì)包括影視在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予以了極大傾斜。
在一些電影節(jié)和電影展上,民族電影的分量也越來越重。上海國(guó)際電影節(jié)連續(xù)幾年都有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進(jìn)入競(jìng)賽單元并獲獎(jiǎng);北京大學(xué)生電影節(jié)連續(xù)幾年設(shè)立了最佳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獎(jiǎng);新近由陜西省西安市政府舉辦的絲路電影節(jié),也有民族題材的創(chuàng)意獎(jiǎng)項(xiàng)。
到2017年,北京國(guó)際電影節(jié)民族電影展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第9個(gè)年頭。在經(jīng)歷過市場(chǎng)化的沖擊和洗禮之后,北京民族電影展的社會(huì)影響似乎出現(xiàn)了邊際效應(yīng):常規(guī)工作越來越定型化,而真正因影展而成長(zhǎng)起來的有影響力的民族電影項(xiàng)目并不多。但對(duì)于那些不能上商業(yè)院線的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而言,北京民族電影展依然提供了一個(gè)展示的平臺(tái)。2017年,該展集中推介了幾部云南民族電影制片廠和天山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如果沒有影展平臺(tái),這些電影很難有機(jī)會(huì)進(jìn)入生產(chǎn)地之外的主流觀眾的視野。從這一角度來說,北京民族電影展的展映環(huán)節(jié)仍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第二屆中國(guó)民族志紀(jì)錄片學(xué)術(shù)展對(duì)于民族志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而言,適逢一個(gè)提倡“文化自覺”的時(shí)代,中國(guó)多民族的厚重文化積淀成為創(chuàng)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這屆民族志紀(jì)錄片展映活動(dòng),讓不同來源、背景與生產(chǎn)方式的民族志紀(jì)錄片齊聚一堂,更是凸顯了民間傳統(tǒng)文化保護(hù)、傳承與傳播的國(guó)家在場(chǎng)。當(dāng)代國(guó)人漸漸有了共識(shí):只有在文化保護(hù)與傳承的基礎(chǔ)上,才能建構(gòu)起更有活力的新文化。
融入市場(chǎng)
2017年是民族電影的爆發(fā)之年,從來沒有如此多的民族電影進(jìn)入到主流商業(yè)院線。業(yè)內(nèi)一直在呼吁民族電影上院線,2015年《狼圖騰》上映之后,曾有一些民族電影大制作項(xiàng)目躍躍欲試,但終于因?yàn)槭袌?chǎng)規(guī)則的叵測(cè)而紛紛“交了學(xué)費(fèi)”。
這一切在2017年終于改觀。《岡仁波齊》打響了民族電影市場(chǎng)闖關(guān)的第一槍。上映前,各方預(yù)測(cè)票房至多500萬。不料,在好萊塢大片、國(guó)內(nèi)明星電影的夾擊中,《岡仁波齊》竟脫穎而出,票房上億,這個(gè)結(jié)果讓出品方、發(fā)行方甚至導(dǎo)演自己都很意外。《岡仁波齊》無疑拓寬了文藝片,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題材文藝片的市場(chǎng)疆界。
《岡仁波齊》成為了2017年現(xiàn)象級(jí)的電影,少數(shù)民族電影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關(guān)注,成了公眾熱議的話題。獲得了罕見的市場(chǎng)好成績(jī)后,制作方與發(fā)行方頗為躊躇滿志,對(duì)同期套拍的另一部藏族題材電影《皮繩上的魂》有了更高的市場(chǎng)期待。但世事難料,《皮繩上的魂》放映幾天下來,票房慘淡,不得不提前下線。
從《岡仁波齊》到《皮繩上的魂》,對(duì)于導(dǎo)演來說,可謂成也市場(chǎng),敗也市場(chǎng)。前后兩部電影的發(fā)行成績(jī)可能令他們迷茫。那些自以為通曉行業(yè)規(guī)則的業(yè)內(nèi)精英,經(jīng)常被市場(chǎng)邏輯打得措手不及。這兩部同一導(dǎo)演的作品遭遇如此懸殊,說明民族電影人還遠(yuǎn)未掌握市場(chǎng)規(guī)則。
已經(jīng)問世幾年的電影《侗族大歌》,終于在2017年上了院線公映,卻沒有獲得市場(chǎng)的肯定。“非遺”主題類民族電影一直是民族電影的代表,在公映之前,該片獲得了很多專業(yè)人士的好評(píng),但最終沒有擺脫“叫好不叫座”的魔咒。而另一部并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民族電影”《七十七天》,票房竟然也上億,似乎又打開了民族電影的好運(yùn)口令。
市場(chǎng)展現(xiàn)了迷人的魅力。2017年如此多電影在市場(chǎng)試水,本身就是電影市場(chǎng)繁榮的結(jié)果。隨著影院及其銀幕數(shù)量的增加,電影市場(chǎng)的體量擴(kuò)大,市場(chǎng)一方面需要能帶來相對(duì)穩(wěn)定收益預(yù)期的類型電影,另一方面也需要那些具有市場(chǎng)異質(zhì)性的文藝片,以開掘市場(chǎng)獲利的空間。
另一部電影《清水里的刀子》借助藝術(shù)院線聯(lián)盟,也獲得了面對(duì)觀眾的機(jī)會(huì)。這是中國(guó)電影市場(chǎng)成熟的另一面。在主流院線之外設(shè)立藝術(shù)院線,成為許多民族題材文藝片的“生路”。其實(shí),文藝片也有自身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藝術(shù)院線聯(lián)盟可被視為針對(duì)文藝片的另一種分眾市場(chǎng),目前還很微弱,但隨著中國(guó)電影市場(chǎng)的進(jìn)一步擴(kuò)展,藝術(shù)院線必將成為相關(guān)制作者與愛好者重要的行業(yè)依托。
2017年末,蒙古族導(dǎo)演哈斯朝魯?shù)氖袌?chǎng)化大片《戰(zhàn)神紀(jì)》讓人們翹首以盼,不料,這部耗資相當(dāng)大的民族電影卻悄然撤檔。這似乎又一次顯示出市場(chǎng)規(guī)則的冷酷與神秘。
文化重構(gòu)
由于在商業(yè)院線頻繁曝光,民族電影迎來了與更廣大觀眾及與主流社會(huì)對(duì)話的契機(jī)。
新世紀(jì)以來,民族電影獨(dú)樹一幟,成為學(xué)術(shù)界研究的課題。但相關(guān)的理論生產(chǎn)一直推崇一種關(guān)于民族電影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小成本、多元文化主義價(jià)值導(dǎo)向、文化保護(hù)與傳承主題、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二元結(jié)構(gòu)等。然而,筆者以為,民族電影主題和題材范圍可以更廣。現(xiàn)有的電影故事中,地域與人物常常從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抽離,復(fù)雜的社會(huì)聯(lián)系被簡(jiǎn)單化,角色僅僅生活在民族文化的模型中難以自拔。對(duì)此,我們需要反思,民族電影不僅關(guān)乎少數(shù)民族文化非遺主題,也應(yīng)當(dāng)有復(fù)雜的文化構(gòu)成,它可以是主旋律,也可以表現(xiàn)各種現(xiàn)代社會(huì)問題,總之,可以具有和主流電影一樣的復(fù)雜性和多樣性。
由于商業(yè)院線的參數(shù)加入,民族電影中受推崇的“母語電影”的文化價(jià)值也需要從另一個(gè)角度考察。目前中國(guó)電影依托的是商業(yè)電影體系,在國(guó)家主流院線里,母語電影的存在領(lǐng)地并不宜擴(kuò)大。在進(jìn)入商業(yè)電影院線之前,母語電影在彰顯少數(shù)民族文化價(jià)值方面成效顯著;但在主流院線里,它也意味著主流觀眾在文化理解方面的障礙,從而使少數(shù)民族文化失去了更大范圍傳播的機(jī)會(huì)。而純粹的母語電影所展示與描繪的“單一民族”生活,在國(guó)家電影的價(jià)值體系中,可能并不利于建構(gòu)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因此,一方面國(guó)家要加大建設(shè)藝術(shù)院線聯(lián)盟以容納在文化表述上有抱負(fù)的“母語電影”,另一方面電影主創(chuàng)也要清醒地意識(shí)到母語電影在主流院線中的各種局限,并愿意承擔(dān)由此帶來的市場(chǎng)風(fēng)險(xiǎn)。
另一部表現(xiàn)湘西苗族村寨“精準(zhǔn)扶貧”的電影《十八洞村》,在2017年的市場(chǎng)中獲得了政府罕見的扶持力度,最終票房過億。但這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業(yè)票房,這也讓我們看到了當(dāng)下中國(guó)電影 “政策市”的一面。“精準(zhǔn)扶貧”政策對(duì)于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和基層黨組織建設(shè)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和宣傳作用。這部電影的市場(chǎng)表現(xiàn)令我們正視民族電影在社會(huì)教育和社會(huì)引導(dǎo)方面可能擁有的巨大作用。國(guó)家開始用公益化的方式在商業(yè)院線內(nèi)進(jìn)行嵌入式扶持,但如何嵌入而不違背商業(yè)電影體系、如何進(jìn)行評(píng)估以保障公平,仍舊需要更精微的制度設(shè)計(jì),考驗(yàn)著相關(guān)部門的責(zé)任心和智慧。總之,我們也要在新的時(shí)代重新考察民族電影的社會(huì)功能,并開啟新的制度建設(shè)。
《老獸》在2017年末放映,呈現(xiàn)了內(nèi)蒙古當(dāng)代城市的世道人心。這部電影揭示出,民族電影在主題與題材選擇方面具備某種“全民性”,就可以獲得更多觀眾的共鳴。許多民族電影市場(chǎng)不利,不僅與豐富的社會(huì)性內(nèi)容缺失有關(guān),更與“全民性”主題缺失有關(guān)。如果只執(zhí)著于一族一地的關(guān)切,耽于封閉的想象,沒有和當(dāng)下社會(huì)豐富多彩且不乏沖突的社會(huì)意識(shí)相呼應(yīng),自然不會(huì)贏得主流觀眾的認(rèn)同。這是電影《老獸》帶給我們的文化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