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力:他在“貧窮”中死去 ——聞概念藝術家庫奈里斯逝世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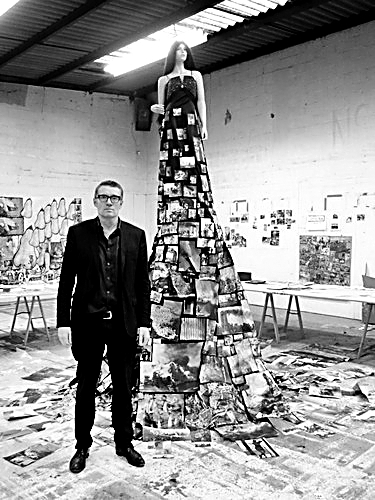
雅尼斯·庫奈里斯與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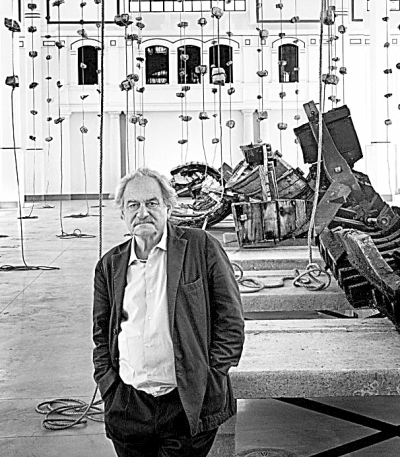
雅尼斯·庫奈里斯與作品
雅尼斯·庫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于2月16日在羅馬去世。他是一位以“貧窮”著稱于世的稀有藝術家。所謂“貧窮”,并非說他身世貧困,是指他終生信奉“清貧”的藝術概念,至死不渝。法國《世界報》載文稱:他的辭世使得“貧窮藝術失去了它最忠誠的捍衛者”。
筆者自幼喜愛繪畫,但對“概念藝術”流派卻不敢恭維。數度去瀏覽巴黎香榭麗舍,或盧森堡公園舉辦的概念藝術展,感覺是乏善可陳,比觀賞一年一度的大宮殿“國際現代藝術展覽”還更讓人掃興,喚起對薩爾瓦多·達利褻瀆達·芬奇繪畫的反感。或許,這是因為自己真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了。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庫奈里斯是一位可敬的藝術探索者,尤其是他給人啟迪的“清貧”哲理概念,引人深思當代造型藝術和空間藝術日益商業化的頹勢。
雅尼斯·庫奈里斯1936年生于希臘比雷埃夫,20歲進入羅馬美術學院,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熏陶,不久擺脫非形象藝術,代之以幾何圖形為象征的新穎創意。庫奈里斯獨辟蹊徑,從馬塞爾·杜尚的創作中汲取“概念”,沖出物質的樊籠,來展示主體內在的靈動,以無形超越有形。從20世紀60年代,他卷入了在意大利開始流行的概念藝術潮流,聲稱:“我找到什么,就用來創作,像一個老式畫家,來時兩手空空。”他采用日常碰見的自然元素創作出藝術形象,譬如玻璃、石塊、樹枝、毛織品、鐵皮及其他金屬薄板,長刀和木匠釘子等等,以此表達藝術與生活的思維,用材樸素無華,成本遠比大理石和青銅低廉。繼1967年將活鳥裝置進自己的作品后,庫奈里斯于1969年再出驚人之舉,把法比奧·薩勒基迪尼的阿蒂科畫廊改成馬廄,拴入12匹活馬,以表現人類奴役大自然。爾后,他又用活鯊魚、飛鴿和松鼠等動物當展品,讓觀眾看到的絕非“皇帝的新衣”,而是實實在在的自然生態,由此催生藝術沖動。
由于其創意不同凡響,越出了席勒唯人類藝術觀雷池,他數度應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和加卡塞爾文獻展,以及熱那亞、巴塞羅那藝術展,開始有了一定的國際影響,作品也陸續由歐美大都會、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烏拉圭等十余國重要的博物館,尤其是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收藏。2016年3月,位于巴黎新橋附近的法國鑄幣局舉辦了雅尼斯·庫奈里斯作品展覽。展品中有一籠子活老鼠和兩尾在水中繞尖刀游動的金魚。地上堆放著一些破麻袋,墻頭掛著一塊鐵板,板前點燃一支蠟燭,板上用粉筆寫著斜體大字:“不自由,毋寧死!馬拉萬歲!羅伯斯庇爾萬歲!”由此可見,這位概念藝術家受了卡拉瓦喬和德拉克洛瓦繪畫理念的沖擊,一改早期的“無題”為“有題”,尋求一種藝術道德,坦露出作者的思想意識。
“貧窮藝術”一詞本出自意大利文藝評論家杰爾瑪諾·切蘭之口。切蘭則是從波蘭戲劇導演耶日·格羅托夫斯基所稱道的“貧窮戲劇”得到啟示,為概念藝術這一獨特流派定出這個名目。“貧窮藝術”立意奇特,謀求藝術擺脫物質,以觀念取代實物,屬于概念藝術范疇。它的思維模式注入了不少思辨因素,使一些傳統價值觀發生變化,引出了諸多時髦的文化語匯,如“概念美術”“概念音樂”“概念舞蹈”等等,一時琳瑯滿目,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歐美各國流行起來。在西方,人們常提到的“貧窮藝術家”里,有馬里奧·麥茲、朱塞佩·波諾納、盧齊亞諾·法布羅、米開朗基羅·波斯托萊多、朱里奧·包利尼。雅尼斯·庫奈里斯似乎是這一藝術流派的代表人物。
庫奈里斯的“貧窮藝術”,與同屬“概念藝術”的“行為藝術”,或稱“行動藝術”不同。“行為藝術”源于法國,代表作是伊夫·克萊因的《自由落體》,偏重于自由展示行為過程,難免導致藝術泛化,在一些受眾眼里,“行動藝術”被視為“非藝術”,而西方的“肢體藝術”往往喪失“行為準則”,與東方傳統倫理價值相悖。與之相較,“貧窮藝術”似乎無此頹唐之虞。庫奈里斯強調天賦的生命力,總以自然為本,視之為藝術之源。作為“貧窮藝術”的至誠信奉者,他不尚浮華,著眼于人類生活的“簡樸”,崇尚言簡意賅的表達原則,故與時髦的“波普藝術”形成鮮明對照。法新社在2月16日報道庫奈里斯逝世的消息時,特別提到:“雅尼斯·庫奈里斯被公認為‘貧窮藝術’的創始人之一。這個意大利藝術思潮不滿20世紀末60年代稱霸的美國文化,尤其質疑波普藝術。”法國《世界報》也于同日發表記者菲利普·達讓的署名文章,指出雅尼斯·庫奈里斯作品的主旨是“追求視覺的清貧”。這正應和了我國經典《國語》中的古訓:“驕泰奢侈,貪欲無藝。”
這里闡明了一個看來淺顯,實則深刻的藝術哲理。俄國文藝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在1858年已論述過“藝術與現實的美學關系”。他越出人本主義的范圍,肯定“美就是觀念在事物上的顯現”。從這一角度來審視雅尼斯·庫奈里斯的“貧窮藝術”,再將之與“波普藝術”前衛明星安迪·沃霍爾進行一番比較,就能明顯感覺二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靠《瑪麗蓮·夢露》《可樂樽》《布利洛肥皂盒》雕塑和《金寶罐頭湯》系列等時髦廣告畫一躍成為美國流行藝術寵兒的安迪·沃霍爾,顯然是跟應市創意和商業炒作的大眾文化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商業化的超消費文化一時炫目,但畢竟會變成過眼煙云。沃霍爾自己也并不贊同名人崇拜,坦率承認“我不認為自己的藝術有恒久的價值”。他這番話預示著,迎合世俗審美趣味的波普藝術商業效益雖顯著,但文化商品化意味著單調和虛無,終將要走下坡路。
雅尼斯·庫奈里斯生前曾到過中國,用兩年時間考察中國的社會文化,于2011年底在北京一家美術館舉辦了《演繹中國》展覽。他把中國的古老瓷片、瓷碗等拼成不同圖案,當作語言概念,暗喻歷史,來呈示自己的“貧窮藝術”,不失為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一種與東方“他者”進行的跨文化對話。一位西方的概念藝術家在遙遠的、重形象藝術的中國留下足跡,是一件不多見、值得稱道的幸事。如今他已歸西,要看故人給當今世界遺傳下什么。恰于此時,筆者看到《費加羅報》雜志婦女版對“貧窮藝術”新秀、瑞士人托瑪·伊赫索恩的介紹。他的畫坊裝置在巴黎衛星城奧伯維利耶,正展示著用透明膠帶將一沓沓彩紙粘貼成的一對女模特,雙姝窈窕,身材修長,一似長頸鹿,觀眾得仰首方可一睹芳容。面對伊赫索恩如此曼妙的兩淑女作品,筆者悠然遐想:庫奈里斯宗師不復在世,但斯翁一生不改初衷,堅持探索的“貧窮藝術”已經成為一種異類美學,自有承繼的后來人。
(作者:沈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