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徐風:生活在顧景舟的世界里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11月27日10:36 來源:中華讀書報 舒晉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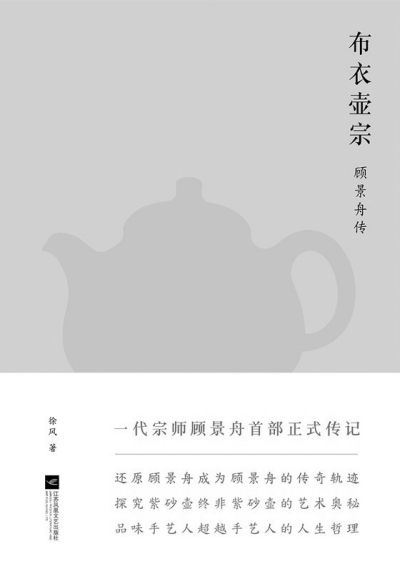 《布衣壺宗——顧景舟傳》,徐風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2015年出版,58.00元
《布衣壺宗——顧景舟傳》,徐風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2015年出版,58.00元我把顧景舟的離去,看作是中國手工藝界的最后一位士大夫的謝幕,是一個時代手藝的終結。
一個作家寫什么,作品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背后的風景。對于徐風而言,紫砂是他背后最大的風景。他生長在宜興,很早就熟悉紫砂,對它的材質、工藝、傳承等等比較了解,尤其喜歡紫砂的古樸內斂、溫潤大氣,在紫砂界結交了許多朋友,壺,風習,藝人,江湖故事,常常帶給他充沛的靈感和創作激情。經過這么多年與紫砂的耳鬢廝磨,徐風的感悟越來越多。他認為,紫砂壺集雕塑、詩文、書畫、篆刻等于一體,是地道的“中國表情”,同時又保留了一份來自民間的生動與率真,且壺中又留下寫不完的故事,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探究與表現。
在《布衣壺宗——顧景舟傳》中,徐風用了近兩年時間采訪70多人,顧景舟的形象在他的心里逐漸清晰,他甚至覺得自己仿佛生活在顧景舟的世界里,捕捉他生命的肌理,甚至他的呼吸、心跳、氣場,然后把這些轉換為文字。“我要貼著他的呼吸、心跳寫。到后來,我真的把顧景舟當成了自己的一位長輩。我經常在睡夢里見到他,這在之前的寫作生涯里,是從來沒有過的。”徐風說。
讀書報:《顧景舟傳》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感覺您像是進入了傳主的內心世界,和傳主有一種精神的交流。
徐風:關于傳記寫作,王彬彬教授曾經引用過一位外國作家的話:傳記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鑒賞。簡言之,傳記寫作的過程,就是鑒賞一個生命、透視一個生命的過程。為什么我要寫顧景舟?從精神的維度上講,無論是文化品位、人格風范、壺藝水平,他都是中國紫砂界的喜馬拉雅山。而且,我把他的離去,看作是中國手工藝界的最后一位士大夫的謝幕,是一個時代手藝的終結。當然這個認識的過程也是逐步的,顧景舟離去已經20年,他身后的紫砂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自己的一把壺,價格炒到2000多萬。而他一直到臨終前,仍然是個布衣藝人。他的性格內向,平時很寡言;一般不肯接受媒體采訪。寫這樣一個老人,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讀書報:《顧景舟傳》為讀者傳遞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閱讀的過程感覺漸入佳境。采寫一個已經去世的傳主,您覺得最難把握的是什么?
徐風:最難的是寫出顧景舟的精神史。寫出這位一代壺藝宗師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精神狀態,突出他“風骨”層面上的東西。作家的手里只有文字,但一定要寫出傳主特定的氣場與肌理。顧景舟留下的傳世作品,線條冷峻、骨格清奇,構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基調。壺的背后是人,壺的氣息實際上是人的氣息的延伸。和那些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比,他一生并沒有太多的大起大落,坊間的傳說里,他是一個清高寡言的人。傳記作品最大的難度,就是如何把從各處搜集的資料打碎、糅合,然后設計一種貼合傳主氣質的語言進行書寫。這可能是決定一本傳記作品成敗的關鍵要素之一。
還有一個,就是要把傳主放到當年的歷史現場去觀照。這個“歷史現場”也是要靠文字去修復、重現的。同時,既然這是一部為手藝人立傳的作品,書中寫到了諸多顧氏經典作品,那么我想,最關鍵的,是要寫出傳統手工藝的那種迷人的手感。
讀書報:在這部書的寫作中,和寫其他的紫砂藝術大師,有何不同的感受?
徐風:首先他是一個終身孜孜不倦的文人,甚至他是一個精神上有潔癖的文士。然而他又是一位一絲不茍的工匠。身懷超出一般工匠的獨絕工藝。這種文人與工匠的完美融合,在中國紫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我覺得他身上最可貴的是:文人的錚錚風骨,藝人的工匠精神。這種融合的品格在當下尤其寶貴。因為文藝界太浮躁,很多人靜不下心來,克隆抄襲、偷梁換柱,學藝三個月就想著辦個展,還未滿師作品就想進博物館。我從顧景舟一生的人格修為和壺藝成就的脈絡中,梳理出一條走向:即是從“知行合一”到“天人合一”,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是一種高境,而知行合一是邁向前者的途徑。顧景舟一生有無數細節,有力而飽滿地支撐著這八個字。這也是我寫該書的一點收獲。
讀書報:藝術家多是有個性的,不知道寫這樣的一位紫砂大師,您是否也有為尊者諱的顧慮?
徐風:其實,書中顧景舟還有一次發火的情景,“文革”初期的一個黃梅天,他妻子把他藏在床下的一捆舊書畫拿到院子里晾曬,被他大罵了一頓。事后他向妻子道歉:我不該向你發這么大的火,可是這些書畫,也就是我的一點愛好和念想了,都是友人的東西,見物如見人。那時“文革”破四舊之風已盛,顧景舟的發火,其實也是對時政的抗爭。這個世界無論誰,性格都會有局限。有些細節,在書中表現得比較含蓄;還有的情節,在沒有征得家人、徒弟同意的情況下,書中就沒有展開。在取得第一手資料的過程中,也有人和我講到顧景舟與某些人的恩怨,但不能寫。筆墨也是可以殺人的,我確實在采訪顧景舟的生平過程中,發現了他和少數人的一些恩怨和難以啟齒的細節。這些細節對顧景舟或許沒有傷害,但是對和他交往的人是有傷害的,那些人還在,甚至名聲隆隆。不能寫的情節,至少有幾萬字。這是我的無奈。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