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北戴河尋訪鄧友梅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01月27日09:08 來源:北京晚報 蘇北 本文作者與鄧友梅合影
本文作者與鄧友梅合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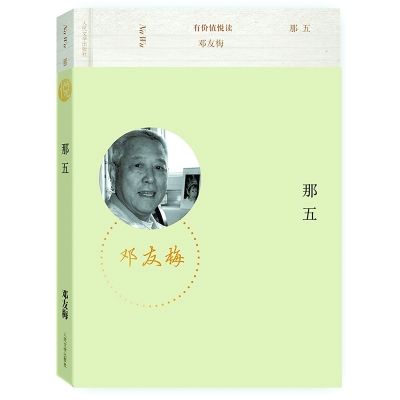
一
鄧友梅先生將他的虎皮鸚鵡帶到北戴河創作中心,每天把鸚鵡掛在院子里的一棵茂密的核桃樹上。正是夏日,核桃樹綠蔭披紛,結果無數,以至于枝條弋地。
我和鄧先生聊天的窗子正對著那棵大樹。透過窗子可看到掛在樹枝上的鳥籠。談話就從鳥兒開始吧。
“這是只什么鳥?”
“虎皮鸚鵡。”鄧先生笑:“放在家里沒有人照管,我只得把它帶過來養。”
“每天都掛到外面?”
“晚上,或者下雨天收回來。被雨淋了,易生病。”
“我知道鳥也會感冒的。”
“是的。著涼了,就會生病。”
二
我手頭有一本《那五》。在訪問前,我先把《那五》這本小說集里的《尋找“畫兒韓”》、《那五》和《煙壺》等小說,通讀了一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這些小說剛發表時,也讀過。可那時年輕,所寫生活又離我們較遠,因此不易記住。
我選擇中心一側的小花園高大柏樹下的雕花鐵椅上去讀。午休時分,那里十分安靜。花園里有十余株柏樹,已十分茂盛。碎石地面十分潔凈。
極喜歡這座小花園。剛來的時候,我就相中了這座花園。心中盤算:在未來的十天里,我會每天下午坐在那里,靜靜地獨坐,并趣說,“是我家的客廳。”我有時整整坐一個下午,讀書,讀《那五》,眼睛酸了,就抬頭聽蟬鳴,聽風聲,聽水聲(有一個小小的流動的水源);看花,不遠處一荷池,極小,有荷幾枝,開花幾朵。
下午三點多鐘,小花園里的柏樹漏下斑駁的陽光。陽光是強烈的,而樹的陰影下,是陰涼的。我坐在鏤空的白色鐵椅上,頭頂上蟬鳴如嘶。一只近處的老蟬,長鳴聒噪;稍遠的一只,則短促吟唱。整個花園,空無一人,只一女清潔工在擦拭著一切:石凳、木椅、燈柱及地上起裝飾作用的彩石……院門外,不時有汽車駛過。花臺上的美人蕉和太陽花,開出濃烈的彩色。我坐在花園中,享受這午后的一個人的寂靜。
頭頂上的蟬又嘶鳴了。夏日的一切的昆蟲進行著它們的吟唱。
我讀著《尋找“畫兒韓”》,再次重讀的感覺依然飽滿有趣。甘子千、畫兒韓,以及盛世元幾個人物都極其鮮明生動。特別是關于假畫賣、燒、贖,一波三折,妙趣橫生。實在是一篇讓人叫絕的短篇小說,堪稱短篇之典范,也是京味小說之代表作品。說到京味小說,我對鄧先生說,評論界一般認為,新時期鄧友梅、林斤瀾、汪曾祺為代表作家。其實,嚴格地說,您才是正宗的京派。汪出生于江蘇高郵,寫的生活多以高郵為主,語言也不是北方方言,而林呢,溫州味也重,雖然汪、林也寫了不少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而您,出生在天津,十幾歲就到北京來混,筆下是北京味最重的作家。
鄧先生認真聽著。對這個觀點,我自認為他基本認可的。
三
決定訪鄧先生,純屬偶然。
到北戴河,才知道鄧先生也在此。因有寫《汪曾祺傳略》的計劃,鄧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初的幾年,一直與汪在北京市文聯同事交往甚多。之前林斤瀾等沒有訪問,已成遺憾。
午后我見到鄧先生,先送給他一本《憶·讀汪曾祺》,在他的小客廳里坐了一會兒,說,想寫《汪曾祺傳略》,有時間請先生談談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與汪的交往,及“文革”中汪從張家口回來的情況。鄧先生說,可以,只是年紀大了,許多事情記不清楚,不知我想了解些什么?我說,到時候我列個提綱吧。
晚飯后,我坐到核桃樹下。過了一會兒,鄧先生從外面散步回來,也坐到樹下的鐵椅子上休息。又有人圍過來合影,先生盡力配合著。之后先生說,一個下午都在看我送給他的書。我想,是汪曾祺這個老朋友在吸引著他。他對我說,要是訪問,上午十點鐘之后,下午三點鐘以后,去時先打個電話更好。他又說,年紀大了,許多事不記得了,不知道具體要談什么?我說,我會擬個提綱的。又有人過來合影。過了一會兒,鄧先生起身走了,說,我回去了,馬上來人又要照,我受不了。我知道,年紀大了,相機一照,閃光燈一閃,眼睛受不了。
鄧先生拄著拐杖,一步一步上臺階,回房間了。
四
“您在書中寫道,醬豆腐肉,這是一種什么做法?”
“用臭豆腐的鹵子,燉肉。”
“放臭豆腐鹵嗎?”
“也說不好,可能要放一點。不會太多,至多半塊吧。”
“什么樣的肉?五花?肋條?”
“這得是五花肉。肥瘦都得有。”
鄧先生在《再說汪曾祺》中寫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次他從東單過,順道去住在三條的汪曾祺家坐坐,進門一股醬豆腐味。原來汪曾祺在做醬豆腐肉。汪說:“按說晚上坐上沙鍋燉最好,可夜里怕煤氣中毒,改白天做試試。”鄧友梅后來問過一位高人,過去王府做此道菜,是有講究的,一般都是二更天開燉,沙鍋邊還要糊上毛邊紙,鍋下點著王八燈,要第二天中午才能開鍋。而汪曾祺住在大雜院里,一家只住兩間小房子,沒事整這種高雅的玩意兒,也可見其可愛、可笑。之后有一次,我見到汪朗,說起這個事。汪朗也是個吃貨,他告訴我說,做醬豆腐肉,根本不用放臭豆腐鹵的,只用豆腐鹵的一點點汁即可。
聊到當年劃右派的事,鄧先生自己興趣先上來了。他說,反右之初,一天恰巧遇見王蒙,王蒙特地下了自行車,把我拉到路邊,小聲對我說:“你最近講話要注意,風聲緊。你跟我不一樣,我比較謹慎,你喜歡亂說。現在反右了,我提醒你,你要注意一點。”沒想到沒過半個月,王蒙自己倒先被揪了出來。
之前不久,中宣部召開過一個青年作家座談會,找幾位有點影響的青年作家座談。散會后,幾個青年人聚在一起,包括王蒙、林斤瀾等,劉紹棠說,我們這些人不會有事的,我們都是先進分子。結果不久,劉便被打成了右派。而在北京市團委禮堂召開的揭批劉紹棠大會上,鄧友梅上臺發言,他說劉紹棠搞特殊化,下鄉還自己帶白面饃,不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下面群眾熱烈鼓掌,認為他講得有血有肉。他在臺上正得意呢,這時主持人接過話筒說了:“下面不要鼓掌。鄧友梅也是右派分子。”
鄧友梅對我說,這時他在臺上,完全蒙了,因為一點精神準備也沒有。臺下忽然又是一片亂糟糟的人聲,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就在臺上也不用下去了,接著開始接受別人的揭批。
鄧先生說完,他咧著嘴,就這么坐在沙發上。表情是笑的模樣,短短的白茬分布在上嘴唇上。我們都沒有接話。我知道,那些年,對他這一代傷害是慘重的。他的心中有痛。
這些,其實我已在他的散文集《八十而立》中讀過,現在由他親口說來,雖已當成陳年舊事的笑談去說,可仍是十分無奈。
五
核桃樹下的雕花鐵藝的桌椅,經常坐滿了人,作家們飯后聚在一起聊天,高談闊論。大樹下面好乘陰涼。這真是一棵大樹,覆下的陰涼近小半個球場。是個名副其實的“作家的沙龍”。
有時我們聊著,見鄧先生窗口的燈亮著。房間有人影晃動,鄧先生正在工作;有時他也走近窗口看看。晚上九點多,鄧先生出來拿鳥,我給他取下,遞給他,我說:“我們在外面說話,吵了你吧?”他說:“不吵,愿意聽你們說話。”早晨,鄧先生出來掛鳥,我正散步,接過鄧先生的鳥籠子,給他掛上。鄧先生嘴上一溜小胡子,花白,他說:
“在北京,我把它放出來,隨它飛。它的一個伙伴,飛出去,回不來了。”
我說:“它的小腦袋還挺聰明。”
鄧先生說:“是的。”說著用手伸過去,給鳥去啄,鳥并沒有過來。鄧先生轉身走了。我也試著把手伸過去,小鳥轉來,伸出小嘴啄我的指心,有點癢癢的,還挺舒服的。
六
那天晚飯后,鄧先生從餐廳出來。一個湖南的作家問他:“還寫什么嗎?”
鄧先生擺擺手:“寫賬還寫錯。”他邊走邊擺手:“除了寫賬,別的不寫。”他笑著說。
過一會兒,他又說:“賬,還總是寫錯呢!”
我想,這是鄧先生的托詞。寫什么,一句話說得清么?又有必要說么?所以,別人問,干脆說什么也不寫。
雖已是83歲高齡,鄧先生肯定不會放下他手中的筆。一個作家,他只要拿起筆,就不會再放下了。這是一個寫作者的宿命。
也是有一天,在小花園,一個作家問他為什么選擇寫作?
他說,那時年輕,自己又沒別的本事。一個人活著,總得有點意義,為國家、社會做點事。自己的工作又在文化單位,就估摸著寫點先進人物,這樣就慢慢走上了寫作的道路了。
我想,鄧先生是會有自己的計劃的。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