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格非VS安意如:聊將“錦瑟”記流年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4月02日10:58 來源:文學報 傅小平 安意如
安意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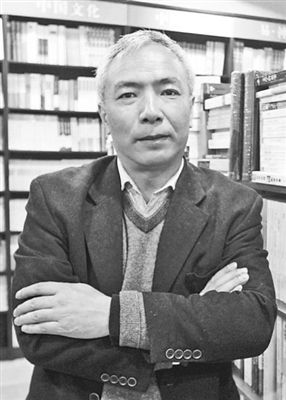 格非
格非 純粹是出于巧合,近期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先鋒作家格非的自選集《相遇》里,收入了他一篇早期的小說《錦瑟》,而古詩詞鑒賞作家安意如推出的清代詩人黃仲則的詩傳,題為“聊將錦瑟記流年”。于是,在堪與納蘭容若比肩的這位被遺忘的傳奇詩人的詩句里,兩位似乎八竿子打不著的作家,有了不期而然的“相遇”。
或許不只是巧合,格非的小說脫胎于唐代詩人李商隱的《錦瑟》,而有了李商隱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才有了黃仲則《感舊》里的這句詩,才有了安意如的詩意描繪。一如安意如新書的內封上,以李商隱詩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勾畫出來的《荷塘圖》,亦象征了黃仲則人生華美之后出淤泥而不染的枯敗與荒蕪。其間的隱秘關聯或許是,黃仲則在并非詩歌的年代里,寫下了美好的詩作,雖然他終究沒能如李白、杜甫,乃至納蘭容若那樣為后世敬仰。同樣格非、安意如,在并非文學的黃金時代里,依然書寫著自己的“文學”。
在安意如的理解里,黃仲則的價值在于他的悲苦,是大多數人的悲苦,是說不出口的悲苦,是那種時代循環里所謂“庸常”的悲苦,他甘于庸常就罷了,偏偏他不甘于,他有才華,他要掙扎。“就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寒士想要力爭上游,但時代的瓶頸越縮越緊,如果你不是有過人的運氣,你很難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位置或是高度。”正因為此,安意如以為,黃仲則更有在當下被書寫的必要。“他詩中的慷慨悲歌,不僅是當時落寞才子感同身受,現在像我們一樣被生活、被社會被很多東西壓抑的人也會感同身受。”
黃仲則出身寒微,際遇不佳又一生潦倒。雖然他與乾隆年間的大學士朱筠、袁枚等皆為好友,與嘉慶年間的名臣洪亮吉也有著生死之誼,但他一肚子臭脾氣,完全不懂得人情世故,即使這些知名人士對他欣賞有加,卻未必能長久相處。雖然他在9歲的時候,就被當時去江蘇巡視的學正大人相中,料定必成大器。他也果真16歲就成了秀才,且在三千子弟學員當中名列第一,但從19歲開始,一路考到35歲,他都沒有中舉,更別說當官了。如是,正如安意如所說,一如既往的窮困潦倒,文人的不事生產,才華和現實的脫節,在黃仲則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像一面鏡子,既表現出和過往、以后詩人不同的玄秘連接,又呈現了‘士’這個階層,這個特殊群體有才無運的命運共同性。”
雖然黃仲則35歲就英年早逝,但他的詩才在他的時代里,也算得名重一時。他短暫的一生留下了兩千多首詩,其中如“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等詩句,至今為人傳誦。而從清乾隆年間直至民國,黃仲則詩作在文人、知識分子中間影響頗大,蘇曼殊、郁達夫、瞿秋白、金岳霖、柔石、郭沫若等人,都對其推崇備至。但說到對大眾讀者的影響,黃仲則是典型的“詩紅人不紅”。在果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裁瞿洪斌看來,某種意義上,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套路,造成了這種悖謬的現象。“最近幾十年,但凡是研究文學,總是先推測其時代背景、歷史潮流,他的家庭、情感經歷,然后才是他為什么在那樣的年代里寫出那樣的作品。這樣的研究,或許適合李白、杜甫。對于黃仲則這樣一位與時代有著明顯的錯位,沒有復雜的人生經歷,靠心靈寫作的詩人,卻是完全錯誤的研究思路。而黃仲則就這樣被文學研究者低估了。”
當然,作為清華大學教授的格非,其境況非唯有入仕一途方能自證價值的時代里的黃仲則可比,但在評論家陳曉明看來,雖說格非的實力絕不在同為“先鋒派三駕馬車”的余華、蘇童之下,但他的重要影響卻是被低估了。“格非是唯一生活于先鋒派的童話世界里的作家,他的寫作超越了現實。”陳曉明表示,格非的小說還保持著探究歷史的愿望,他把破敗的歷史時刻寫得異常鮮明。“他始終堅持按自己的意愿和風格寫小說,這在今天尤為難能可貴。”
事實上,在寫小說的道路上,作為“專業學者”同時又是“業余作家”的格非有過自己的彷徨。上世紀90年代,格非曾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暫停了自己的寫作。“90年代末期時,我的精神狀況遇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我在某種場合說過想暫停寫作,因為一個作家當你拿起筆來寫的時候,你必須要有非常充沛的感情,而不能硬寫。那時對我來說,我找不到任何寫作的想法。以至于很多人給我打電話問:‘你就這么完了嗎?’”當然格非沒有“完”,他于2004年推出了長篇小說《人面桃花》。“開始我就設想把它寫成‘三部曲’,想用地方志的結構,后來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我寫作的變化跟社會變革有關,我在調整自己跟社會的關系,在被打了‘一棍子’以后重新思考。”
格非的“重新思考”,也包含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致敬。事實上,正是重讀《金瓶梅》,使得他最終決定另起爐灶寫《人面桃花》。“我讀過各個版本,唯獨沒讀過引進版,之前偶然發現這本書,覺得《金瓶梅》真的是中國古典小說里面最好的一部。它的簡單、有力讓我極度震驚。之后,我覺得完全可以通過簡單來寫復雜,通過清晰描述混亂,通過寫實達到寓言的高度。”
然而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我國古典文學傳統,顯然還沒被國人普遍認識到。格非說,幾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國南部一個小村莊,專心寫作《人面桃花》。那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小村莊,但令他驚訝的是,那里的農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國家的文化,絕大多數農民對福樓拜、普魯斯特等本土小說家的經典文學作品格外熟稔,津津樂道。格非坦言自己特別羨慕這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五四’時主張向西方文化看齊,影響至今,‘西方中心論’的思想仍在許多小說家的頭腦中作祟,他們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
安意如想必于此心有戚戚。在3月22日上海松江新城鐘書閣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她坦言自己欣賞好的現代詩作者,也喜歡讀北島、顧城、海子的詩,但她不會像讀古詩詞一樣,去賞析這些詩歌。在她看來,現代詩無非是散文的一種寫法,并不適合她去賞析。“現代詩學習西方詩歌的東西,但忽略了中西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而且西方詩歌與我們詩歌,有著很不相同的韻律。”
相比生前孤寂,身后落寞的黃仲則,安意如筆下的黃仲則,在強烈的宣傳攻勢下,可能會有明朗的市場前景。這在某種意義上喻示著,黃仲則在并非詩歌的年代里寫下的詩歌,自有其流傳后世的恒久價值。同樣,在并非文學的黃金時代里,對文學寫作的堅持,依然有其特殊的意義。作為從文學的黃金時代里走過來的先鋒作家,格非強調,文學黃金時代的逝去,并非代表文學的衰敗,而是告別了單純社會功能的層面,回到了它本身。“文學曾經被強行拉到服務于政治、社會的層面,它的功能被放大。黃金時代文學的唯一功能被認為是推動社會,但是現在社會通過法律、傳媒等科學化方式就可以推進,不需要靠文學推動。”
以格非的理解,這意味著,眼下回到了一個文學相對正常的時代,有不同的人在從事不同文體的寫作,而文學對一些人來說不怎么重要,但對某些人來說或許很重要。相應地,文學的使命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學不能幫你什么忙,但它能幫你找到跟生活之間的真實關系。現在幾乎所有電視、報紙上的信息,都在討好你、迎合你,讓你進入這個時代的文化消費中。但文學要觸碰你的經驗,它通過觸碰你、冒犯你,來讓你來思考你所面對的真實境遇。”
某種意義上,黃仲則的詩歌,正是對他所處的時代,及那個時代里的庸常自我的冒犯。作為詩歌奇才,他無緣生于唐宋,雖有才華,思想心境卻與時代格格不入。而文學的真諦或許就在于如格非所說的,它天然帶有冒犯的力量。“托爾斯泰當年說,存在著兩種生活,一種稱之為安全的生活,另一種是真實的生活。后者充滿危險,需要付出代價。而文學會給你提供一個強大的支撐,讓你在選擇生活道路的時候,覺得你和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站在一起,去獲得真實生活的勇氣。”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